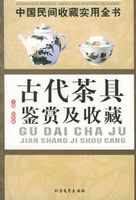以上观点看到了曲辞与宾白的区别,即“雅”与“俗”的区别,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元杂剧版本来考察,元杂剧中的确存在曲雅白俗的现象,这一现象似乎颇令人费解,何以同一剧本中的文字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呢?上述各家观点虽然有其道理,但从常理上来分析,一本剧作的作者分别由文人与艺人来完成,这似乎很难说通。所以,王国维就很不赞成这种观点:“填词取士说之妄,今不必辨。至谓宾白为伶人自为,其说亦颇难通。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此最易明之理也。”
由于“宾白”的不稳定性和文字的俚俗,使得许多当代研究者依旧认为宾白是伶人所作。但是,我们认为,王国维先生的观点是比较正确的,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元刊杂剧三十种》来看,许多剧本就有“宾白”的存在,虽然很简略,也很减省,有的甚至没有,但也用一些诸如“一折了”、“云了”、“说关了”等形式省略宾白。到了明代,许多关于元杂剧的刻本、抄本如《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古今名剧合选》、《元曲选》等元杂剧中却都有整齐的宾白。从这些现象来考察,我们认为,作为元杂剧中次要的因素,最初的元杂剧本身宾白就比较少,而且,由于元杂剧是由宋金杂剧与诸宫调相结合而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所以,伶人在表演时还保留了俳优的语言特征,常常在舞台上会随时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现场情况,运用剧本中没有的语言来吸引观众、调动现场气氛,正如孔尚任在在其《桃花扇·凡例》中所说:“旧本说白,止做三分,优人登场,自增七分俗态恶谑,往往点金成铁,为文笔之累。今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所以,剧本中的宾白除对戏曲情节理解和故事发展有关系的部分,经常不需做出细致的提示;
第二,正如上文所以王国维先生所言:“元剧之词,大抵曲白相生;苟不兼作白,则曲亦无从作,此最易明之理也。”元曲家如果不兼作宾白,在故事的紧凑程度上,在情节的发展与推进方面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即王国维所谓的“苟去白,则曲全无意味。”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强分曲与白作者的观点是很难站住脚的。
第三,元杂剧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很多戏曲作家,在创作曲词的同时,也在完善宾白。而且随着戏曲程式化的形成,宾白也开始从过去的从属地位上升成戏曲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时候,宾白就开始成为了文人在进行曲词创作同时必须要注重的一个方面,因而宾白的创作也越来越完善,也即孔尚任所谓:“今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的情况。但是,由于宾白具有“俗”的传统,且考虑到接受者的文化层次问题,文人在创作宾白的时候,也经常使用俚语、俗语,因而给人一种不太协调之感。其实,我们只要稍微联想一下所谓的“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认为,宾白完全是文人在考虑到舞台效果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
§§§第三节宾白的功能
一、塑造人物形象
杨恩寿《词馀丛话》中所云:“凡词曲皆非浪填,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可见者,则此词曲以咏之。若叙事,非宾白不能醒目也。使仅以词曲叙事,不插宾白,匪独事之眉目不清,即曲之口吻亦不合。”元杂剧是以唱为主,曲白相生的艺术,虽然大段的唱词来抒发人物的感情或进行性格塑造,要比宾白具有更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但由于一人主唱的演出体制,使得其他人物形象往往不能通过曲来展现,这就体现出了宾白的重要作用。
《看钱奴》是以其讽刺艺术著称的,所以,其宾白就相对要细致而富有特色,。比如第三折中的一段宾白:
(贾仁云)我儿也,你不知我这病是一口气上得的。我那一日想烧鸭儿吃,我走到街上,那一个店里正烧鸭子,油渌渌的,我推买那鸭子,着实的抓了一把,恰好五个指头抓的全全的。我来到家,我说盛饭来我吃,一碗饭我咂一个指头,四碗饭咂了四个指头。我一会瞌睡上来,就在这板凳上,不想睡着了,被个狗舔了我这一个指头。我着了一口气,就成了这病。罢、罢、罢!我往常间一文不使,半文不用,我今病重,左右是个死人了,我可也破一破悭,使些钱。我儿,我想豆腐吃哩。
贾仁在《看钱奴》中由净脚扮演,这段宾白成功地刻画并塑造了一个吝啬鬼的形象,通过剧中人贾人的讲述,不仅夸张地表现了一个为富不仁的吝啬鬼得病的原因,同时也让观众对这个可恨又可伶的家伙有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元杂剧是的接受者主要是普通的广大市民百姓,所以,作者在创作时就必须要“投合最大多数的民众之口味。”换句话说,就是要考虑广大民众的审美心理、欣赏兴趣与接受能力,因而特别注重人物形象的“本色”。而表现本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多用俗语、俚语等富有生活气息的语言。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常言俗字,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为了适应普通大众的审美心理与演出的需要,杂剧作家在创作时就必须要注意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特征,能够使观众正确把握人物性格特点,在观众的心理上迅速获得认可并进入情节,留下深刻印象。而相对于比较华美的曲,宾白就显得更加生活化,更加能够还原特定环境下的生活真实,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
比如《渔樵记》中就大量运用了市民口语、俗语来突出人物形象:
【旦儿云】朱买臣,巧言不如直道,买马也索籴料,耳檐儿当不的胡帽,墙底下不是那避雨处,你也养活不过我来,你与我一纸休书,我拣那高门楼、大粪堆,不索买褂有饭吃,一年出一个叫化的,我别嫁人去也。
【正末云】刘家女,你这等言语,再也休说。有人算我明年得官也。我若得了官,你便是夫人县君娘子,可不好哪!
【旦儿云】娘子,娘子,倒做着屁眼底下穰子;夫人,夫人,在磨眼儿里!你砂子地里放屁,不害你那口碜;动不动便说做官!投到你做官,你做那桑木棺,柳木棺,这头踩着那头掀,吊在河里水判官!丢在房上晒不干。投到你做官,直等的那日头不红,月明带黑,星宿眨眼,北斗打呵欠;直等的蛇叫三声狗拽车,蚊子穿着兀刺靴,蚁子戴着烟毡帽,王母娘娘卖饼料。投到你做官,直等的炕点头,人摆尾,老鼠跌脚笑,骆驼上架几,麻雀抱鹅蛋,木伴哥生娃娃,那其间你还不得做官呢!你这嘴脸,上角头饿纹,驴也跳下过去!你一世儿不能发迹,将休书来!将休书来!
这段对话,在玉天仙的口中,什么蚊子、蚁子、驴子、粪堆、屁眼、放屁、蛇叫、人摆尾、老鼠笑、骆驼上架几,麻雀抱鹅蛋,木伴哥生娃娃等等俗语接二连三说出,并运用了大量的民间俗语、成语、谚语、歇后语和一连串排比、谐音、夸张的口语和俚语,将民间语言的趣味性表现得鲜活淋漓,同时也让玉天仙这个泼辣、势利的市民形象跃然纸上,不仅富于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更容易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让观众感觉亲切自然。
二、展示复杂的人物心理
罗纲在其《叙事学导论》中指出:“个人的真正生活,只有对话渗入其中,只有它自身进行回答和自由地揭示自己时才是可以理解的。”也就是说,语言是可以揭示自己你真正的生活,并能表达自我经历和内心情怀的重要工具。如《绉梅香》第二折:
(旦儿云)那生病体如何?(正旦背云)我说的重着些。(回云)那生病体甚是沉重,看看至死。(旦儿背云)怎生便病的这般了也?我又不敢着意问他,怎生奈何?(正旦背云)适间小姐所问,颇见其意,这般呵,不妨事。(回云)小姐,恰才樊素探白敏中病去来,他着我将数字来,申意小姐,不知上面写着什么……
【六国朝】(旦儿见香囊背云)嗨!怎生落在他手里。(正旦云)你不道来,大胆小贱人,这里是那里?(唱)……
这段宾白就是运用“背白”比较成功的例子,通过正旦与旦儿两人的背云成果地突出小姐的矛盾的心理,从而把一个既心急又矜持的性格展现出来了,同时,也通过正旦的开玩笑和小姐的急心对比,突出了两个人的不同心理状况。
另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梧桐雨》,《梧桐雨》是末本戏,主唱者是玄宗,而杨贵妃虽然没有唱词,但我们可以通过其宾白来看出她的内心世界。在第三折马嵬兵变,杨国忠被杀,禁军进一步提出必须处死杨贵妃以平息众怒的要求下,身为天子的唐玄宗不但无能为力,而且吓得“战钦钦遍体寒毛乍”。下面是一段对白:
(云)杨国忠已杀了,您众军不进,却为甚的?
(陈玄礼云)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
(高力士云)贵妃诚无罪,然将士已杀国忠,贵妃在陛下左右,岂敢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矣。……
(旦云)妾死不足惜,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正末云)妃子,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
(陈玄礼云)愿陛下早割恩正法。
(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
(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
(陈玄礼云)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若不正法,以谢天下,祸变何时得消?望陛下乞与杨氏,使六军马踏其尸,方得凭信。
(正末云)他如何受的?高力士,引妃子去佛堂中,令其自尽,然后教军士验看。
(高力士云)有白练在此。
(高力士云)娘娘去罢,误了军行。
(旦回望科,云)陛下好下的也!
(正末云)卿休怨寡人!
我们可以从这段对白中审视杨贵妃在赴死前的心理变化。在陈玄礼开始提出要处死自己时,杨贵妃首先表示她先是表示“妾死不足惜”,但面对死亡,她还对玄宗抱有一丝幻想,希望用平日的恩爱打动玄宗,所以,在说出“妾死不足惜”之后,紧接着就表示:“但主上之恩,不曾报得,数年恩爱,教妾怎生割舍?”一方面是面对死亡的恐惧迫使她做最后的努力,用感情来打动玄宗,另一方面,也在为自己能够活下去寻找道义上的理由。她的努力显然没有成功,玄宗表示“不济事了,六军心变,寡人自不能保”,杨贵妃已经顾不上委婉表达自己求生的渴望,急忙发出“怎生救妾身一救”的哀求。但当最后的努力也归于失败时,她发出略带愤恨的“陛下好下的也!”的最后抗争之音,而且是加上一个“回望”的动作,杨妃的全部性格与复杂的内心矛盾就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杨妃当时那种失望乃至绝望的心情是如何的强烈。
三、推动故事发展
罗念生在《论古典文学》中谈到:“动作固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行动,戏剧中的对话要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更能表现行动和冲突。”的确,由于曲文是演唱,观众虽然很喜欢唱腔,但对于所唱内容却不一定能完全把握,而宾白由于通俗易懂,对于一些水平不是很高的观众来说,可以通过宾白了解故事内容,于培养对戏曲兴趣爱好而言,无疑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另外,戏曲是综合艺术,科白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宾白如果运用得当,不仅可以补充唱词难以表达的内容,还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如《李逵负荆》第二折:
(云)众兄弟每都来听着。
(宋江云)你着他听什么。
(正末云)俺如今和宋江鲁智深同到那杏花庄上。只等那老王林道出一个是字儿。你那做媒的花和尚。休要怪我一斧分开两个瓢。谁着你拐了一十八岁满堂娇。单把宋江一个留将下。待我亲手伏侍哥哥这一遭。
(宋江云)你怎生伏侍我。
(正末云)我伏侍你。我伏侍你。一只手揪住衣领。一只手揝住腰带。滴留扑摔个一字。阔脚板踏住胸脯。举起我那板斧来。覰着脖子上可叉。
(唱)便跳出你那七代先灵也将我来劝不得。(下)
(宋江云〕〕山儿去了也。小偻罗鞴两匹马来。某和智深兄弟亲下山寨。与老王林质对去走一遭。
这段对白生动活泼,不仅给观众留下充分的动作提示,而且通过李逵激烈的言辞,迫使宋江不得不亲自下山与王林去对质,从而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四、拓展舞台空间
众所周知,舞台是一个相对固定和狭小的空间,而故事却有着极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所以,要想在舞台上表现出这种情境,就不能离开宾白的帮助。
如《救风尘》第一折:
(周舍上,云)自家周舍,来此正是他门首,只索进去。
第二折:
(云)如今着这妇人上了轿,我骑了马,离了汴京,来到郑州。
第三折:
(云)说话之间,早来到郑州地方了。小闲,接了马者。且在柳荫下歇一歇咱。
以上空间的转换,均是演员通过宾白对于环境的交待中完成,这就使得演员能够在舞台这个有限的空间中进行全方位的表现,即“对话着的人物可以随时游离出剧情虚构域而返回现实游戏域。”
宾白不但能突破空间上的限制,而且还可以突破时间上的限制,如《秋胡戏妻》第二折:
(净扮李大户上,诗云:)“……如今秋胡当军去了,十年不回来。……”
(罗上,诗云:)……“自从秋胡当军去了,可早十年光景也。……”
(卜儿上,云:)……“自从孩儿当军去了,可早十年光景音信皆无……”
(正旦上,云:)……“自从秋胡去了,不觉十年光景……”
再如《货郎旦》第三折:
(孤抱病同春郎上,云)自家拈各千户的便是。自从我在洛河边买的这春郎孩儿,过日月好疾也,今经可早十三年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