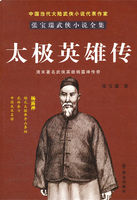让他们感到宽心的是,后半天斌武开始表现得乖顺起来,他们怎么送来饭就怎么吃,他们怎么劝解他话,他就怎么答应。
其实,自打上次疤三儿带人去过强盗沟后,斌武就再也没有见过月圆。斌武知道今天钱福顺过寿,更知道月圆今天订婚,斌武的内心痛苦得死去活来,可他只能是像一只被困在圈里的老山羊无奈地等待着什么。后来想到晚上上白彪岭唱戏,他安稳了许多。他想,他固执地想,他一定要去一趟上白彪岭,一定要去见一面月圆。见了月圆又能怎么样?他没有多想,但是他一定要见见月圆,只是见一见,见一见都不能行吗?一定要见。
也许是因为霍斌武装模作样的乖顺表现,晚上,家里人的警惕性有所放松,霍斌武借上厕所的机会,翻过土夯的围墙,一路直奔上白彪岭去。
斌武不知道,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去想,钱福顺为了防范有人来上白彪岭寻衅滋事,早已安排好了疤三儿等治安人员随时随地采取应急措施。
斌武一进上白彪岭,已经就被人盯上了。只是钱支书事前有吩咐,只要他不乱来就不动他,这才放他进入露天戏场。斌武走进戏场里的时候,戏台上,扮演沈皇后的旦角演员正唱道:“万岁莫要动真气/妾妃有本对君提/汾阳王今辰寿诞期/八婿七子在宴席/一个个成双又配对/只有咱驸马独自己/哥嫂们一定会闲言碎语/难道说驸马就无有面皮/驸马难堪回宫去/皇儿也不肯把头低/招惹的驸马火性起/才引起这场闲是非/为君的应有容人义/念只念老亲翁年迈苍苍白了须/消消火压压气/哪有个岳父大人斩女婿……”若是平常,霍斌武是会很认真地聆听、品味戏词的,也会和其他年龄大些的戏迷们一样高声叫好的。可是,现在他的心思不在戏曲上,他着急着想要尽快见到月圆。他知道,看戏时,老年人一般都带个板凳什么的坐在前边,年轻人则喜欢站在后边,注意力也不一定在戏台上,而在周边同样年轻的男男女女。
斌武就在年轻人堆里寻找着月圆的身影。
露天戏场里只是在两根高杆子上挂了两盏瓦数不大的灯泡,探眼看去,人影绰绰模模糊糊,斌武东瞅西看,好歹看不到月圆的身影。正想着,月圆是不是就没有来,或者是不是被钱福顺关在了家里?却听见一个女子的声音:“三姐、三姐,咱们到这边看,这儿堵得甚也看不见?”
寻声望过去,却就看见了月圆熟悉的身影,正被她妹妹月爱拉着移动位置。斌武急忙从人群中挤过去,挤得人群一阵骚动,甚至有人骂骂咧咧,他却是什么也不管不顾,挤过去,一把拉住月圆就往外边跑。
月爱惊叫了一声:“你是谁?你做甚咧呀?”
马上就有几个年轻后生把斌武和月圆堵住了。月圆看清了斌武,迅即摔开斌武拉着她的手,着急地用空拳捶着斌武的胸膛:“哎呀,你怎来了咧,你来做甚呀,做甚呀……”
斌武只说:“月,咱们走、咱们走……”
“走?大腿上的虱子——往球上走咧!”疤三儿喊叫着,“钱支书,下白彪岭的可真来搅场子了啊!”
钱福顺披着件崭新的灰色的中山装从人群后面走进来,他手里拿着一只长把子手电筒,手电筒照在斌武的脸上,晃得斌武睁不开眼睛。钱福顺冲着月爱和刚刚挤进来的大女儿月娥、二女儿月琴叫喊:“你们把月圆拖回的,关起来,等等我回去再整治她!”
“月圆不走!”斌武一把把月圆抱在怀里。
月娥拖开月圆,一口唾沫吐在斌武脸上:“何地儿跑来的二百五!”
这时,月琴母老虎似的冲上来,一把揪住斌武的领口,伸手就是几个清脆的耳刮子:“是强盗沟骡子家的吧?怎么这么不要疙瘩×脸咧!”
斌武被月琴的耳刮子和咒骂激怒了,他说了一句:“你滚得远些!”说着,两手使劲一推,月琴就朝后飞去,幸好后面有人挡着,才没倒在地上。疤三儿一挥手,便有两个后生动作很快地把斌武的手扭到了后背上。
月琴震怒了,大骂着冲上来:“你妈的臭×,敢打老娘!”再次冲上来,拳打脚踢。
钱福顺叫唤了一声:“行啦!把月圆弄回去!”
月琴不敢违背钱福顺的命令,骂骂咧咧过来拖拽月圆。忽而,她又放开手,返身揪住斌武的头发,让斌武的脸仰起来,一口唾沫啐了斌武一个满脸花:“记住,这是还你老子霍把式的,在渔场里平白无故啐老娘一口就没事啦?”
斌武也想啐月琴一口,头却被人压了下去。
月圆被她的姐妹们拖出人群,月圆哭着:“斌你真蠢咧,你来做甚呀,你来做甚呀……”
嘈杂的人声湮没了月圆的哭泣。
钱福顺往霍斌武面前走了一步,哼哼哼笑了几声:“真不愧是强盗沟的种,月黑风高夜,跑到我上白彪岭打家劫舍来了?”
斌武被两个后生扭着胳膊,身子朝前弯着,却使劲儿把头仰起,说:“我是来寻月圆的,不关你们的事!”
钱福顺:“你说甚?脱下裤子来撵毛狼——胆大不害羞!竟敢跑到我上白彪岭来耍流氓,还耍到我老钱家孥子身上啦,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啦!”
疤三儿吼叫道:“怎咧,钱支记,咱们是活剥这狗日的,还是劁了他,让他当太监!”
钱福顺说:“不用影响唱戏,把他带到大队去,咱们上白彪岭是有名的文明村,不能乱来,公事公办,叫镇派出所来处理!”
钱福顺说的大队其实就是设在村中心的村委会办公地。
斌武被疤三儿一帮人像押犯罪分子一样押进了村委院子,又进了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吊着一盏电灯泡,亮堂堂的。钱福顺一屁股坐在办公椅上,先是推了推放在桌子上的那支绑着红布的麦克风,然后耸了耸肩,没让披着的中山装掉下来:“说吧,骡子家的,是把你送派出所蹲号子,还是敲断你的一条狗腿?”
霍斌武两眼一瞪:“你家才是骡子家!”
疤三儿一个耳光扇过来,斌武侧脸躲过,疤三儿随手一拳却就砸在斌武的脸上,斌武的嘴里便冒出了血泡泡。
钱福顺断喝:“疤三儿,不许随便打人!”
疤三儿说:“我可没打他,是这狗日的想打我咧!”
钱福顺似乎没有理会疤三儿的回话,却对斌武说:“我不唤你是骡子家的,我唤你的尊姓大名:霍斌武,你听着,我不唤你是骡子家的,可你家就是个骡子家呀,你知道是为甚?是因为你家祖上在强盗沟做了损事了,报应了,绝后了!”
“你才做了损事,你才绝后咧!”
“我做甚损事了,我怎么就绝后了?”
“你拆了龙天庙,你损塌天灵盖!你生不下嗣儿,生下嗣儿也没屁眼!”
钱福顺从来没有让人这般指责过,在场的人都以为他会怒发冲冠,却是没想到,钱福顺忽然哈哈哈大笑起来,说:“拆不拆庙关你祖宗八辈儿裤裆里的事咧?老子没生下嗣儿怎咧,一个女婿半个嗣儿,老子四个孥子,两个嗣儿咧!”
霍斌武很响地往地上吐了一口血水。
钱福顺没有在乎他的表现,眼睛却瞅着门口的灯绳,说:“说过多少回了,不要你来上白彪岭,你还牛头八怪不识好人劝,你又来了,来了好啊,你说吧,是把你送派出所蹲号子,还是敲断你的一条腿?快说吧,不用耗时间,等会儿停了电,黑灯瞎火的,话也就不好说了……”
钱福顺这般说话的时候,听见灯开关“吧嗒”一响,房子里忽然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