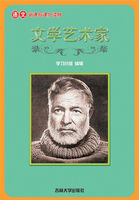心理欲望
听到那炮弹的第一响轰隆声,我们发现自己存在中的一部分,猛一下子跳回了一千年。一种在我们心里觉醒过来的动物的本能,指导着我们,保护着我们。那倒不是意识到的,那比意识更加迅疾,更加可靠,更加不会失误。那是谁也没法儿解释的。一个人随随便便地走着,心里什么也没有想,忽然间他扑倒在一个土炕里,而一阵碎片便打他头顶上飞过去;可他就是记不清楚,是不是已经听到那炮弹在飞过来,还是想到自己要扑下去。不过,倘若他不是凭这种冲动行事,那么他现在肯定已经成肉酱一堆。正是这另一种,我们身体里的一种具有洞察力的嗅觉,使我们仆倒下去,救了我们的命,而我们自己却并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要不是这样,那么从佛兰德到孚日早已没有一个人会活着的了。
——[德]雷马克:《西线无战事》
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上跛跛踬踬,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说实话,我在这软绵绵的歌舞升平的年代,却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无非背着阳光窥见自己的身影,口中念念有词,埋怨我这废体残形。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趁着韶光洋溢卖弄风情,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许,专事仇视眼前的闲情逸致了。我这里已设下圈套,搬弄是非,用尽醉酒狂言、毁谤、梦呓、哀叹使我三哥克莱伦斯和大哥皇上之间结下生死仇恨;为的是有人传说爱德华的继承人之中有个G字起头的要弑君篡位,只消爱德华的率直天真比得上我的机敏阴毒,管叫他今天就把克莱伦斯囚进大牢。且埋藏起我的这番心念,克莱伦斯来了。
——[英]莎士比亚:《查理三世》
他用自己灵魂里全部力量去爱她,觉得为了她的微微一笑,就能使他把鲜血、品德、荣誉、不配和永恒,今世和后世的生命通通抛弃;他恨自己不是国王、天才、皇帝、天使或神灵,不能在她脚下成为一个比较伟大的奴隶;他日日夜夜认在思想里和睡梦里拥抱她,但他看见她喜爱的却是军官的制服,而自己能献给她的只是她所害怕和嫌弃的肮脏的教士长袍,她把她的爱情与美貌浪费在一个可恶的笨蛋身上,他便着嫉妒与愤怒出现在她面前。看着那使人燃起欲记忆的形体,那十分甜柔的胸脯,那在别人的亲吻下颤动和羞红的肌肉啊,天哪!爱着她的脚,她的手臂,她的肩膀,梦想着她的发蓝的脉络,她的浅褐色的皮肤,一直到他整夜地蜷伏在自己那小房间的石板地上。但是看见他所梦想的种种温存竟使她遭受刑律,竟使她去躺在那张皮床上!啊,那真是些用地狱之火烧红了铁钳呀!哪怕是被锯死的人或被五马分尸的人,也都比他幸运呀!你知道忍受着怎样的疼痛,在那些漫漫长夜里,他血液沸腾,心灵破碎,头脑胀痛,他用牙齿咬着自己的手,残忍的苦刑使他像辗转在烧红的铁耙上一样,辗转在爱情、妒忌和失望的念头上!姑娘!慈悲吧!对我宽大一会儿吧!在这个伤口上涂点香膏吧!我求你揩掉我额头上大颗地流淌的汗珠!孩子啊,请你一只手惩罚我,另一只手爱抚我吧!怜悯吧,姑娘,怜悯我吧!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
情境迷茫
这是奥勃洛摩夫一生之中清明觉醒的一瞬。
当关于人的命运和使命的生动而明晰的观点,在他的心里突然产生的时候,当这些使命与自己的生活之间的对比一闪而过的时候,当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在他心里一一觉醒,像小鸟在睡眠着的废墟内,突然被阳光所惊醒,胆怯地乱飞一阵的时候,他是多么惶悚啊。
为了自己的智能开展过晚,精神上的力量停止发展,为了头脑昏昏沉沉妨碍着他的一切,他感到忧愁和苦痛;看到别人这样充实、这样开朗地生活,自己却仿佛有一块沉重的石头给投在他那狭窄而可怜的生活途径上,嫉妒心就刺痛着他。
他自觉到他天性的某几方面没有完全觉醒,另外几方面也仅仅给触动了一下,任何方面都没有彻底发展,他那怯弱的心灵里就产生一种苦痛的意识。
同时他痛苦的感觉到,有一种美好而辉煌的元素,像埋在坟墓里似的埋在他的心里,也许现在已经死了,或者像黄金似的埋在矿里,虽然早已是把这批黄金铸造通货的时候了。
可是这个宝藏被脏东西和积起来的垃圾深深地、沉重地埋了起来。仿佛有什么人把世界和人生赠送给他的宝贝偷了去,埋在他本人的心里。仿佛有什么东西阻碍他投身人生舞台,不让他用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在台上鼓翼翱翔。仿佛有一个暗中的敌人,在他人生之路的起点,把一只沉重的手臂加在他的身上,把他从笔直的、人生使命的道路上远远地甩掉了……
仿佛他再不能从密林和荒野中回到笔直的小径上去。他周围的以及他心里的树林,越来越密,越来越暗;小径越来越蔓草丛生;清明的意识觉醒得越来越稀少,而且仅仅把睡眠着的力量唤醒片刻。他的理智和意志早已麻痹,而且似乎要永远麻痹了。
他生活上的事件,已缩小到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而且就是这些事件他也对付不了;并不是他从一件事情转移到另一件事情上去,而是它们把他好像从一个波浪抛到另一个波浪似的抛来抛去;他既不能凭意志的弹力去对抗一件事物,也不能凭理性去追求另一件事物。
这种内心里的自我忏悔,在他是痛苦的。对于往事的无益的憾惜和良心上剧烈的谴责,像针一样地刺痛着他;他竭力要摆脱这些谴责的重荷,要找到另外一个可以归咎的人,要把这个针刺移转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可是移转到谁的身上去呢?
——[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
同一的思想,那么常使他烦恼的,现在又冲过他的脑中了。生命,他这样的说着,已经在他身边走过了;即一个英雄的生活,其开头也是充满了倦厌与悲哀的,其结局也是没有快乐的。他记忆起他的生活永远是在期待些什么新的,把现时所做的事情看作是临时的;可是它“临时”在拉长着,正和蚕一样,不住的发展出新的身段,而蚕的尾端都渐渐地在老死中隐消下去了。
“一个成功!一个某一种的胜利!”犹是绝望的扭绞着他的双手。“去显名一时,然后死了,没有恐怖,没有痛苦。那是惟一真实的生活!”
一千种的冒险,一种比一种更为英雄的,皆自现于他的心上,每一种都像冷笑的死亡的头颅。犹里闭了他的眼,能够清清楚楚的看见一个灰色的彼得堡的清晨,潮湿的砖墙,及一具绞架朦胧现于铅色的天空。他幻想有一把手枪的铁管压在他的额前;他想像他能够听见皮鞭痛快打在他的无抵抗的脸上及赤裸的背上。
“那便是为一个人而储待着东西了!一个人必定到那里去!”他叫道,烦恼地挥着手。
英雄的行为消失了,代替而生的,乃是他自己的无助,像一个讥嘲的面具对他冷笑着。他觉得,所有他的胜利的梦想以及勇气,都不过是孩提的幻想而已。
“我为什么要牺牲了我自己的性命或投服与侮辱与死亡,为的是要使20世纪的工人阶级不会因乏食或缺少性的满足而受苦呢?鬼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工人与非工人都取了去!”
犹里重又感到一种无边的恶毒,无目的而且使他自身痛苦地侵袭过来。他全身盘踞着一种抛弃一切,脱身世外的不可抑止的需要。但是不可见的爪牙紧紧地握住,完全的疲倦之感冲到他脑里,心里,活的躯体充满了死的幻灭。
——[俄]阿乐志跋绥夫:《沙宁》
嫉妒心态
羊脂球吃东西时,饥肠辘辘的贵妇人们所有的眼光都向她射过来了。不久香味散开了,它增强了人的嗅觉,使得人的嘴里浸出大量的口水,而同时腮骨在耳朵底下发生一阵疼痛的收缩。几个贵妇人对这个“姑娘”的轻视变成猛烈的了,那简直像一种嫉妒心,要弄死她,或者把她连着银杯子和提篮以及种种食品都扔到车子底下的雪里去。
——[法]莫泊桑:《羊脂球》
萨克勒门先生从孩童时代起,装在脑子里的只有一个想得勋章的念头。……由于没有权利可以在礼服上佩带一条有颜色的勋表丝带,他是一直痛苦的。他在城基大街上遇见了那些得了勋章的人,常常使他心上受到一种打击。他抱着愤怒的嫉妒去侧眼瞧着他们。……他在街上慢慢地走着,利用自己那副惯于从远处分辨那种小小的红点的眼光,去考查人家的衣服。等到散步完了的时候,他因为那些数字吃惊:“……竟有这么多!”……他如同一个挨饿的穷人经过了大饮食店的前面而生气一样,因为遇着那么多的勋章气坏了……晚饭以后,他依然又上街了,后来考查了那些制造勋章的铺子。他审查了一切不同的典礼当中,在一个满是宾客的和满是惊奇者的大礼堂里,自己挺着一个胸脯,上面挂着无数垂在彼此重叠如同肋骨一样的别针之下的光辉闪烁的勋章。
——[法]莫泊桑:《勋章到手了》
阿巴公:喂!你说什么?原来并没有人。不管是谁下的手,他们是处心积虑地早把机会琢磨好了的;他们恰恰是拣我跟我那个吃里爬外的儿子谈话的时候,咱们出去吧。我要到法庭去报告,我要请法官来审问全家的人:女仆、男仆、儿子、闺女,全得审,连我也得审。这儿怎么聚了这么多的人啊!所有的人不管谁,我瞧着都可疑,都像偷我的钱的贼。你们在那儿谈论什么呢?谈论偷我的那个贼吗?上边怎么嚷嚷得这么凶啊?莫非偷我的贼就在那里吗?慈悲慈悲吧!谁要是知道我那个贼的下落,我哀求你们赶快告诉我吧。他没躲在你们当中吗?大家都拿眼睛盯着我,都笑了。瞧吧,偷我的这一案里,他们必定都有份儿。你们快来吧,调查员呀,警察呀,法警呀,审判官呀,快来吧!拷问的刑具呀,绞架呀,刽子手呀,全拿来吧!我要请求把所有的人都给绞死;如果我不能把我的钱重新找回来,我自己也得上吊。
——[法]莫里哀:《悭吝人》
烦躁
今晚,我独自回到旅馆,那一位准备晚一点回来。心中便有了焦灼,就像毒药已经准备好了似的(嫉妒,被抛弃感,坐立不安);胸中的焦灼在积蓄等待,只消一会儿功夫,便会以合适的方式外露出来。我“镇静地”拣起一本书,服了一粒催眠药片。偌大的旅馆,寂静中透出回籁,冷漠而又呆板(什么地方的浴缸在排水,发出咕噜声,听起来那么遥远);房间里的陈设和灯光都那么死板板的,没有一点点人情味可让人温暖一点(“我冷,咱们回巴黎去吧”)。愈加焦灼起来,我注意到了这个心理变化,就像苏格拉底在喋喋不休时(我正在读),觉得毒药开始在体内发作起来;我听得见它渐渐涌上来,像是带着一副漠视一切的精神,与周围的一切相呼应。
——[法]罗兰·巴特:《恋人絮语》
聂赫留朵夫到这里来是为了散散心。平时他在这座房子里总感到很愉快,不仅因为这种豪华的气派使他觉得舒服,而且周围那种亲切奉承的气氛使他高兴。今天呢,说也奇怪,这座房子里的一切,从门房、宽阔的楼梯、鲜花、侍仆、桌上的摆设起,直到米西本人,什么都使他嫌恶。他觉得米西今天并不可爱,装腔作势,很不自然。他讨厌柯洛索夫那种妄自尊大的自由派论调,讨厌柯察金老头那种得意洋洋的好色的公牛般身材,讨厌斯拉夫派信徒卡吉琳娜的满口法国话,讨厌家庭女教师和补习教师那种拘谨的样子,尤其讨厌米西说到他时单用代词他……聂赫留朵夫对米西的态度常常摇摆不定:有时他仿佛眯细眼睛或在月光底下瞅她,看到了她身上的种种优点,他觉她又娇嫩,又美丽,又聪明,又大方……有时他仿佛在灿烂的阳光下瞧她,这样就不能不看到她身上的种种缺点。今天对他来说就是这样的日子。今天他看见她脸上的每道皱纹,看见她头发蓬乱,看见她的臂肘尖得难看,尤其是看见她大拇指上宽大的指甲,简直同她父亲的手指甲一模一样。
——[俄]托尔斯泰:《复活》
他一晚没有睡好。他神经不安,常常突然之间身子抽搐,像触电似的。梦里有犷野的音乐跟他缠不清。他半夜里惊醒过来。白天听到的贝多芬的序曲,在耳边轰轰地响,整个屋子都有它急促的节奏。他在床上坐起,揉了揉眼睛,弄不清自己是不是睡着……不,他并不没有睡。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液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了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地透人了他的内心,使他的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比。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哦!多么痛苦!……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罢!永远受苦罢!……噢!要能坚强可多好!坚强而能受苦又多好!……
他笑了。静寂的夜里只听见他的一片笑声。
——[法]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