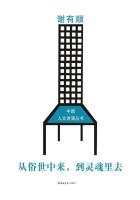盼了多年的第一场大雪终于来临了。
雪断断续续下了好多日子。落雪的白天和夜晚,都没有起风,天气并不怎么冷,甚至有一种微微的暖意。雪花在静悄悄地降落,落在唇边甜滋滋的,落在头上湿润润的。街旁的树上也落满了雪,只要有一点点风掠过,那树枝上的雪便像一群银色的鸽子,又像是一群白色的蝴蝶飞翔于枝条间。不知谁家孩童,时不时地放几响鞭炮,给这落雪的小县城平添了无限的喜气和祥瑞,让人不由得又有了春的感念,有了节日的相思和快乐。也让人回想起了小时候下雪的情景来。
那时候的雪,总是在不经意间就悄悄来的。有时,一觉醒来,满院的白,跑出门去,山野白花花一片,树枝上毛茸茸地积了一层。我喜欢辽阔,站在无垠的白色世界里,眺望着起伏绵延的“山舞银蛇”,幻想村子以外,该是什么样的雪天?
对干旱缺雨水的山里人来说,一场大雪就是一次盛筵。
如果运气不错,有时候一场大雪能下到尺余厚。雪往往是夜里落下的,睁开眼睛已成了一个银白而又肃穆的世界。远处的地平线上,覆盖白雪的山峰似乎一下变得平缓起来,显出了许多柔和美妙的曲线,大地上那种单纯的、无边无际的白色,会使人的内心变得非常恬静和谐。感情丰富的人,会在这样的时刻产生诗的联想,画的意境,音乐的旋律。
大雪不仅给山塬塑造了灵气,而且使人的心里充实了,静谧了。它以温厚的面貌遮却了不少的坎坷和狰狞。一时间,人们像是处在了另一个空间里。放眼望去,在大片大片的银白里,蠕动着许多黑影。在雪的映衬下,他们像是一个个深奥的洞穴。
原来,这都是背雪的人。
人们嘴里喷着白雾,揣着一颗火炭一般热烈的心,三三两两四散在雪野里,用铁勺、缸子把白得发紫的雪装入自己的背篼或筐子里。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兄妹都不免贪婪起来,背着装满雪的背篼,踩在咯吱咯吱发响的雪地上一溜小跑,恨不能把这满世界的雪都装到自家的水窖和家里的水缸里。我们的手冻得红红的,抓一把雪搓洗搓洗,手就更红肿,然而不冷了。雪搓过的手竟渐渐热起来,水汽也从手上一缕缕浮散开来。到后来,我们一直把家里能装水的家具全装满雪才收工。到做饭时,锅里也堆满了雪,高高的把锅盖顶起在半空中。炉膛里的火异常地热烈着,伸出抒情四溢变化多端的舌头猛舔着锅底。锅盖就一点点落下去,直到能把锅盖盖严时,高耸的一锅雪融化成水就少多了,而且浑浑的。母亲便把浮漂在上面的麦秸柴火过滤掉,再把沉在锅底的泥沙澄除,给我们做熟的黄米黏饭,吃起来照样是那么的香喷喷。
要是白天降雪,当纷纷扬扬的雪花在天地间轻歌曼舞的时候,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关闭了门窗,把自己的琐碎和邋遢紧紧关在屋子里,让寂静笼罩了整个村庄。青烟袅袅盘旋在每户人家的屋顶,扶摇而上的身子轻轻躲避着雪花的追逐,那一缕朦胧的诗意衬托出的意境,如梦似幻。热炕上的乡亲们是温暖的,自足的。他们在炕上“折牛腿”、下象棋,拉谈憧憬着来年的好收成。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而炕洞里的热灰里埋着的洋芋,它的皮子已慢慢地变得焦黄,并且向外冒着热气。不多时,屋子外面的万物被雪姑娘罩上一层蝉衣锦绣,整个山塬像仕女一样恬静、娴淑、清香、悠远,淡淡的,圣洁的……
原来,那如诗如画的落雪,不仅仅是山里人的盛筵,更是上天赐给他们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