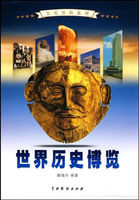杨大妈家酒店周围的商店里挤满了欢乐的姑娘。她们在协助母亲和结了婚的姐姐管理商店;同时凭着她们的本事充当交易中间人。生意之间空闲时,她们坐在门口台阶上,打着颜色俗艳的羊毛衫或在用各种颜色的丝线绣着七星花盘。每一个纳西族妇女,已婚的或未婚的,背上都披着一块传统的羊皮——狭长的女式披肩,它能保护她的背部,不受她永远背着的篮子的磨伤。羊毛朝里面,而外面肩头上盖有深蓝色的羊毛布披肩。这些美丽的小圆盘直径大约有二英寸。原来有两个更大的圆盘,代表太阳和月亮,可是现在不戴了。
这些姑娘无忧无虑、不知害羞,永远欢乐。有时她们还很调皮。可是她们内心是善良的,她们做生意的本领是惊人的。大约有八人的一伙姑娘,组成了某种形式的俱乐部。总是坐在一起讲闲话。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叫阿崇仙,大约有十六岁。她漂亮,皮肤白皙,很顽皮。她表姐阿妮仙大约有二十岁。她脸形圆而白皙,黄头发,绿眼睛。她老于世故,对于城里的人和事,她无不知晓。另一个姑娘满头乌发,胸脯鼓鼓的,名叫阿翠荷,一双大眼睛闪闪发亮。还有面貌特别秀丽而又强壮的阿荷华,温柔的丽迪娅(作者用西方美女名字来形容纳西族姑娘——译者注)。
对其他姑娘我不太了解,可是美丽的菲多西亚(作者用西方美女名字来形容纳西族姑娘——译者注)总是叫我羡慕,她在市场上开一个佐料货摊。她已经结婚,头上戴着黑色圆形套头,这是已婚妇女特有的头饰。她看上去完全像妮菲蒂蒂王后(埃及王后——译者注)。我把有名的早已去世的埃及王后的半身像拿给她看。她自己承认她和相片极为相像。杨大妈的已到结婚年龄的女儿阿福仙与这些姑娘是一代的。可是阿福仙忙着帮助她母亲,很少有时间参加其他姑娘们讲闲话或开玩笑。她面色灰黄,对人不友好,对她母亲的顾客总是尖声大叫;我想她不喜欢我到她家商店来,我们长期不和,但是表面上客客气气。无论何时她吵吵嚷嚷,我常提醒她没有一个丈夫会喜欢她这种脾气的姑娘,这话通常能制服她一会儿。
阿翠仙和阿妮仙时常观察着我到杨大妈家来,她们求我给她们一杯窨酒喝。
之后其他姑娘也过来了,你很难拒绝给她们也喝一杯。最后我发觉我的财政负担太大了。
“听着,阿翠仙,”有一天我说,“天天给你们付酒钱,我实在付不起了。”
“可是你很有钱。”她撅起嘴说。
“我并不富有”,我说,“我想我没钱来这里喝酒了。”
阿妮仙来了。
“让我们订个契约,”她说,“今天你招待我们,明天我们招待你。”于是我们达成协议。可是实行起来并不如此。所以只有星期六我答应给她们买饮料、甚至这个安排也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当我为听到某些好消息感到高兴时,我邀请她们额外喝上两杯,阿荷华的祖母傍晚路过市场时,我敬她一杯酒;她很高兴。她已85岁,然而还健壮,她会给我一个桃子或苹果作为交换。
像所有纳西族妇女和姑娘一样,阿翠仙和阿妮仙完全无拘无束,坦率到有点野性的程度。她们深深地牵连在本地方的丑事丑闻之中,她们如此兴致勃勃,满腔热情地向我讲述这些丑闻,尽管我麻木不仁,却抑制不住地脸红了。不久她们抓住了我到李大妈家酒店去的时间。
“你在跟她谈情说爱,就是这样。”她们有一天胜利地宣布道。“你小心!她丈夫是很嫉妒的。”她们警告说。尽管这个玩笑是荒唐的,全城人熬有其事的传说,当我说我要到李大妈家喝一杯酒时,有些人会意地向我眨眼睛。
阿翠仙和阿妮仙都无法相信我没有结过婚。
“我还在找媳妇。”我开玩笑地向她们保证说。
“阿翠仙,为什么不嫁我呢?”有一天我问她。
“呸!”她唾了一声,“情愿做小伙子的奴隶,也不做老头子的情人。”她说。
“我真的那么老那么难看吗?”我坚持说。
“当然啰,你那光头加上眼镜,你看起来有八十岁。”她粗鲁地答道。
“阿妮仙怎么样?”我继续说。
“阿妮仙已经有丈夫,很快就要结婚了。”她向我吐露说。
的确,几星期以后阿妮仙就不见了,好久之后我见了她一眼,她穿着已婚妇女的服装。她看上去很不高兴,也瘦多了。一个月以后她又回到石桥边她的老地方。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阿翠仙。
“我告诉你,”她说,“可是别告诉她是我说的。”然后她低声说,“阿妮仙离婚了。”我感到惊讶。
一两星期后,吾汉,我的一个朋友,他也了解这些姑娘的事,告诉我这场离婚案告到法院了。
“你为什么要与丈夫离婚?”法官问。阿妮仙勇敢地站出来说:“尊敬的法官先生,我的丈夫才是个小男孩,等到他长大,我已是个老太婆了,我不能等候。”
由于这或多或少是事实,法官立刻同意了她的请求书。然后他走下高台,来到阿妮仙跟前,按照吾汉的话,法官说:“阿妮仙,我这一辈子都等待着像你这样的女子,我是个鳏夫,我想娶你。”婚礼两星期后举行,这一次阿妮仙永远地抛弃了我们这小伙人。可是有时我们看见她,一个衣着华丽的少妇,法官的妻子,从市场穿过,向她的老伙伴们打招呼。
六点钟后市场逐渐空荡了,到7点钟商店都上了窗板。市场上的货摊都又收捡起来堆放着。街道上空空荡荡,已是吃晚饭的时间了。
直到傍晚8点钟后,大街上又开始挤满了人,商店又重新开门。有些商店点着普通的油灯,红色的灯光忽隐忽现。其他商店则用汽灯或煤石灯照明。不时点明子火把,人群来回走动,嘴里吃着葵花子和南瓜子。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街上挤满了人。未婚的姑娘,本地叫潘金妹(大姑娘的意思——译者注)穿着盛装,手挽手地走着,四五个姑娘成一排,正好把街道横拦住。就这样她们在街上冲上冲下,咯咯发笑,放声歌唱,吃着葵花子。粗心大意的小伙子很快被这些魁梧而有男子气概的女子征服,被她们领走,命运成了未知数。比较老练的小伙子们沿商店的墙和门站着,评论行进中的美女们。不时一群姑娘在一个小伙子跟前停住,作一场扭打、短暂而徒劳无益的挣扎,然后这个小伙子就被领走,被围困在姑娘们狂笑和尖叫声之中。这些囚犯的目的地,也许更情愿地是公园,在河边草地上,烧起明亮的篝火,歌舞持续到半夜。
李大妈的酒店晚上通常开着,可是换了顾客,主要是本地名门富豪子弟,他们饮酒作乐,然后没人陪伴地冒险在街上溜达。普通的村民和藏人,由于敬畏这些风流的调情说爱的人群,慢慢地走着,同样手挽手走成排。当姑娘们的队伍有意闯过来时,他们一般散开。有人尖叫或大笑,可是没人介意。银色的月亮从高空向下微笑,从松明子火把发出的芳香烟雾直升九霄。后来四方街上竖起几个大帐篷,逐渐把广场变成了营地。火炉架起来了,石头地面上摆开长凳和方桌。芬芳的气味开始从许多锅和盘上升起。
有时候我坐在其中一个帐篷里直到半夜,吃着一碗饺子或面条,观看着全副武装的藏族赶马人或部族人。更为稳重的城里人认为在这些帐篷里吃东西有点危险。有时土匪以奇异的伪装出现,喝醉酒的人之间的吵闹是寻常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杨大妈家酒店附近的一个姑娘,会给我一把明亮的明子火把,以便照亮我翻山回家的路。
藏族居住区下头是和大妈家的酒店,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高级的,她主要为藏族商人备办伙食。她家的房子在藏族居住区是最宏伟的大楼之一。她的两个儿子在拉萨,他们在那里办一个生意兴隆的进出口公司。最小的儿子在学校读书,是个又傻又没有礼貌的青年,经常用些愚蠢的问题挑逗我。她丈夫是个矮胖的中年人,他整天抽鸦片烟,在酒店里很少见到他。主要帮她忙的是她那个已长大的脸红得像苹果般的女儿,名字也叫阿妮仙。
和大妈是个身材丰满、像个慈母的中年妇女,整天欢欢喜喜;开着有伤风化的玩笑。她的酒店是李大妈的酒店的翻版,除了做正统的生意外,她实际上把它办成一个疲劳归来时的歇息处。她家的房子是城里最大的房子之一,共有三块间隔的院坝,用石板镶得很整齐,用大瓷盆种植的鲜花和灌木摆在雕花的座子上,作为装饰。整所房子里面雕刻精致,十分清洁,设备完美。主楼都附设有宽大的马厩。起初她曾留我住在边房里,后来又帮助我解决了很多难题。她提供的信息和李大妈的一样可靠,可是不像那个一本正经的老妇人,她喜欢议论丑闻,对当事双方她加上耸人听闻的叙述和精辟的评论。其结果是我离开她的酒店时总是笑痛了肚皮。她给我大量的礼物,有时一块火腿或一罐特地酿造的酒,或她从阿登子(德钦城)收到的某种新的洋白菜。我给她的孩子作免费医疗或送她美国花种菜种,尤其是甜菜种,虽然纳西族不喜欢吃甜菜,说甜菜太甜不能做菜吃。一天晚上阿妮仙红着脸来了,我议论说她涂了太多的胭脂。那不是胭脂,和大妈解释说,而是甜菜汁,阿妮仙优先使用了。这个古怪的做法很快传开,后来阿妮仙和她的伙伴就种植甜菜,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甜菜汁的化妆价值。
去和大妈家酒店的最佳时间是晚饭后。那时酒店里挤满了住在她家的藏族商人。和大妈经常把我介绍给他们。这些相会是非常愉快的:我们总是要谈到深夜。
顺从的藏族仆人不时地带来一些下酒用的精美食物。有一次来了一个东旺的喇嘛,他带着一个大马帮和许多曹巴仆人。他性格粗野,力气很大,此外还是一个大色狼。他甚至使自由随和的丽江人产生反感,在公园里当他猛然冲向成群的大姑娘时,姑娘们一边尖叫一边耻笑他,分散开去。他甚至一边和我喝酒,一边向和大妈使眼色。这使和大妈放声大笑。后来我逗阿妮仙说:“你为什么不嫁他呢?你会当上喇嘛寺女主人的。”我建议。
“你为什么不娶李大妈?”她闪电般地反击我。
通过她的在拉萨的儿子的介绍,许多有钱的马帮来到和大妈家。马帮头们受到和大妈殷勤热烈的接待,并且分配给宽敞而舒适的住所。他们的骡马和仆人也安排在同一幢房子里,过得很舒适。其他的赶马人和马匹如果有住房的话,就安排在隔壁邻居家里,或露宿在通向我们村的道路边。后头到来的马帮也同样对待,直到房子住满了。然而不允许安排得使任何客商感觉拥挤。藏人喜欢宽敞的房间,几个房间为两三个商人专门使用是常有的事。大量而贵重的铜器和银器装饰品,光亮的火盆和许多珍贵的褥子,这些东西是保持一个藏族商人的尊严和保证他过得舒适必不可少的。吃食好也是必需的。食物分别供应到每一伙人住的房间。在伙食方面仆人们随他们的心愿。
每隔一段时间和大妈为住在她家的客商举行盛宴,我通常都被邀请参加。食品是向一个包办伙食的人订的,按照陈规烹饪。可是饭后不久,赶马人在他们的女友陪同下来了。院子里烧起一小堆营火,院子角落里摆上小桌子,桌上放着白酒壶和酒杯。男男女女边唱歌边拍手,互相面对面,欢快地跳舞。不时地他们喝上一两杯酒以振作精神。他们喝得越多舞蹈也跳得越快,直到舞蹈乱作一团,变成了公开的谈情说爱。所有的营地都举行类似的舞蹈,整个夜晚有节奏的歌咏声不时传入我的窗户。
除了赶马人这种自发的舞蹈外,不时有小队的康巴歌舞演出队。他们由两三个妇女和大约同等数量的男子组成。作为一个特殊的标识,他们的腰带上挂着许多串珠子,他们带着单弦琴、琵琶、笛子、手鼓和小鼓。他们从一家到另一家,为了一小点施舍,五十分到一元,他们作精彩表演。历时约半小时,有歌唱,有旋转舞。如果主人要求,为了得到更多的酬金,他们可以击鼓起舞一整天。他们在丽江停留一两个月,看生意情况而定,然后转移到别处。他们的表演很有艺术性。
住在和大妈家的藏族商人吃住不用付钱,虽然他们在丽江通常停留一两个月。
不过和大妈取得了代销他们的货物的专利,所得的好处足以弥补她殷勤接待客人的费用。一年内有一两次她的一个儿子带着马帮从拉萨回来。如果货物不在丽江出售,就由马帮运到下关。可是和大妈并不跟随货物到下关去,因为丽江做生意的妇女没有一个想跑那么远。
居住在丽江北面大约七天马帮路程处的某个母权制部族人来到丽江时,总是要引起一场轰动。无论何时这些男女为购物而路过市场和大街时,丽江妇女和姑娘感觉她们的尊严受了伤害,而发出愤怒的低语声,耻笑声和尖叫声,男子也发出淫荡的评论。他们就是长江大转弯处对岸永宁领地的居民。纳西族称他们为吕喜,而他们自称里喜。他们的社会结构完全是母权制。家庭财产由母亲传给女儿。
每个女人有几个丈夫,于是孩子们总是说:“我们有妈妈可是没有爸爸。”母亲的丈夫们被称作叔叔,一个丈夫准许停留的时间只长达他能使这女人满意为止。如果他不能满足她,无须多少礼节她就可以把男的抛弃。
永宁领地实行婚姻自由,除了丈夫之外,永宁女子的全副精力都集中在引诱更多的情人上。无论何时藏族马帮或其他陌生人路过永宁,这些女子就聚在一起商量并且秘密地决定每个男子应该住在哪里。接着这位女子指示她的丈夫们避开,直到她来叫之前不要再来。她和女儿们为客人准备盛宴,为他跳舞。之后这位老妇人吩咐他在老经验和无知青年之间作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