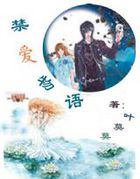回家的路
和钟华
家,是一个人生命的依托、心灵的港湾。离家,回家,是人生中的寻常事。
然而对我们和家来说,却显得寻常而又不寻常。
我是纳西女,家住丽江古城百岁坊。因祖上曾出了位拔贡,我家被称为“和拔贡家”。与大多数纳西人家不同的是,从拔贡老爷爷以来,我家几代人多出门在外,或寓居,或客死他乡者,代所不乏。回家,对我们这家人来说,更有一层现实的、具体的和心灵的、情感的历程。它意味着恋乡,思乡,感恩故乡,回报故乡……
先从我的祖上说起。高祖和钦是拔贡,生活在清咸同年间。拔贡是科举制度中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保送入京,作为拔贡(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故高祖当年曾到过昆明、北京。这是我们家第一个离家赴京城和省城的人。不知当时丽江至北京需行多少天,但从我记事以来听说的是需走3个月;丽江到昆明是18天。那已是民国以后的事了。
高祖卒于云南县(今祥云县)教谕任上,因造福于当地,被传成了当地的城隍。
人回不了家,只有灵柩回到故里。
曾祖和富谷,曾被授振武将军衔,于光绪年间随名将杨玉科参加抗法战争,杨玉科阵亡,曾祖受重伤。杨玉科反被诬陷、籍没家财。曾祖为其赴京告状。延京三年,终得平反。后奉命主持督修杨武愍公(杨玉科)祠,劳伤并发,殁于大理。曾祖生前多次离家远赴云龙州、滇桂边境、昆明、北京、大理等地,保家卫国,伸张正义,鞠躬尽瘁,殁于异乡,最终仍以灵柩还乡,魂归故里。
祖父和积贤,清末丽江杰出的教育革新家,丽江府中学堂(今丽江市一中的前身)及云南省第一张白话报——《丽江白话报》的主要创办人。曾任丽江府中学堂、丽江府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及丽江白话报社社长。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因业绩卓着,早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省学院就推举祖父赴欧留学,然因他致力于家乡办学事宜,毅然放弃了此一难得的机会。凭着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祖父担起了办学兼办报的重任,“昼则坐镇学堂,夜则谋划报纸出刊事,累月未归家”,终因积劳成疾,37岁即辞世。对我们和家人来说,祖父是上述三代人中唯一一位“生于斯,死于斯”的“守家”者。往返于百岁坊与中学堂之间,可能是祖父一生最频繁的“离家”与“回家”了。
到了我父亲这一代,计四子一女。虽为名门后代,然因父母早逝(祖母亦只活到46岁),家道中落,历尽艰辛。除已成年的大伯迁往石鼓定居外,其余四兄妹先后到了广州、昆明谋事。为了生计,老家、故乡只能是他们的梦境。除二伯父如愿以偿、回乡定居外,三伯父及我父亲,皆客死异乡。听说他们生前唯一的愿望是此生能回家看看。然而,回家的路,对他们来讲多么漫长、多么渺茫啊!
我们这一代,父辈四弟兄共有七个子女。我是独生女,又是排行最小者。除了大堂姐、小堂兄早逝于家乡外,其余全在外谋生。至今除我一人外,都已客死异乡!1988年春,我赴台奔丧时,与二堂姐、大堂哥相聚。他们一直保持着家乡的风俗习惯,在一起还不时讲讲纳西话。他们最怀念的是故乡!问得最多的,是家乡的故地、亲友、小吃;讲得最多的,是在家乡的趣事;最动感情的,是期盼在有生之年能回家看看。大哥如愿以偿,数次返乡省亲,还穿着纳西服装留影。
而二姐,因健康原因,终不能如愿,只有数次让姐夫和侄子代她回家。最后,他们都已长眠在异乡的土地上。二堂哥16岁离家,80多岁了,还能讲一口较流利的纳西话。在昭通工作了大半辈子,晚年回了一趟家,最后仍逝于昭通。小堂姐参加边纵,在严酷的战争中经历了战火的洗礼,20岁即病逝于保山。她的战友们在胜利后大都返回故乡,她却留在了异乡,葬在当地应龙池风景区,因搬迁,至今连坟墓也不知在何处!
我们家五代人,无论男女、无论婿媳,大多数都归宿于他乡,遥望故乡而不得归!回家的路,好漫长,好漫长……
现在来谈谈我自己。我出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刚满周岁,父亲即随堂伯父入滇军上了抗日前线。母亲带着我从昆明回到了在石鼓谋生的外婆身边。直到12岁,才回到老家百岁坊。但回老家的机会很多,凡要去参加老家的红白事、购物及办其他事,外婆或母亲都要把我带上。所以从石鼓到古城老家的这条路,记忆很深。那时,七十多里的山路,要走两个半天。在我六七岁以前是捆在马背上行路的。从下海洛到沙坝这一临江路段,是条又弯又窄的茶马古道,最窄之处,仅能单马而过。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滚滚江流,马蹄踏在已被岁月磨光的石板路上,常常滑倒,前腿跪地,几乎要滚进江中,吓得我直叫。如今回想起来,都还有点不寒而栗!这还不算,马爬陡峭的冷水沟坡及雄古坡,得不断地绕着走“之”字形的路,忽上忽下,忽快忽慢,马累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气。而我的双脚则疼得发胀。待到住地“打野”或住店,被大人抱下马时,双脚已麻木得站不起来。
8岁以后,我就跟着大人们爬山下坡,用双脚丈量这条回家的路了。当时一般在街子天(石鼓三、六、九为街天)下午启程,走过江边小路,爬上冷水沟坡时,已累得两脚酸软、满身大汗。在大人们边聊边哄、边夸边逗下,好不容易到了雄古住店时,已是天黑时分。脚已磨出了水泡,浑身累得像散了架。母亲让我用热水泡过脚,然后用盐或酒帮我擦脚板,说这样可以消劳解乏。草草吃过晚饭,大家围着火塘,以木为枕,以板为床,盖上床粗毯,横七竖八地睡觉了。外面狂风呼啸,阵阵狼嚎从不远处传来,我在恐怖和疲劳中进入梦乡。第二天鸡叫头遍,我在恍恍惚惚中被大人们叫醒。吃点干粑粑,摸黑爬上雄古坡。不能说话,不能点火把,只有人们的喘气声打破着这寂静而又几分恐怖的氛围。因为在雄古坡的“四间湾”一带,是强盗们常出没的地方。过了这一危险地带,又下到“尔刷洛”。
这是一条狭长的深山沟,一到冬天,沟底箐里结成几尺厚的冰块,用石头砸也砸不烂,人被冻得脸耳麻木。上了坡,过“补市洛”,就算平安到“平地”了。接着穿过拉市坝,翻过黄山哨,终于到了丽江坝。过茨满,经“钏堆”、“午托”,爬上狮子山顶,首先进入眼帘的,是老家花园里那棵高大的柿子树。见到它,就像见到了家,高兴得直叫“雅阁嘞吐色!”(“又回到家了!”)——这就是儿时回家的感觉!
丽江解放后,我随母亲回老家定居。1956年上大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远行。由丽江到昆明,三天车程。再坐小火车到沾益,换乘代客车的货车,经贵州盘县、安顺、贵阳、遵义、桐梓,进入四川綦江,到达重庆南岸海棠溪,汽车轮渡到朝天门码头,再上两路口转至北碚。记得约花了七天时间。沿途领略了壮观的黄果树瀑布,从门缝中瞻仰了遵义会议地址,亲历了娄山关惊险的“七十二道弯”。在那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祖国大好河山的壮美,激动之心、爱国之情,油然而生。然而离家越来越远了,也平添了几多惆怅。乃至到了綦江之夜,我竟蒙着被子偷偷哭了起来。
到了西南师范大学,校友们热情地把我迎进美丽的校园:掩映在绿树丛中错落有致、宽敞明亮的教室,别致新颖的桃园、李园、杏园、梅园宿舍,名师荟萃的教师队伍,在当时的西南诸大学中,算是佼佼者之一。能在这样的大学读书,我是幸运的。然而,故乡,古城,老家,石鼓仍使我魂牵梦绕。唯一的愿望是好好读书,毕业后回家,报效乡梓、报效民族。我以品学兼优的成果,完成了四年的大学学习。遗憾的是我被留校任教,回不了故乡。留校,对多少人来讲,是多么令人向往的工作,可我却感到失望。从此,“不安心工作”成了我鉴定表上抹不去的评语。
第一次回乡,是在我离家六年之后。因有身孕,当时坐的是苏式小型飞机,24个座位,一张机票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飞机颠簸得很厉害。尤其是到了贵州威宁上空,气流波动特大,飞机忽上忽下几百米,全体乘客吐得一塌糊涂!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能闻点油腥味都是一种奢望。但在下机后机场免费赠送每位乘客一碗红烧肘子面时,因晕机太厉害,竟没有一个人吃下这碗面!从此我成了一个乘机恐惧者。直到20多年后,才敢再次尝试坐飞机。
从昆明到丽江,有三天车程,是粗糙的土公路加一段段弹石路。一到住宿地下车,全身是一层厚厚的灰尘,犹如从水泥厂车间里走出来一般。累是累,苦是苦,但离家越来越近了,那种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特别是车行至剑川甸南山坡上时,玉龙山奇迹般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像见到了久别的母亲,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又见到玉龙山了!我又回到家了!”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6年前离开老家到重庆,一共花了10天的时间,离家越来越远,心里越来越想家。6年之后返乡,才4天就到家了。久别的游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看惯了重庆的雨雾,领教了重庆的炙热之后,倍感故乡的天特别蓝,云特别白,水特别清,地特别绿!听惯了川东的方言之后,又听到了熟悉的纳西话,倍感亲切,倍感兴奋,倍感幸福!更坚定了不再离开老家、把自己的所学回报家乡的决心。
本来回家生小孩,为的是创造条件回故乡工作。母亲一人在家无依无靠,孩子又小,需要照料,按当时的户口政策,这是最好的理由。可不巧的是正碰上“干部冻结”,回家的愿望又泡了汤!就这样,在“一切服从组织需要”的年代,我又回到了山城重庆,心儿却留在了家乡!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举家返滇。虽只到了滇池之滨,但随着新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进程,回乡的路程不断缩短。特别是高等级公路、机场的建成,陆路一天即可到家,空中飞行,只需45分钟,回家犹如当年从城里到乡下,便捷得多。更主要的是,可以随时回家开展课题研究,把家乡的文化推介向全国、推介向世界,为纳西学的研究和纳西文化的弘扬尽点绵薄之力。这是此生最愉快、最欣慰之事!
我们夫妇都是地道的纳西人。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的民族。这种与生俱来、难以割舍的情结,潜移默化地濡染了我们的子女乃至孙辈们。虽然生长在他乡,成长在异文化圈中,但纳西人的根骨、纳西人的血脉、纳西人的文化、纳西人的性格,让他们有一种血浓于水的情感!他们以纳西人而自豪!从而也形成了一种报效家乡的自觉性和责任感。
儿子幼时曾与我母亲在家乡生活了四年,能说一口较流利的纳西话,对故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虽然在异乡长大成人,但故乡的亲人、小伙伴、儿时趣事常挂于口,一讲到丽江,就深情无限。只要回乡,他都要一个人摸到老屋看看,尽管屋已易人,但他却搜寻到了童年的记忆。至今他的车子里回响着肖煜光的纳西流行曲,每到激动处,还会来个“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说他要回到故乡生活,后半生要在丽江度过!
女儿在她的《我的纳西情结》一文中对纳西、对故乡的感情,有过发自心底的叙述,在此不再赘述。现在,她正在故乡主持一项引进的文化产业项目,频繁往返于昆明和丽江之间,实现着回报家乡的愿望。而昆明到丽江、丽江到昆明,犹如我当年往返于家和学校之间那样便捷。
我的孙子对回家的表达,就是一到假期,只要一有机会,就要领着他的朋友们到丽江。即使只有他一个人,也会走到古城的一些小巷慢慢地品味、领略,把心儿贴近、再贴近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故乡和乡亲们。
回家之路,从我的祖辈到我的儿孙们,一代代不停地走着,走着。有形的路——时空距离越来越缩短,而无形的路——心路历程则将越来越长,无限延伸……
古城记忆
杨福泉
少年眼中的纳西人
我出生于1955年9月17日,属羊。我在22岁考入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丽江。我的童年、少年和不少青春的岁月是在这个处于文化巨变的纳西古王国的土地上度过的。
纳西民间文化对我的影响在童年就开始了。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懂很多民间故事的人。他们常常给我和弟妹讲故事。像那机智的姑娘用火红的烙铁杀死吃人的鬼婆,鬼婆在树下化作荨麻的故事;一个妇人生下一只怪手,这只怪手最后差一丁点捞出了金沙江中神秘的金钟的故事;纳西族火把节来历的故事,金沙江姑娘和玉龙山老翁的故事,等等。
除了祖父母讲的故事,我还从古城的老人们那里听到了很多民间故事。我小时候,每天晚饭后,常与小伙伴到四方街玩耍。古城的一些老人在晚饭后也不约而同地来到四方街,在北面店铺前成一排坐下,慢慢从怀中掏出各种各样的小酒瓶,边呷边说古道今,讲的多是地方掌故和民间故事,有时还互相争论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