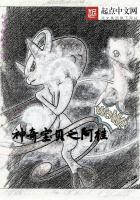蒙冤与平反
1951年,在社会大变革时期,75岁的仁和昌创始人赖耀彩,被抓被斗,说他剥削和压迫人民。性情耿直的他说,我没有剥削压迫人,而是一辈子修桥铺路,日晒雨淋地去做好事、善事。因这个矮老头太顽固不化了,便被关在铁笼里,铁笼底还有铁刺,让他不打自倒。
年纪一大把的赖耀彩,被折磨得支持不住了,倒在宠中铁刺上,快不行了,家里人便把蓬头垢面、胡子拉碴,一身伤痕的他保释回家。第二天他便悄悄地离开了人世。那是1952年,穷松松的家里人只好将尸骨草草收殓,匆匆抬到金虹山坟地,随便掩埋了。
但是历史没有忘记家有几十万银圆而修桥铺路,专门行善积德的人,自从纳西族女作家以“修桥铺路益乡里”为题记述仁和昌赖耀彩的事迹文章于1984年在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民族文化》第四期发表后,赖耀彩的事迹在《云南日报》、《春城晚报》、《丽江日报》、《丽江文史资料》、《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纳西族人物简志》、丽江社区网站等媒体,争先恐后地记述和传播着,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美德一个富得流油的商家老板,却身着布衲褂子,脚穿露趾头的草鞋,满手老茧地与民工打成一片,顶烈日冒风雨,拿自家的资金修了一座又一座铁索桥,自告奋勇地与古城人民一道克服了老天降给丽江的一次又一次灾难……这样的人物,在物欲横流,讲求享受的今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仁和昌赖耀彩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的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弘扬的。
仁和昌的继任经理赖敬庵,凭借仁和昌在地方上的影响,竭尽全力为丽江的解放事业带头捐献了不少的黄金,为解决当时军政费用的支出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在解放初期是丽江地下“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丽江县财务委员会主任,丽江县人民政府财务科长。“守口如瓶”(王丕震语)的他,没有因功自居,也不会以功自居,一直以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是顺应历史潮流,没有他,丽江照样解放。
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1951年他被以旧县参议员、商会理事长为“罪名”,抓去判了五年徒刑,押到邓川铅厂劳改。没收了仁和昌的房产和财物,便提前释放回家。他背着个空篮子,回到分给他的一家五口人住的三间房子的家中。
从此凤凰拔毛不如鸡的他厄运加厄运,在建筑队做泥水工,拌泥巴,拌沙灰……20世纪60年代,年过花甲的他随大女婿王运隆(高中生),遣送下放到金沙江边的武侯山村,在饥寒交迫被“改造”了七年,之后,经过要求才准迁回丽江古城,以74岁的高龄去光义街基建队做小工,用手锤打混凝土原料公分石,直到将近耄耋之年的77岁。
1984年,经过赖敬庵书面申诉,他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给予离休干部的待遇,并任丽江县政协委员。时年81岁,沉默寡言的他,禁不住激动的心情,拿出青少年时喜爱阅读中外名着、诗词歌赋的“功底”,开始吟诗作对,抒发自己的感情,歌颂大好春光。用半文半白的语言撰写了《丽江工商业资料》、《赖耀彩事略》、《我的自述》等史料,整理并油印了丽江赖氏家谱,给后人留下真实可靠的资料。
1991年,仁和昌的经理赖敬庵走完88年的坎坷人生,在古城土木瓦房里,在笔者和笔者的岳父岳母(赖敬庵的大女儿)眼前悄悄地病逝。没有追悼会,也没人致悼词,他的灵柩被送到了据说是块好墓地的赖家坟安葬。
简短结语
仁和昌商号在历史长河中只存在了四五十年,但它在丽江和藏区树立了一个高大的丰碑,它是奇绝多姿的玉龙大雪山养育的结果,是丽江纳西人的骄傲,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骄傲!今天,仁和昌修建的德钦溜筒江铁索桥已经被水泥桥代替,但丽江梓里金龙桥和石鼓铁虹桥却依然存在,二者同为文物保护单位,甚至是国家级的保护单位。记住丽江大商家仁和昌,不管大老板还是小平民,可以感悟人生和怎样做人!
昔日的丽江市场
和汝恭
六七十年前,来到丽江的外籍商人很少,纳西族的老百姓,懂汉语的也寥寥无几。会做买卖者更是凤毛麟角,很难找到,他们只知出售粮食及农副产品,以卖得的现钱又去买生活用品。
那时市场上使用的货币,为方孔铜制钱。制钱有两种用法,一种称老钱,一文说成两文;一种称足钱,按实际计算。丽江属使用老钱的地方。47文,称为“九四”钱,48文称为“九六”钱,49文称“九八”钱,50文称为“满钱”。一般“满钱”和“九八”钱最少使用,用“九四”、“九六”的时候多。“九四”改用“九六”,或“九六”又改用“九四”,改用开始那天,由县衙门传锣,大声喊叫:“县长的命令,从今天起,使用九钱!”喊一声敲锣三下,从街头走到街尾。如有人已在敲锣之前成交买卖的,他们言定:即碰到传锣改用,彼此退钱或找补。传锣后他们讲信用,该补的补,该退的退,不兴扯皮争吵。
外地来丽江做生意的商人,最初为大理人。他们租房在四方街南侧的现云阁,丽江对大理叫“见罗”,所以喊现云阁为见罗个。个是指巷。他们资本较多,生意也好,如遇地方上派款,他们一次代为支付,不要居民摊派款。往后几年,大研镇人慢慢向他们学习,进一步与他们竞争,大理人的生意萎缩,先后撤号回去。
此时丽江妇女已经学得一套做买卖的本领,就在现云阁开起杂货店来。如盐店、马料店以及火腿、腊肉、酥油等铺子,生意慢慢发展,跑鹤庆城街(狗街、龙街、七天街)的人也有了。跑城街的贩来大宗棉布、茶叶及杂货,不要求左手交钱右手取货,回丽江那天下午前可先取货,等到下一街子的晚上才付货款。安排得好,不要资本也可以贸易得利。
这以后,藏族商人也到丽江做贸易。永宁吕喜商人也来丽江做贸易。藏商驮来大宗皮毛山货药材。吕喜商驮来植物油(用羊皮口袋装)、腊肉、腊油。丽江妇女们为了生意买卖,不能不学会藏语。吕喜商食宿在主顾家。她们学会了几句生硬的藏话,掺杂纳西语与他们交谈。至于汉语,由于永胜马帮天天到丽江卖米、席子、鸭蛋、土碱等杂货,早已学会了,但还混进一些纳西语言。这时藏人来丽江的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丽江开设藏商堆店的也有好几家,一般人对藏店称为蛮店。丽江双石桥一带的人,已经能说流畅的藏语。当时开蛮店的收益非常大。
藏商的规矩是所驮来的货物,一概先交予店主(乃聪),可以介绍出售。老板(聪本)只作为成盘的决定人。要买的货,也由店主介绍购进。不论卖出买进,一切按照货款数字给付佣金(藏语称“八赠”,读Z)。但店主要负责:①保证货款如数收清;②鉴别货品的真伪;③买进商品的搭配,如普洱茶十驮,要搭配原山茶(猛库老叶子茶)一驮。原山茶乃地道货,味美醇香,活佛、高僧、贵族爱吃。
藏商来丽江投宿那天,店主要以大瓶酒(自己动手倒吃)大块肉及鸡蛋面条热忱款待。赶马人(劳多)、打杂人也全数一起招待,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第二天各自吃自己的糌粑(炒面)、酥油茶。其他人也各到山坡坟坝放牧打野去了。
堆店的睡床,不宜搭成高铺,最好接近楼板或地面,床边要烧一塘火,以便盘腿坐在床上,一面念经,一面倒茶或温酒下糌粑吃。
店主要注意客人启程回去那天,切不可打扫他们的住房与睡床。因为他们临行之前,大门外烧起天香。出门动步时,一面口中念经,一面起步,这是一种严格的规矩。遵守了规矩,下次来丽江,一直来到原店,宾至如归。倘若店主只图清洁,客人刚走,马上洒水扫地,他们知道了,下次再也不来了。遇见原主人,也就十分冷淡了。
藏商驮来的货物,有大量的皮子、细羊毛,还有山货、药材。如麝香、熊胆、虫草、贝母等,都是些名贵的出口俏货。他们买的为大宗茶、糖、粉丝等。当年丽江市场的繁荣,主要与藏商的贸易有关。
丽江古城四方街,为丽江贸易中心。那里全是露天摊,而交易形形色色。有菜场,有卖红糖者,有卖麻布者。卖菜人全是妇女,没有坐着的,个个都站着卖。
麻布生意最好,应接不暇。因纳西妇女的围腰,都用麻布缝制,只是做客,参加喜事及赛会时,才换穿蓝色的布围腰。麻布尽是白色,品种不胜枚举,其中最讲究的为“新妇私纺麻布”。这种麻布,从洗煮麻皮工序起,格外加工。纺纱务求均匀细致,织布的纬线里,织入少许红绿丝线以及火草线。麻布里加入火草线,柔软可爱,但费工、费时、价高。为新妇婚后第一匹织物。多数买者作为赠送礼品。
四方街菜场,有新鲜菜,有豆腐、豆芽、(黄豆、绿豆)、粉丝等。交易时不用秤称,卖粉丝与豆芽,有抢抓规矩。盛东西的是一种竹编的只比手掌大点的平底小筲箕。讲好价值,钱货交接后,买主撒开五指;拼命去抓卖主篮里的东西。
卖主只劝少抓些,任由她抓去。有人说,其原因是清政府的农业税,均折成钱,不收实物,粮价过于廉贱,而找几文现钱极其困难。所以卖东西的人认为,只要东西变为现钱,货物损失一点,不必可惜。
四方街旁的现云阁街口,有卖炒面的,因藏商喜吃炒面。又丽江多产麦,少产米,故有专业的磨面户。此外有屠户行、钉钉行。这两个行业,只有由本行业的人世袭独占,别人不得染指。四方街尾有卖草鞋巷,由白族妇女自编自卖,草鞋供不应求。买者一买就是10双20双,最忌讳5双。说王瘟神是五尊,故五双不吉利。又有个卖鸡巷,在现云阁北面,当时老百姓有节约之风,少有人买吃,常有一篮篮卖不掉背回家去者。
屠户不需缴屠宰税,占领着四方街一段摊位。唯祭孔的春秋二祭日期(每逢“丁”)的牺牲,要由屠户搞好送去,不给钱。牛(太牢)羊(少牢)则由牛羊汤锅户弄成牺牲送去,也不给钱,也不收屠宰税。野味祭品,由丽江雄古里的猎户送去,猎户不需缴农业税。
四方街有人专设簸箕摊,凡卖米、糯米者,米要倒在簸箕里,她先问卖者有几斗几升,问后由她们主持卖出量到最后,如果米多出卖米人说的数字,多出部分全归守簸箕人所有。这种喧宾夺主,不容正主管业的不合理行为,料想这里才会有。而守簸箕的妇女,不知耻地自夸:收田租的,一年只收一次,我们则一年可收三百六十次。有人说,卖主为什么不会到别处去卖呢?其实人们只习惯到四方街做买卖,如到别处卖,很难卖出去。还有什么升子大啦小啦地争执,何况多出的米,是由守簸箕的骗术得来的。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见怪不怪了。
四方街人来人往,丢弃的烂菜叶、破草鞋、果皮残渣到处都是,再加上当时全街附近找不到一个公共厕所,卖菜妇女,怀抱奶儿,看守菜篮,一时碰到,忍无可忍时,顾不得一切,蹲下撒尿。一到热天,臭气熏蒸,令人欲呕。因此政府规定,每十天冲洗街子一次,派轻刑犯人来清扫。洗街并不困难,四方街子,高枕着一条大河,只需以桌凳木板在桥边一堵,河水马上冲刷下来,再用扫帚略微一扫,街子便洗好了。洗街那天,特许洗街犯人可向屠户讨一小块肉,准许水果摊上顺手抓一两个,见蔬菜也抓他一把,习以为常。
春节期间,妇女煮卖白野薯,纳西人称“补勒”,与红糖同嚼,很好吃。这些小生意,极为兴隆,可新年一过,就没人卖了。
二战时期的丽江“工合”
李耀煌
一、中国“工合”的诞生
“工合”,对今天70岁以下的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在抗日烽火然遍神州大地的年代,三角形、黄底红字的“工合”标识曾经遍布于从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从西部边陲到东南沿海的广袤国土……
不知道有多少汉语词汇曾被其他国度的语言所化用,“工合”是其中一个。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工合”(Gongho),已改为美国语言的一部分——它是美国字典中的一个词条,其意为团结、合作、勇敢、开拓。
这些文字有足够的理由让人蓦然神情专注,去探究这段浩茫宏大、充满硝烟与烈焰的历史。这是我们不该忘记的:工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或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的简称。
由此知道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正当中华民族痛苦地承受日本帝国的铁蹄践踏之灾时,两个外国人在上海租界的一幢高楼屋顶,凭虚眺望布满疮痍的大地。此刻,黄浦江上空灰暗而破败的凄风,吹拂起两个他乡远游者真切的忧思与义愤——中国人民友好而诚挚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与路易·艾黎,就这样在战时中国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在创建工合运动前的最后一幅肖像。正是在这可以高瞻远方的屋顶上,他们决定了为重建凋零破落的中国民族工业而必须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这一时期,中国一半以上的民族工业毁于战火,埃德加·斯诺与路易·艾黎因此向全中国发出倡议:“让中国人自愿组织起来,成立一切归合作者所有、自选领导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工业生产合作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