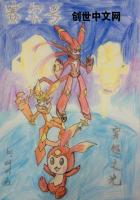“你退休再剩几年了,可我才三十多,还有好多年呢。总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吧。这样不明不白地下去,和瞎子骑驴差不多,说不定哪天就掉到沟里了。”向东嘟嘟囔囔地说,“再说抓赌博也有问题,介头所去年过年抓了一伙打麻将的,罚了钱,可后来张县长出面了,说人家几个人是亲戚,过年在一起玩玩有什么吗?最后让所里把钱给退了。你想,这《治安条例》中也没说是亲戚就可在一块赌吧?还有,上半年夫妻看黄碟的事,听说这名干警已被调离公安系统了,可按法律上规定所有人都不准看黄碟,夫妻既然是公民,就应该在禁止之列。可后来倒霉的还不是那个干警?你说这世道成什么样了?还有,现在是只讲证据,不讲个人口供,可娼身上又没写着字,你明知道是娼,天天在你面前招摇,一个一个耀武扬威的,你干着急就是没法抓。唉,这警察是越来越难当了。”
这时大亮已睡熟了,呼噜一声接一声。
大亮的呼噜声和这些念头折腾得折向东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起床洗了脸,向东和大亮就到了队部院里。发现院里多了一辆救护车,还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他一问古丽才知道,所长和其他几个人昨晚根本没在这儿住,而是直接回派出所了,今天就喊了镇卫生所的人,要验血,做最坏打算,通过DNA确定歹徒。听到这话,向东就有一种失落感,心灰意冷,觉得一些东西正在离自己远去,同时觉得又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正在向他靠近。所长显然已对自己不信任了,以往这些事都要和他商量的,但现在,却是在他睡梦中不知不觉进行的。
几个人吃完饭,支书就开了村里的喇叭,点名喊叫昨晚确定的十一个人到队部来。一会儿就来了一些人,一个个土眉土眼的,脸拉得老长,满脸的不高兴。支书让抽血,没有一个人肯,都沉默着不说话。其中一个二杆子和支书大声吵了起来,问:“凭什么抽我的血,而不抽村里其他人的血?”支书就说是所长定的,他是在执行命令而已,要说就跟所长去说。那人说:“所长,所长,有什么?你倒是解释解释,凭什么我平白无故就成罪犯了?”大亮听到这儿,就往前冲,说:“破案需要抽谁的就抽谁的。”这时呼啦一下子,十一个人一哄都围住了大亮,一起乱嚷起来,大亮一见这阵势,就职业性地从腰中摸铐子。这时,所长来了,说:“除过妇女,除过老人与孩子,村里的人每个都存在嫌疑,因为占用的时间长,决定分批抽,其他的人到下午再抽,上午时间包括村干部都要抽的。”
于是大家就嚷了起来:“那就让村干部先抽嘛。”
所长说:“行,村委会是村里的一级组织,就让他们带这个头。谁拒绝抽,就说明谁有问题。”这个话说完,崔支书和几个村干部就傻了眼,但是又没得话说,只好一个个脱棉袄,挽袖子,抹胳膊,让镇上的医生抽起血来。
大约用了两个钟头,抽了十五个人的血,血被抽进专用器皿里,然后在瓶子外边贴上了每个人的名字。
一大堆人都阴沉着脸,一个个都不吭声。所长给每人发了一支烟,然后夹了包上了车。
向东他们第二次离开了村子。
折向东一回到城里就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有个记者明察暗访将他们此次抓捕强奸犯的案子在报纸上发了花边报道,接着这个报道被其他报纸转载了。很快人们都知道了,都把破案中民警让受辱妇女再次受辱当成了笑话,四处传播,并且这件事大有蔓延之势。县上领导知道后,高度重视,将公安局长收拾了一顿,于是公安局长叫来了黄所长,将他骂了一顿,并要他一是堵住记者的嘴,二是限期破案,想来个快刀斩乱麻,难怪黄所长这两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
世上的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冥冥之中仿佛总有个跟向东过不去的神似的,注定了这件事情根本不会就这么简单地结束。
一晃一个月就过去了,就在所有人都乐观地等待着鉴定结果出来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却从省上通过传真传了回来。报告显示:田翠花的内裤及毛巾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精斑,A种与B种,一个多一个少,一种大面积分布,一种零乱地洒落,一种分布有规模,一种散乱,同时送去的十五个男人的血型竟然没有一个与精斑是一致的。这个消息使这些乐观等待的干警一下子懵了。不可能吧,怎么会这样?精斑竟然会有两种?那就是说那一夜田翠花与两个男人发生了关系,那么这到底会是谁的呢?整个事件忽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对于折向东来说,这句老话再次得到了验证。纸箱厂厂长吴发喜这个混蛋的事情终究被她老婆知道了,老婆大吵了一顿,给他的脸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疤痕。撕开了脸面这一层,吴发喜索性不管不顾起来,和小燕直接住到了一块。并且他一不做二不休,到处扬言,自己在派出所受到了所长与折向东刑讯逼供才不得不承认嫖娼,不得不签字的,还有派出所罚自己款开的是收款收据等。小道消息传来,他正在找人写材料,要告双良派出所的状了。
胡局长知道这些情况后,将折向东与黄所长叫到办公室美美气气训了一顿:“你们这么多年的警察都是怎么当的,你们他妈怎么能想出这样损的着儿?有警察在身边农妇遭强奸啊,你们有脑子没有啊?脑子是用来戴帽子的,还是用来喂饭的?你到底是保护公民呀还是跟强奸犯是同伙呀?事情一桩接一桩,领导成天给你们擦屁股都擦不干净。”直训得折向东、黄所长恨不能头钻到地缝里去。
案子既然没有破,那么重新召开会议,研究新的对策,部署新的方案,采用新的破案方法是必然的。本周星期四上午公安局就此事召开扩大会议,把如何破这个案子摆在首要位置,重新成立田翠花强奸案专案组,因为是午夜发生的事,代号就变成“010”,指午夜十分的意思,由公安局局长任组长,县刑警大队直接负责办案,双良派出所全面配合。在这次会上,折向东被点名做了内部检查,局长最后讲话要以此为教训,并且流露出了要处分折向东的意思(但消息只限于内部)。
会议开到最后,就是确定新的思路。折向东和所长遭批后,大家的情绪都受了挫折,都沉默着不言不语,除双良派出所几个人外,其他人对这案子了解得不是很多,当然也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
然而就在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双良派出所干警青科却打破了沉默,发言了。他结合“010”案件说了三个问题。一是当初确定这个抓捕方案时,他也在场,他也有错误。当时他就意识到这个方案有问题,并立即向折副所长指出,建议向黄所长汇报,但折副所长没有表示。他自己的错误就在于对抓捕方案错误的严重性没有充分认识,当时也只是简单地提议,而没有坚持原则,导致了今天这样被动的局面,给公安系统的名誉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件事也表明了自己原则性不够强。二是具体案件发生后,他一直参加,他觉得破案的思路有问题,上一次经过几轮排查,原则上说是宁滥不漏,但在实际操作中,只怕扩大范围,招致负面影响,基本采取了宁缺不滥。破案视线被群众错误引导集中在了村干部身上,致使确定的十一名重点对象和四名村干部中没有嫌疑犯,错过了最好的抓捕机会,新一轮的做法他认为应该再扩大范围。
青科的话引起了局长极大的兴趣,局长说:“先说你对两种精斑怎么看?”
张青科停顿了一下说:“我觉得思路应该再开阔,我们应该相信科学,科学鉴定是没有错的,出现两种精液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第一夜第二夜强奸的人与第三夜的可能不是同一个人。‘010’案件中,虽然两个嫌犯都采用了同样的手段,扛着斧头,午夜时分翻窗子,但只能说明这两个人仅仅是采用了同一种手法,在两天的同一个时间作的案而已;另一种可能就是破案当天夜里有两个人同时与田翠花发生了性关系。”
“哦。”局长越听越来兴趣,“你继续说。反正都是自己人在一块,错也罢,对也罢,大家都不要外传,大家知道破案当然还是要靠证据的,不能靠推理。你就给咱说说最大的嫌犯可能是谁?”
青科得到了鼓励,便有恃无恐,不顾所长的白眼,也不顾向东的表情,自个儿侃侃而谈:“说点不成熟的看法,首先第一种,有两个人采用同一种方式强奸了田翠花,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两个歹徒的特征当然不一样,但田翠花因为第一夜受惊吓,辨别得不够清,误认为两个人是一个人。从事件本身来看,发生这事后,她将所有细节对邻居说了,就是那个和她一起报案的邻居,那么歹徒所采取的时间、方式就只有邻居和田翠花两人知道,所以当第三夜出现同一个场面,如果还有第二个人的话,最大的嫌疑犯应该就是田翠花的邻居王刚来。他采取了将计就计的策略,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当然这也仅是猜测而已。第二种就是在破案当夜田翠花两次遭强奸,一个人肯定是凶犯,另一个可能是……”
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望了一眼向东与黄所长,低声咕哝着:“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就停住了。
局长没听懂青科的话,就问:“你有什么就说。想到哪里说哪里了,这不是案子破不了吗?”
这样青科就非说不可了,他说:“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应该不避嫌地说,破案当夜所有跟田翠花接触的人都存在着嫌疑——包括我们自己人。”
这句话像一记重锤咚地敲在会场,坐在角落里的折向东,脑子嗡的一声,吓得冒出了一身冷汗。青科这个前年警校刚毕业的娃娃,他看似简单的话里却藏着很深的玄机。卑鄙,真是太卑鄙了,是典型的落井下石。本来他也在抓捕组的,可到如今他却将自己推得干干净净,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折向东与黄所长,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既然知道破案方法有问题,为什么当夜不明说呢?向东这才想起那一夜他所谓的母亲病了或许只是个借口,关键就是他已经意识到了破案方法的问题,是为了避免参与到这起案件中来而临阵脱逃。或者,那时他就已经算好这一切了。他又回想起,去年追捕逃犯时,青科走火打伤自己脚的事,现在想来,当时分成几个组,他所在的这一组先遇见了持枪的歹徒,青科又在最前面,是不是怕持枪的歹徒伤了自己才故意这样做的呢,真是好险恶的用心啊。想到这一切,向东再看青科,觉得戴着眼镜的青科活像圆睁着双眼、不断吐着信子的眼镜蛇,顿时不寒而栗。
真没想到,为了邀功,他竟然将对犯罪对象的怀疑直接转移到向东与大亮、小安子他们身上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听到这些话,折向东简直气炸了肺。
青科说到这里,黄所长腾地站起身来,打断了他的话,说:“破不了案或许思路不对,要开阔思路是对的,但像青科所说的,怀疑公安干警参与这起强奸案,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容忍的,况且那一晚上还留下了衣服、斧头等系列证据……”
这时,胡局长在空中挥了两下手,示意黄所长坐下。黄所长停住了话头,重又坐了下来,青科不作声。胡局长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青科的话只是一种推测,也开阔了我们的思路。这样,青科暂时先借调到局里来,就任专案组办公室副主任吧。”他咂了咂嘴唇,喝了一口水,说:“罪犯是狡猾的,但是再狡猾的狐狸也躲不过好猎手。这件事截至目前,没有进展,这说明我们的破案思路有问题。青科的话给了我们好多启示,虽然结果还未确定,但是他的思路非常好,现在不是讲共产党员先进性嘛,在破案上我们大家就要与时俱进。刚才黄所长也说了,不相信公安干警会干此类事,我也不相信,不过,如果公安上有败类,我们将从严从重打击,决不姑息养奸,决不允许有害群之马。这件事就到这里为止,散会后所有人都要严守纪律,不得透露今天开会的任何内容,谁透露了处理谁,绝不姑息。”
这天夜里,大亮做东,请小安子跟向东,三人喝了一场酒,喝着喝着就喝多了,大家就骂青科,说青科不是个好东西,怎么先前就没看出来呢。骂了一遍又一遍。大亮喝高了,索性当时就要跑到局长家里去,就要挽胳膊袖子验血,但被向东挡住了。最后三个人喝得昏天黑地的,哇哇吐得到处都是。从酒店回来的路上,已是午夜了,人高马大的折向东衣衫不整,伏在矮小的小安子肩上,他哭了,鼻子涎水抹了一脸,他拖长声音哭着喊道:“谁教教我啊,这他妈的警察该怎么当啊?”
街上没有行人,空荡荡的,路灯温柔地发着光,向东的哭腔干咣咣地在街上游荡。
此后一连几天折向东都没上班,也没出门。单位也没有人叫他干什么事,这个世界仿佛把他忘记了。折向东待在家里,面对着一个新的家,他发现这个世界对于他来说是越来越陌生了,陌生到他都不知道该如何走路,该如何睡觉,甚至有一个晚上他醒来的时候,他费尽心思都弄不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