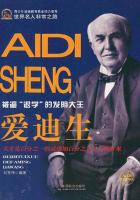一
祁乡长出得大门,门口空旷的地上正有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她们四个把一条腿叠架在空中,然后用另一条腿转着圈跌着拐拐,一边拍着手念儿歌:
二十三,灶王送上天,
二十四,扫屋子,
二十五,磨豆腐,
二十六,割块肉,
二十七,杀只鸡,
二十八,蒸枣花,
二十九,灌壶酒,
三十赶个小年集儿,
初一撅个尾巴乱作揖。
唱一段,这群女孩又把腿放下来,拍几下手,又开始重新叠,重新玩。祁乡长一时看得有趣,不禁就呆了。有一会儿,他不知怎么蓦地想到了自己的童年:临过年了,黄昏,一群男孩子在场里互相追打嬉闹,女孩子们则在一旁玩和这一样的游戏,叫编花篮。不过,那时的歌词可不是这样,而是“编,编,编花篮花篮里边有小孩小孩名字叫小兰坐下,起不来蹲下,起不来……”在这一时的恍惚中,祁乡长脑海里出现了一种温暖的情调,有了一种温馨之感。但这只是一瞬间的感觉,接着一下子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了。他呆呆地站着,脑海里用力捕捉着那一瞬微妙的感觉。
这时,他的衣角被人悄悄地扯了一下。
原来是文书小张来了,他站在祁乡长身旁喊了两声,见他没吭声,就扯了扯他的衣角:“祁乡长,祁乡长。”
祁乡长扭过头来,木然地看着小张,一时反应不过来。
“东西弄好啦,乡长。”文书小张左右看看没人,就将一张纸递给了他。祁乡长接过这张打印出来的纸,眯着眼睛看了半天,也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是条件反射似的向乡政府办公室走去。
办公室里,何副书记正在打电话,见乡长进来了,便挂了电话,走了。
祁乡长坐在老式的排椅上,静下心来看着手中的那张纸。那是一摆溜打出来的字,最上面是一行大写的黑体字:“林平乡拆迁户情况统计。”
祁乡长一边看,一边问小张:“都统计到了?”
“到了。”小张站着说,接着凑了过来,“这十一户,平头老张的女子跟喜来的儿子在外边上大学,韩平是咱何副书记的丈人,风林与根要是咱学校校长的亲戚,冯大脑的儿子去年也刚当了兵,听说要在部队提干哩。另外四家都好说,他们都有儿子或女儿在咱这七站八所里上班哩或雇着哩,就是最南边的韩胖子没有统计到,听人说,和咱县里的金县长是亲戚,论起来还大县长一辈,县长得管他叫阿舅哩。”
“嗯。”祁乡长嗯了一声,又逮住名单看了一下,对小张说,“这样,你把这些拆迁户和他们的亲戚都通知一下,让下午两点半开会。”
“那韩胖子呢?”
“你先不管,通知到就对了。对了,要尽快,时间要紧促。”
小张应了一声出去通知人了。
小张走了,祁乡长一人坐在老式排椅上。尽管是坐北向南的房子,但因为是冬日,日子短,故而到现在这时段,阳光只能从半窗上斜射进来。祁乡长将身子斜了斜,让阳光正好打在自己身上。他脑子里又想起了刚才在大门口的那种感觉,但琢磨来去,还就再也找不到那种温馨感。他索性闭了眼,可闭了眼的当儿,忽然觉得身上有一丝清冷,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他这才想到现在已是冬天了。便站起身来,到墙上翻着看了看日历:农历十月二十一,星期五。
是啊,时间真快,刚才门口的那些小朋友已在盼着过年了,可年这个概念在他祁乡长的意识里却是那样的遥远。
乡里每年放假都在腊月二十五以后哩,现在手头还有许多事要做,有许多硬仗要打啊。
下午的会开得非常沉闷,也非常顺利。除了韩胖子没到以外,其他的拆迁户和他们的亲戚都来了。
因为乡上的郑书记到党校学习去了,会议就由何副书记主持。会上,祁乡长就公路沿线的拆迁谈了几点意见,说,修路是市上的大事,公路要从本乡地盘过,道路要拓宽,要上柏油,这是好事,每一个干部与公民都应该给予支持,要拿出风格来,要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咱们乡沿路拆迁进度太慢,已受到了县上的批评,领导下了死命令,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这件硬任务拿下来。为此,乡上制定了一定的优惠政策,给每个拆迁户根据拆迁面积大小按比例在乡上新规划的农贸市场里划底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为了确保按期完成这件政治任务,乡上根据其他兄弟乡镇的做法,并结合实际定出以下制度措施,说明白了,就是实行拆迁承包制。
承包制,就是由乡上包括七站八所在内的所有和拆迁户有亲戚关系的干部职工承包具体的拆迁户,没有亲戚的,由乡上领导承包。一个包一户,必须在十月底前开始动工,十一月上旬全部拆迁完,否则,是领导的以工作不力上报县组织部,是干部的停发工资,将人员搁置起来。对于拆迁户中拒不执行的,有儿女当兵或上大学的将把家长的所作所为写成材料,盖上乡党委、政府公章,邮寄或派专人送到有关单位部门请求处理。同时也制定奖励措施,本月底前能完成拆迁任务的,乡上将奖励每户一千元钱。
话说完了,祁乡长就问大伙有什么意见没,大家都不吭声,一个个仿佛祁乡长要扒他家祖坟似的,耷拉着脸。
开完会,祁乡长给大家散了一轮烟,就回到了办公室。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暗想着,是人总是有所顾忌的,总会有疼处的,问题是谁能抓住这个疼处才算是真正的赢家,这一回,他祁乡长就抓住了。
这时,文书小张进来了,他给乡长倒了一杯水,斯斯文文地想说话又说不出的样子。
祁乡长不吭声。
小张斯文了再三,才开口说:“乡长,那韩胖子怎么办?”
听到这话,祁乡长奇怪地盯着小张:“谁让你问的?”
“是这样,院子里的人都没走,都在一起议论哩,说真要把韩胖子弄倒了才算有办法哩,把韩胖子弄不倒,其他人就都不拆。”这话其实是何副书记让小张问的,但小张此时不敢提何副书记的名字。
“你不要管了,你忙你的去吧。”祁乡长说。
“大家都说韩胖子不拆,他们也不拆。”小张又强调说。
“嗯。”祁乡长应了一声,陷入了沉思之中。
其实这一点道理祁乡长他是明白的,韩胖子仗着是县长的亲戚,不愿拆迁,目的就是想多要些钱,但赔偿标准乡上又做不了主。目前,他是所有一摊人中乡政府什么也卡不着的,儿子没当兵,也没上大学的,大儿子开车,二儿子和他爸生了一回气,父子俩人打了一架,过年后跑了,到现在还没回来。这些年,他自己和老伴开个小卖铺,生意还过得去,所以任你说死说活就是不拆。祁乡长一时也拿他没辙。
到下午的时候,祁乡长爱人来了。祁乡长爱人在另一个乡的中心小学教书,正是星期五,她一放学就来到了丈夫的单位。
祁乡长的爱人翠花原来有个好身材,是本乡里有名的美人,个子高挑,皮肤白皙。可这几年也许因为丈夫当了官、个人心情好的缘故吧,渐渐地富态起来了,越来越胖,从背后看她的腿像两根柱子似的,说话声音也粗、也大了,笑起来咔咔的。一进单位大门,一听声音,大伙就都知道乡长夫人来了。
祁乡长待在房子里一声不吭,心中依然想着拆迁这回事。翠花一进门看着祁乡长满脸的晦气,就问他怎么了。祁乡长不吭声,只是长长地放了一个屁。老婆没听清,说:“你有什么你就说,不用这么叽里咕噜的。”听着这话祁乡长满肚子的气就消了,笑出了声,就对她说了拆迁这个茬。
老婆一听就来了劲,大着嗓子说:“那有什么难的?韩胖子外甥是县长也得讲理不是?这是市里的项目,又是县上布置的工作,他不带头,谁带头?再说,他韩胖子是个什么东西?当年还占了明娃子好多地基呢,两个人为了这打得头破血流,被派出所关过几天呢。这回他再嚣张,就让派出所把他再关起来。”
听到老婆说这话,祁乡长就多了个心眼,问老婆:“你说他多占了明娃子的地基?”
老婆说:“可不是?是个瞎怂,有一年雨特别多,下了足有十多天,到处都是水,他家与明娃子家之间的院墙塌了,等天一晴,韩胖子就顺势把院墙往外移了不少,明娃子不愿意,两个人就打了一架,明娃子被打得头破血流,韩胖子被派出所关了几天。后来明娃子看看闹不过人家,就把这地方卖给公家,一家人到城里去了。这以后韩胖子就在这镇上得了个韩霸天的外号。”
“好好。”祁乡长说着就出去了,将老婆一个人扔在办公室。
老婆追出来说:“好个屁哩,有啥好哩,神经病似的。”
祁乡长出来就打电话给乡上的土地管理员郝老五,得知他正在一个村上下乡,祁乡长就打发司机开上车赶紧把郝老五接回来。
到了傍晚时分,郝老五就来了。祁乡长在大路上等着,他对气喘吁吁的郝老五说:“你坐上乡上的车,到县土地局去,给咱把韩胖子的地基具体年份、亩数等情况都弄清楚。”
郝老五听了这话,不明就里,呆呆地望着祁乡长。
祁乡长就说:“你看武打书不看?”
郝老五说:“看啊,金庸的武打书我都看完了。”
祁乡长说:“没有人天衣无缝,每个人身上都有短处,在武打书上叫命门吧,抠住了这个命门,他就全身都疼哩。重要的是你要首先找到这个命门。”
郝老五说:“我明白了,让我换一下衣服吧。”
车停在当路,两人相跟着往乡政府走,路上郝老五说:“乡长,你刚才说命门每个人身上都有,我看也不一定,我看你们身上就没有命门,起码在这个乡你是什么也不用怕的。”
恰好这时祁乡长心情也特好,就说:“也有怕的,只是你不知道。”
郝老五说:“怕领导,怕把官撤了。”
祁乡长一听,哈哈笑了,说:“这些,所有当官的都怕,这是共同的特点,其实官不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但每个人在具体的生活中还有怕的。比如说,现在我也怕啊。”
“怕什么?”
“呵呵,那就不告诉你了。”祁乡长其实现在脑子中是想说最怕的是老婆的大嗓门,但觉得开这玩笑有点不合适,就住了口。
“我知道了,你是怕韭菜吧?”
“什么韭菜?”祁乡长一时没反应过来。
“乡上让种的那些韭菜啊,我今个听说那些人要闹事哩,要上访哩。”郝老五一边说,一边瞅着祁乡长的脸。
生活中,人们有时往往宁愿喜欢一无所知的人,也不会喜欢自以为是的人。这个郝老五工作多少年没有被提拔,大概和这些自作聪明是相联系的。
果然,祁乡长听到这话,心情突然就糟透了,他沉下脸来:“什么韭菜,上访!你快点到县上去吧。”
“是。”郝老五加快步伐走了。
“坐班车去。”祁乡长说。
“我现在就骑摩托去。”郝老五为不明就里得罪了祁乡长而感到有些诚惶诚恐。
事情说怪也怪,就在郝老五说了韭菜的第二天中午时分,乡里就来了几辆拉韭菜的三轮车,停在了乡政府大门口,呈一字形排开。从三轮车上下来几位当地的农民,这些农民一个个脸冻得通红,浑身瑟缩着,有几个头上戴着个猴娃帽子,拉长了,将耳朵也全部遮了起来。
祁乡长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脸顿时就沉下来了。
事情还得从去年说起。去年县上领导到沿海去考察,瞅着一种新产品,叫独根红韭菜,这个东西丰产,并且给当地带来了丰厚的效益。县领导脑子一热就谈好了项目,给县上引进了一些,计划在全县种植。当时也有一些同志持不同意见,说怕将来销售成问题,可是县长耐心地给大家讲道理,说销售不了,只是没有成气候,就像我们当地的苹果,前些年太少了,就不值钱,卖不掉;这几年成了气候,每到秋季,外地的车就都来了。咱们县,川道里不适宜栽苹果,那么就多栽一些独根红韭菜,也算是独辟蹊径,给农民开了一条致富道。大家想想县长说的就是有道理。于是县上决议,给川道每个乡下达一百亩的独根红韭菜任务。祁乡长的乡大部分面积在塬上,川道里也有少量的地,但因为是县长包的点,这个乡就首当其冲,下达了150亩任务。为了完成这任务,祁乡长想了许多办法,乡上又给每亩补贴了150元钱,结果到最后也没完成150亩,满打满算只有50亩的样子。这些独根红韭菜,在县城里刚上市时掀起了一阵狂热,为菜农带来了一定的收益,但是不知什么时候,所有的人议论说不合口味,说吃上和草似的,就没人买了,市场就淡了下来。现在到冬季了,最后一茬的韭菜长得生动茂盛,总不能眼看着都烂在地里吧?卖不了,这些农民就拉着韭菜来找他祁乡长了。
其实这事他们都找过几回祁乡长了,只是祁乡长也干瞪眼没办法,什么都得靠市场,菜不适合口味,当地人当然不买你的账,你再大的官有个屁用。为了这,祁乡长还和当初引进的那个地方联系过,人家倒是愿意低价收购,可这一趟拉过去运费比成本还要高哩。所以祁乡长也是干着急没办法。
几个农民走进院子,刚到祁乡长的门口,祁乡长就从门里出来了,于是一摊人就站在房门前说话。大伙你一句,我一句,意思反正是祁乡长你号召种的,销不了你总不能不管吧。其中一个说道:“祁乡长你要不管的话,我们就将这些东西拉到县政府院子去,全部倒在县长门口,反正是县里号召种的,看他县长怎么办。”
祁乡长本来态度低调,想和稀泥抹光墙,尽量给他们说好话,但听着这句要挟的话,不由得就来了气,说:“要倒,你们只管倒就好了,还来找我干什么?”
这是气话,也是真话。
这话说得几位农民面面相觑——这些农民也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并不想去闹事,只是韭菜长成了,又快到年跟前了,变不成钱,干着急。这时遇到祁乡长这句顶心窝子的话,几个农民顿时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