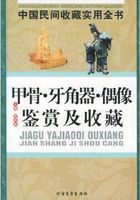这些年,丽如还力推出版了《醒木惊天连阔如》和《江湖丛谈》等书。
这些书,我都购读了,很受益。她在北京图书大厦、地坛书市、王府井新华书店的签售活动我都去了。每次看到读者、观众远排长龙的盛况,心里总是涌出一股为母校为丽如的自豪之情。
补说个小趣事:那天在中央台直播节目过程中,话赶话说到王玥波拜认丽如为义母事,主持人郭静调侃地问王玥波:“岳老师是你义母的校友,你怎么称呼岳老师?”这玥波张口就来:“叫舅舅呗,这不能差了辈儿啊。”您瞧瞧,做节目还得了个这么有出息的大外甥。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印象
亲切、平易、待人诚恳是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给我的印象。这源于:
一,自1979年起,她在长篇评书《岳飞传》中,用几十年的功夫,倾尽心力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我们“岳家门”的民族英雄岳飞的形象。为此,见到兰芳女士后,除肃然起敬外,当然更多的是亲切。二,在一次文化部为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召开的表彰会上,她不仅十分认真、专注地听了我的发言,而且还鼓励表扬了我,认为我的发言“有一定水平”。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得到曲艺行家的夸赞,一种亲切、平易之感油然而生。三,又一次,在民族宫剧院后台的楼道里,我遇到她,彼此问好之后,我请她在《中国曲艺史》扉页上签名留念,她没推脱、没婉拒,而是爽快地应允了。在签名时,她自谦地边写边说道:“我字写得不太好啊。”其诚恳的态度让人感动。
我和她的儿子、相声演员王玉相识。小王每次见到我,若在远处,一定主动笑着招手致意;若在近处,一定走上前来,热情握手,有时还聊上几句,全然没有名人之后莫名其妙的架子,很难得。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成立是一件大幸事
在我看来,2003年10月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的成立,是北京乃至全国相声界和曲艺界的一件大幸事。
说是“大幸事”,理由有三点:
相声俱乐部的成立——
给老百姓创造了一个听正经八百、高水平相声的好场所;
给全国相声演员提供了一个展示、交流、联谊的好平台;
为我国相声的存在、发展、繁荣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好基地。
十多年来,相声俱乐部已演出500多场,几乎场场爆满,观众达20多万。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优秀相声演员纷纷亮相,都把能在俱乐部舞台上表演看作是荣光的艺术经历。为了促进相声的发展,俱乐部还在青年演员的培养、新作品创作、组织相声专着出版、举办各种专场演出、开展各类研讨活动、深入基层做公益演出等方面,做了不少实实在在的事情。
我的结论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犹如一面高扬的旗帜,引领着全国相声人的前进;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路正、人正、活正,让我们看到相声健康发展的希望!
更令人欣喜的是,俱乐部刚成立时来自本地的中老年观众居多,而今,来自全市各处甚至全国各地的青壮年观众成了绝对主力,成了观众的主体;每当置身剧场之中,常常被场上散发的青春、敦厚之气所感染,令你联想到相声发展的美好前景……
十多年来,我从俱乐部获益多多,主席李金斗、秘书长宋德全及王玉不仅对我礼貌有加,而且给了我不少切实的帮助,对此,我将永铭于心。
最后,说点希望吧:我希望俱乐部再坚持、坚守几个“十年”,希望在坚持、坚守中创新、勇进,在创新、勇进中坚持、坚守,更好地发挥领军作用;我希望相声人对相声再敬畏一些、对前辈再谦逊一些、对同行再宽厚一些、对观众再尊重一些、对传统再细研一些、对创新再慎重一些……以上所言可能口气偏大一些、想法偏颇一些,但,这些,都是一位喜欢了一辈子相声的古稀老人的心语。
又:2014年,陕西青曲社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进京“赶考”。剧场演出火爆,颇受欢迎。我认为,因为演出文本的略显粗糙,很可能对他们日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负影响。
国家大剧院中的“小镜头”
2007年11月的一天,有机会在国家大剧院正式启用之前进行了参观。
七年多了,当时所见的三个“小镜头”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
镜头一:迎着大门长长的水下通道上,几位工人师傅正蹲在地上为收尾工程紧张忙碌着。可能蹲的时间太长了,也许是双腿有些毛病,只见一位师傅双腿一边不断地调整姿势和重心,似乎有些吃力,手里一边还干着活……
镜头二:几乎和观众席同样大小的歌剧场的舞台上,几位小伙子正在安装布景,只见他们来来回回地搬着、走着,还不时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据介绍,尽管大剧院舞台机械化程度是世界一流的,但搭景中的不少环节还需人工来完成。有谁知道,这一幕幕一场场逼真的“大制作”的背后,流有装台工人的多少汗水啊……
镜头三:厕所内洗漱室旁一位50多岁的男服务员,用抹布在不时地擦拭着池子边的水渍。也许见我是位老人,在我洗完手后,他向前紧走两步,要为我抻拉擦手用纸。我笑着说:“谢谢,谢谢。”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谢什么呀!”口音中分明带有河南的味道。我爱开玩笑,用河南腔问:“河南的?”他回答说:“河南的。”我略带感慨地说:“不容易啊!”他说:“不容易——没什么不容易——不容易也得干啊,孩子上着学呢!”听到这话,我有些慌乱,似无言以答,只好一边擦着手,一边有些漫不经心地说:“再见,再见。”
他也回应着“再见。”
走出厕所门口的一刹那,回头一望,发现他还在看着我……
人艺就是人艺
我有时看罢演出爱给人家提点建议。2010年看了于明加版的《蔡文姬》首演的当晚,我就这部戏的表演、读音、调度、灯光、音效等写了封建议信。
记得信送出去的第三天,我便收到该剧副导演唐烨女士打来的电话。她先热情地转达了导演苏民先生和剧组对我的谢意,然后说我的建议很中肯、提得很是地方,又说在当日排演前向剧组人员介绍了信的要点;最让我感动的是,第四幕的一场戏中的表演和舞台调度已依我的建议改了,而且当晚演出即以新改动的呈现给观众。唐烨副导演表示,诚如我在建议中所说,第四幕丞相曹操和蔡文姬对话的那场戏中,蔡文姬不应在靠近台中间位置的椅子上端坐,而应侧立一旁敬听曹操的问询——这样既合于礼数,又合乎人物身份。修改后表演顺畅了,看着也舒服了……
因为觉得唐导待人热情诚恳,我又就人艺风格、人艺演员队伍状况、话剧发展的前景、先锋话剧的地位等问题,向她一一做了请教,她的回答又坦诚又有思考力度,让我很受启发,十分受益。
记得焦菊隐大师曾说过,好戏是演员和观众共同创造的(大意)。《蔡文姬》剧组又一次实践了这个艺术理念。
人艺就是人艺。
并非赘言:
1.我的建议信是直送人艺传达室的。一位女工作人员热情地对我说,苏老年事已高,来剧院时间不定,想托请濮存昕转交给苏老。于是,这封信是经由“传达室人员——濮存昕——苏民先生——唐烨”顺序的,仅三天我便接到了反馈。能不让人感动吗?告诉你,存昕:经你手传递的泛着热的光,已传递给了我,让我感到亮亮的、暖暖的……
2.人艺建院甲子之庆前,我致信张和平院长(张和平任院长,是人艺的幸事),建议院庆之时,可否举办一个人艺60年节目单展,以回顾演出足迹、展示人艺的演出成就。张院长认为此议很好,将信转给人艺戏剧博物馆。不久,刘章春馆长热情地邀请我的藏友何大中先生和我到馆,不仅认真听了我们的想法,还展示了人艺节目单藏品,使我大开眼界。后剧院节目单展开展那天,刘馆长还特邀我们参加,使我又多了一次学习的机会。
同样的建议,我曾提给一个国家级话剧院,同样致信的是院长,但信寄后,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人艺就是人艺”吧。
蓝老谈“人艺风格”
2011年8月15日,我到首都剧场看莫斯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樱桃园》。开演前,我和其他观众一起正在大厅浏览着介绍演员的展板时,两位电视台的记者走过来表示要采访我。我摆手说:“还是采访年轻人吧,听听他们对话剧怎么看。”也真巧,就在这时,蓝天野先生走进了大厅。一见此景,我惊喜地说:“快,快去采访蓝老吧。”
在众多热情观众的簇拥中,蓝老回答了记者几个关于此次中俄话剧交流活动的问题。蓝老年近九旬,双鬓如霜,但答起话来声音洪亮,言简意赅,颇有见地。我当然不放过这难得的当面求教的机会,在蓝老回答罢记者最后一个问题后,我客气地请蓝老谈谈对北京人艺演艺风格的看法。
蓝老稍停了一下之后,侃侃而谈起来:“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么多年来,包括北京人艺的人,也包括不是北京人艺的人,都在那谈论一个问题: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艺风格是什么?到现在,很少有人能说清楚。有很多文章,有很多专门的着作,都在谈。但是,谁能说清楚北京人艺演出风格是什么?我觉得很难。
“我个人体会,从相反的方向来讲,北京人艺的演艺风格,它最不容忍的是一般化,是矫揉造作,是虚伪、虚假。正面的说法是什么呢?现实主义太大,我从来不说北京人艺的风格就是现实主义,她绝对不仅仅是现实主义。
我给你说,我们院长曹禺先生很早以前就说过一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我觉得现实主义的东西不可能那么‘现实’。你说这句话对不对?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理解。曹禺先生并没有否定现实主义;但是呢,他的思路里边,他的创作里边,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我的这些话,供大家探讨。”(据录音整理)早在1947年蓝老就和焦菊隐先生合作。建国后,蓝老作为人艺第一代艺术家,亲历了人艺建院六十多年走过的风雨历程。六十多年来,蓝老导和演了数十部话剧,成功地塑造了秦二爷、董祀、呼韩邪单于、黄仿吾等艺术形象。依我看,蓝老是人艺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
我和叫卖声艺术
叫卖声,也称市声、货声,乃至吆喝声。不过,这些都是借代称法,推敲起来,不甚准确。叫卖声,是较普遍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称法。北京叫卖声是带有北京民俗文化、市井文化特色的一道街市胡同的声音风景线。老北京叫卖声,据《燕市货声》(清光绪)载有400多种;新北京叫卖声,据我十多年的采录收集,有80多种。老北京叫卖声已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北京叫卖声作为艺术呈现,当始于人艺的《叫卖组歌》,之后显于臧鸿先生,之后更显于老北京叫卖声艺术团。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我,对北京叫卖声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新北京叫卖声是老北京叫卖声的延续。要采集整理、研究新北京叫卖声,一定要对老北京叫卖声有总的了解和认识。而听看老北京叫卖声艺术团的演出是重要一途。
由于经常看,一来二去,就从彼此熟悉,到不时地交流;从不时地交流,到经常往来;从经常往来到最后身处其中了——我被艺术团团长孟雅男聘为了艺术顾问。先是和团里“叫卖真人”张振元往来多些,后和雅男往来更多些,大凡团里上什么节目、演出地点的选择、节目细节编排、短训班的内容安排、团里纪念和宣传活动、和外地叫卖艺人的交往等,可以说都在“顾问”之列,但更多的是围绕叫卖声发展历史、特点等进行探讨。由是,促进了我对有关叫卖声知识的学习;由是,产生了在这方面也“有所为”的想法。十多年来,我收集到的与新老北京叫卖声相关的方方面面资料多多(也许在北京是最多的)、接触到“叫卖声人”多多、看艺术团演出和参加相关的活动多多……所有这些,不仅丰富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而且扩容了我的知识结构,又增加了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角度,使我活着更有情趣更有意义。遗憾的是,老北京叫卖艺术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较之其他区县,我所在的东城区是叫卖声资源最丰富的区,只是缺乏必要的组织和整合。区相关部门对此鲜有作为,不知为何?
直爽、执着的“叫卖真人”张振元先生
因为要收集新老北京叫卖声,所以和北京的一些叫卖艺人臧鸿、张振元、张桂兰、武荣璋、武绪增等有些接触和来往。其中,和人称“叫卖真人”的张振元先生走得更近些。张先生为人热情、直爽,对老北京叫卖声艺术热爱、执着,加之我们又都是老北京人、年龄又相仿,所以,比较谈得来。很有些日子,我们经常通电话就北京叫卖声特点、分类、韵味,他个人的叫卖声特色、叫卖声艺人彼此交流等方面进行讨论,常常是一聊就二三十分钟;他每新录制光盘,必定不辞辛劳,亲驾电动三轮车直接送给我,并很诚恳地表示要听听我的看法。由于对叫卖艺术的热爱,他为此倾注了不少心血,他不惜花钱,到各个旧货市场淘了不少响器,他不怕费时费力自己动手给艺术团做了几乎全部道具。一次表演需要一个拉洋片的大箱,他二话不说,竟把家里一个大衣柜改装成了演出大箱……除此而外,凡是支持叫卖艺术的人,他都去联系;凡是会几口叫卖的老人,他都去登门求教;他对自己会的叫卖声,做了大量梳理;他试着从理论上、专业上分析思考自己的叫卖表演,甚至已形成大体框架,基本雏形……
他太想让老北京叫卖艺术发展起来了,他太想让叫卖艺术团越办越好了,他太想让自己多会多记一些叫卖声了……太急了,过累了,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