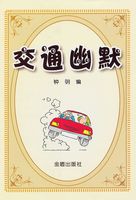思想文化的历史运动自有它本身的内在逻辑。宋代最为重要的思想与文化现象,毫无疑问应为“理学”的建构。但是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理学”或“新儒学”并不仅仅只是一种思想形态,而更是一种思想文化的历史运动。它有自己的“历史性”,从大的方面来说,至少可以上溯至中唐时期韩愈发明“道统”之说为其开端,中经“北宋五子”基于佛道观念之整合的思想努力,而至南宋朱熹完成其哲学体系的宏观建构,而体现为一种“思想形态”或“哲学形态”;它有自己的目的性,即是要重新追回以孔孟为典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价值体系,既以拒斥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宗教文化,又以全面提升国民的道德素质与精神气质,所以理学作为思想文化的历史运动,就其整体来说,同时也是先秦儒学的重建;它有自己的范畴体系与方法论,道、理、心、性,等等成为最为显著的“关键词”,概念内涵的辨析至于“析之毫厘”,而基于不同思想元素的整合以实现思想观点的体系化则表现为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方法;它有自己的经典文本系统,这一系统是以“四书”为基本骨干的,朱熹《四书集注》的完成即标志着这一“理学”文本系统的确立;它有自己清晰的价值指向,即是通过生活实践中的道德修持而实现个体人格的完成,进而通达于圣人境界。
正是在将“理学”作为一种思想文化运动的历史视野之下,我们看到了浙江学者在这一思想文化运动的历史过程中所作出的卓越努力与巨大贡献。显而易见的是,以朱熹为代表而最终实现出来的“理学”思想形态,并不是这一运动所达成的全部结果,而只是其中具有典范性意义的一支而已;除朱熹之外,以陆象山为代表的“心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历史哲学”,同样是这一思想文化运动作为思想形态所实现出来的历史成果。换句话说,宏观意义上的以儒学重建为基本目的的思想文化运动或“理学”哲学运动,到南宋乾道、淳熙之际,已然实现出了三种基本的思想形态,即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以陆象山为代表的“心学”,以及以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的“历史哲学”。此后直至近代以前,中国思想界所呈现出来的基本面貌,即是此三种思想形态在不同维度上的因革与绵延,或相互交织,或相互融摄,或相互消长,而呈现出思想历史之演变的曲折回环与波澜壮阔。
所谓“浙东学派”,是指南宋时期以“浙江东路”为特定区域而形成于其中的具有思想独创性的一个学术派别。“浙东”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而不是指今日的浙江东部地区,当时包括八府:绍兴、宁波、温州、台州、处州、金华、严州、衢州;而杭州、湖州、嘉兴三府,则所谓“浙西”。尽管学术界关于“浙东学派”的名义问题曾有过长期的争议,意见不一,但我们认为,用“浙东学派”或“浙东之学”来指称南宋时期“浙东”这一特定区域之内所出现的、具有基本相同的学术领域、学术方法、学术精神、学术目的的一派学术,无论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还是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都是可靠的。南宋时期的“浙东之学”,也被称为“浙学”。
在相对更为狭隘的地域性意义上,“浙东学派”又被区分为“永嘉之学”(或“学派”)、“永康之学”(或“学派”)、“金华之学”(“学派”或“婺学”)。不过从此三地或“三学”的代表人物的思想来看,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学术精神是一致的,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儒学重建为核心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大的历史与时代潮流的宏观背景之下,“浙东之学”采取了不同于朱熹与陆象山的思想路径与经典诠释方法,不主张将“道”领会为作为一种抽象“实体”的“客观实在”,也不主张将“心性”领会为某种可能脱离于人的现实生活而单独存在的超乎经验的“本质”;而是强调“道”必然呈现于生活的现实世界,现实的历史也即是“道”本身所展开的历史,因此对“道”的追寻就必须诉诸社会生活的历史过程;强调“心性”只能具体地显现于个体的现实生存,并且是在个体的生命存在性获得完整表达的前提之下才得到充分显现的。由于前者,导致“浙东之学”对“历史”以及仍然很少如刘鳞长氏那样用“历史学”的哲学思考,坚持将“道”的寻求贯彻于人类生活的历史过程之中,也即是将哲学的研究推进于历史学,从而实现了历史学与哲学的视域融合;由于后者,导致“浙东之学”对人性问题的独特思考,不主张“理”、“欲”的相互分离,而肯定生命完整表达意义上的“欲”的合理性,又强调“公”、“私”为度而在“理”、“欲”之间保持平衡。
“浙东之学”的这一基本而又共同的学术取向,使当时的代表性思想家都对史学有极为浓厚的兴趣,但永嘉之学从薛季宣始直至陈傅良、叶适,重视制度史的细致研究,而有所谓“制度新学”的转向,他们更为关切政治与社会制度对于生活的引导与规范,更为强调制度本身的“存道”功能,正因此故,永嘉之学在经典文本的研究方面,尤为重视“三礼”,坚持旧有的圣人之制度经过合乎现实需要的“化裁”、“通变”是仍然可以在当前的现实之中实现其价值的,因为“道”本身所展开的历史过程是有其自身的统一性的;永康陈亮与金华吕祖谦,则更为重视人物的活动,强调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的人对于历史事件的影响与作用,从而认为道之存亡是人力可以干预的,人是使道获得现实体现的能动因,因此就研究的主要对象而言,永康、金华便将《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历史文本直接纳入其研究的对象范围,哲学诠释的维度与方法被直接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或者说,哲学的研究采取了历史学的视域与方法。然吕祖谦不论是在学术视野上还是在学术方法上以及学术研究的对象上,都能兼摄融会永嘉的制度之学与永康的人物研究,从而实际上成为南宋“浙东之学”或“浙东学派”的集大成者,成为其卓越代表。南宋的“浙东之学”,正因融史学与哲学为一体,既将哲学的研究推进于制度-生活的历史过程,又对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将哲学的诠释目的及其方法运用于历史学的研究,从而独树一帜,卓然与朱熹“理学”、象山“心学”相鼎立,我们将南宋“浙东之学”所实现出来的这样一种思想形态,称之为“历史哲学”。
这一“历史哲学”维度的开辟,就浙江的学术文化传统来看,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经学与史学两相融会的结果。经学与史学原不相分离,而互为表里。就一般观念而言,经学的目的是在于明圣人之志,从而将圣人之意措置于现实政事之中,以实现出圣人制礼作乐以垂范后世的美意,使王道的辑熙雍穆之治成为现实的政治实绩,所以说经学以经世。而以经学经世,就必须将经典所记载的圣人之意及其善美之政付诸现实的政事活动,而这些活动即成为“历史事件”;“历史”是在实践活动作为过程的绵延中展现出来的,“历史”的意义也体现于这一过程本身。而事实上,经典所记载的,原本就是先王从事政治实践活动的良法美意及其经验教训,以及圣人对这些实践的阐释,它们原本就是“历史事件”。就中国学术而言,史学是随着经学的成立及其研究层面的拓展而独立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是经学的一种延伸形态,但史学既经形成,则追往以通变,穷变以达今,其目的不仅在于保存文献以汇聚人物、政事之迹,而更在于通古今之变,鉴往知来,而借以开物成务,所以又自然而然地将经学纳入其本身的研究领域,使经学成为史学的内容,经学即是史学。因此,经学与史学的目的与意义是共同的、一致的,其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也是相互交错的。经典既成为史学阐释的内在根据,史学则为经典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实践范例。在浙江的学术史上,两汉经学虽并不发达,但魏晋以降,则经学研究渐成风气,在浙东、浙西分别形成了学术的核心地带,而随着经学的繁荣,史学的维度也逐渐得到显化,从而形成了逐渐强盛的经史并重而又相互交融的学术传统。在这一意义上,南宋时候“浙东学派”的形成,也是浙江学术文化传统本身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的内在逻辑结果。
我们已经看到,南宋“浙东学派”以“历史哲学”为基本学术特征的学术研究,就经典的文本依据方面来看,与朱熹“理学”与象山“心学”均有不同。“浙东学派”诸家除“四书”、《周易》之外,十分关注“三礼”,即《仪礼》、《周礼》、《礼记》,并同时将《左传》、《史记》、《汉书》等史学文本直接纳入研究视野。正是这种文本视域的差异性,以及在文本诠释中强大的现实维度的直接切入,使“浙东学派”整体上呈现出关注现实、注重实践的显著特征,并在价值取向上明确要求知识之现实效用的切实转换,也即要求知识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实现其价值效用,为现实制度的完善与改进、为民生利益的实际提升作出有效贡献。正因为“浙东学派”所显现出来的关于知识的效用与价值的根本取向与朱熹“理学”有重大差异,它在当时就被朱熹称为“功利”之说而给予激烈批评,而后人也通常以所谓“事功学派”来加以概括。但在哲学所展开的历史维度上来考察,“浙东学派”的所谓“事功”之说,实际上恰好确立了另一种关于知识的观念,并由此而建构了另一种价值模型。这一独特观念,即使在它脱离某种“知识形态”之后,也仍然作为浙江地域的思想文化因子而存在,一旦外部世界的条件适合这种文化因子的发育,它同样会取得其新的形式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之中显现其旺盛生机。20世纪后半叶以来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视为对南宋“浙东学派”之知识观念的历史回应,当代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因此而可以找到其历史文化上的深厚渊源。
然南宋时代的浙江学术之繁荣,并非仅限于上述。朱熹的“理学”与陆象山的“心学”在浙江的传播与发展不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样也是全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以“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心学思潮,不仅是陆氏心学的最重要传承,更是使其获得强有力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尤其是杨简,以本心之说衡准六经,为经义的诠释另辟一片新天地,不仅为心学建立起经典文本上的广泛依据,而且在信仰意义上体现了对于人心的严重关切;而从袁燮开始,心学的基本观念向经史学术领域延伸,同时也向现实的维度开拓,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于金华吕氏学说的融摄与整合。朱熹“理学”在浙江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来体现的,何基为黄幹的学生,号称得朱熹“正宗”之传;而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从王柏开始,批评意识转趋浓厚,怀疑精神获得彰显,虽为后世所诟(如“四库馆臣”),却正是这种怀疑与批评的精神成就了王柏之学的特点,而因为有家学渊源的关系,王柏的学术实际上同时传承吕祖谦之学;至于金履祥,则将理学转向并贯穿于史学,而有《通鉴前编》之作,同样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学术之价值取向的转移。可见在南宋时期,即使在浙江地域之内,各不同思想与思潮之间的相互融会与整合也体现为思想界的常态。多元思想的多维整合,正是浙江南宋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的重要原因,也是整体显现其繁荣态势的重要原因。
思想学术领域之外,两宋时期的浙江文学创作趋于繁荣,名家辈出。“词”虽为“诗余”,却逐渐获得其特别的发展而成为宋代的典范性文学样式。在北宋词坛,浙籍词人若张先、贺铸、周邦彦等等,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淑真与渡江南来的李清照,并为宋代最为著名的女词人。宋室的南渡,既是政治中心的南移,也是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几乎与当年西晋政权解体而北方士人大量南迁而直接促成浙江文化趋向繁荣的情况相类似,南宋浙江文化的整体繁荣,就文学创作而言,“南渡词人”群体作出重要贡献。而在著名的“辛派词人”当中,浙籍作家尤其众多,如陆游、陈亮、岳珂、黄机、戴复古、汪元亮等,或激情狂放,气魄豪迈,赋为壮词;或呜咽沉郁,凄迷哀苦,发为小调,但皆情感真挚,以写亡国之痛,以抒悲愤之怀,读之皆能动人心魄。“辛派词”的豪放,将最为重大的时代政治主题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在词史上有重要意义;然豪放非为“粗豪”,其情感之细腻真切,才是其豪放之所以为能动人的根本原因。此后如吴文英、王沂孙、周密、张炎等人,虽风格各异,而皆擅一时之胜,篇章脍炙人口,为南宋词坛增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