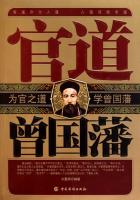其三,以耕读传家为根本的治家之道。在古代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下,治家之道历来被看得很重。这其中,耕读传家被视为最基本的治家之道。“耕”是指农耕,“读”则是指读书。这一注重耕读的传统观念是与我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发展相适应的。
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农养天下,以士治天下。这也就是说,养天下须重农耕,治天下须重读书。我们知道,农业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历代统治者对此深有认识,故而总把“重农”作为安邦兴国的基本精神。《吕氏春秋》里讲,“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所以,春秋战国以来,“重农”已成为君主既定的兴国之道。另一方面,古代的统治者也看到了读书人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于是采用各种方式把读书人中的佼佼者吸收到统治阶层中来,置其于官位,供之以俸禄,使读书人为其所用。统治者的这种重农耕、尚读书的长久治国策略影响到民间社会,就形成了中国家庭“耕读传家”的基本观念。
其实,中国百姓自古就有尚农的传统,把农桑视作生存之根。所以,《周易》里讲:“不耕获,未富也。”从秦朝开始的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抑商政策,更是把人们牢固地牵制在土地上,天下百姓莫不以农耕作为根本的生活手段。长期的经验积淀使得古代中国人树立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农耕是最可靠、最稳定的生存手段,除非万不得已它是不能够放弃的。正是在这样一种观念影响下,在我国古代,即使是通过工商业致富或为官发财的人,最终也以购买田产作为根本生存与发展之计。因为相比较而言,这乃是最稳定的保存家产的办法。
虽然农耕是生存的基础,而若要求发展、求成就、求财富,在中国古代社会,唯一的正道就是读书。因为“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可以通过读书入仕谋生,乃至发财致富,光宗耀祖。所以孟子就说过这样的话:“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读书人做官就像农夫耕地一样可以安身立命。
可见,“耕读传家”这一观念既有重生计之“俗”,又有求高贵之“雅”,实在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一种融雅俗于一体的生存智慧。它是古人在重农尚仕的社会之中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治家方式。也因此,“耕读传家”作为根本的治家观念深植于传统文化之中,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所接受。
其四,以义利合一为基本价值追求。追求义利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的价值思想,它是在古代思想家们漫长的义利之辩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义,而“利”则指利益,一般多指物质利益。
从先秦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就纷纷对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重义轻利。如孔子就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虽然并没有否定“利”,但他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君子要“义以为上”、“见利思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但更强调义与利的对峙。
他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孟子·梁惠王上》),并以“为利”还是“为义”作为区别小人与君子的唯一价值标准。荀子则认为任何人不可能不考虑个人利益,然而应该使个人利益的考虑服从道义原则的指导。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所以荀子认为虽尧舜不能排除民之欲利,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因此,荀子认为处理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见利思义”。这与孔子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只不过他更承认人有好利之心这一基本事实。
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著名命题,以尚义反利的观点片面发展了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所以,后来清初的启蒙学者颜元针锋相对地提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的相反命题。他认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把义与利相互结合起来。可见,颜元在古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对董仲舒以来的道义论价值观作了可贵的纠正。
当然,在义利统一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正统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重义轻利甚至是尚义反利的思想也一直是一个传统。这一传统一方面维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塑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气节、重人格的民族性格;另一方面,也有压抑人的物质欲望,扭曲人性的弊端。对于中国传统价值观中的这一“反利”传统,无疑又是我们今天所应该批判和否定的。
其五,以直观意象为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西方文化传统中比较强调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在思维方式上以直观意象为主,这是一种通过直观、直觉来直接体悟和把握对象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首先是直观和直觉的,儒、道、佛三家的认识论都带有这一思维的特点,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充分体现儒、道、佛三家合一的理学思维。宋明理学家把“太极”、“天理”作为包容了宇宙人生一切真理的本体存在。但对这个本体的认识,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直觉顿悟才能实现。只不过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把经验知识的积累作为顿悟的必要条件,最后通过顿悟而“豁然贯通”,由渐而悟,完成心理合一、天人合一的整体认识。而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则主张当下参悟,明心见性,“立其大者”,“点铁成金”。
张岱年先生曾指出过这一点:“中国哲学只重生活上的实证,或内心之神秘的冥证,而不注重逻辑的论证。体验之久,忽有所悟,以前许多疑难涣然消释,日常的经验乃得到贯通,如此即是有所得。中国思想家的习惯,即直截将此悟所得写出,而不更仔细证明之。”此可见,与讲究分析、注重普遍、偏于抽象的西方传统思维方式不同,中国的直觉思维更着重于从特殊、具体的直观领域中去把握真理。它超越概念、逻辑,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显示出中国人在思维过程中活泼不滞、长于悟性的高度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体现的这一思维方式又是意象的。这种意象性源于直观与直觉。在《周易》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思维模式。《周易》中由阴阳、八卦、六十四卦和三百六十四爻组成的卦象,就充分显示着意象思维。
它由象数符号表现整体意义。如泰(棯)卦的象是地在上,天在下。但实际上应当天在上地在下。这一卦象就象征着天和地的交感变化,所以,是吉卦,预示着事物发展有前途。否(棲)卦则与此相反,天和地没有交感,因此是凶卦,它预示事物发展没有前途。
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则更注重意象的浑融一体,强调只有发现和形成了意象之后的创作,才能臻至独特意境。所以,中国艺术就是营造意象的艺术。中国画强调“意在笔先,画尽意在”,中国画中所要描绘的,与其说是客观对象,不如说是主观的意义和象征。中国书法艺术更是意象艺术,书法美是意象美。即所谓书为心画,是有意味的形式与象征。同样,中国古代的诗歌不同于西方偏于表现情节,而是借象寓意,借景抒情、情景交融,追求意和象、意和境的融通。“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从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就开始的这一对意象的追求与营造,显示出中国传统文学所特有的韵致和意境。
独特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不同于西方文学艺术偏于再现、摹仿、写实,追求美与真的统一,而是偏重象征、表现、写意,追求美与善的统一。正是在这一特有的文学艺术传统的规范与熏陶下,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创作了大量绚丽多彩、意境深远的艺术作品。
三、以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相统一为基本方法,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在走向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的21世纪,摆在当代中国面前的根本任务无疑是尽快实现现代化。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将是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新型文化。但这个适应现代化的新型文化决不是无中生有骤然降临的,而一定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内在的必然的关联性。事实上,从世界上一些已基本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来看,对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开掘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文化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要环节。因此,传统并不是守旧僵化的代名词,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理性和智慧的积淀,对现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总是有着多方面的启迪。这既是传统得以成为传统而不被历史之河所湮灭的缘由,更是我们了解、学习和开掘传统文化的内在根据之所在。
我们知道,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由古代向近、现代转型。在这个充满危机与痛苦的转型过程中,人们对待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诸多的偏激情绪。20世纪20-30年代,“全盘西化论”与中国文化本位论的争论正反映了这种偏激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