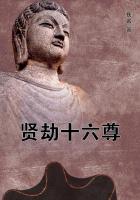1.大风雪送来的爱情,差点赔上了父女情
我是1963年1月飞往美国的冰天雪地,在普渡大学读书。
我21岁大学毕业,在三年半内取得双学士学位。由于成绩优秀,获得往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的奖学金,并获杰出学生奖。
20岁时,妈妈担心我书读得太多,将来嫁不出去,打电话来,要我读完学士后立即回家。
我记住了爸爸从小的教导:要自立,就要有学问。反正我自己也爱读书,好学。
我告诉爸爸,学费方面我有奖学金,其他住宿费和杂费我自己会解决,一定读完硕士才回家。于是我进入芝加哥大学读社会工作学,专门研究问题儿童。
当然我没有告诉妈妈,我每天要在学校宿舍的饭堂里工作,端菜、洗碗,以赚取自己的住宿费和一顿免费饭餐。当然,为省钱,我一日只吃一餐,所以瘦得很。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芝加哥Rotary Club请所有的外籍研究生赴俱乐部参加讲座并举行晚宴。讲座是关于南非经济的。
当晚我穿了一件蓝绿泰丝中国旗袍,外加平日穿的绛蓝色毛大衣。为了头发不被大风吹乱,我特地把长发在脑后盘了个发结,顿使平时略有点假小子味的我,多了几分成熟与妩媚。
可能因为风雪太大,有不少客人未能出席,我当时孤单一人坐一空桌,工作人员便把我带到另一桌坐,恰巧坐在一位身材魁梧、衣着端正、戴着眼镜的外籍人士旁边。
因为我们是完全陌生的两个人,起初只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我礼貌地多谢他今晚请客。
他有点奇怪反问道:“您为何多谢我?”
我说:“因为你头发半白,一定是成功的生意人,所以可以做Rotary Club的会员。今晚你一定是其中一位主人。”
他爽朗地笑道:“我只不过也是像你一样,一个从奥地利来美的留学生,头发大概是先天性早白吧,我才28岁。”这人就是苏海文。
席间,不知是哪个朋友提到我们六个人,曾十个日夜做黑人青少年工作的那件事,苏海文两眼放光,惊讶感慨道:“安娜小姐,真想不到身材如此娇小的你,竟然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真让人佩服!”
原来,苏海文曾在美国南部一所黑人大学任教。别人都说他胆子大,因为他不但是少数的白人教师,也是唯一敢到黑人饭店吃饭的白种人。
当时美国南部活跃着“三K党”,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极端种族主义的白人组织。他们仇恨黑人,更痛恨“爱黑人的人”(Nigger Lovers)。他们不但残酷地烧死过被他们称为“黑鬼”的黑人,而且还把同情黑人的白人找出来,连同他们的家人一并烧死——所谓著名的“猎找妖怪”(Witch Hunt)。市政府和警察不敢插手管,也不想插手管。
苏海文,来自奥地利的白种人,却从来不认为白皮肤高贵,有色皮肤就低贱!他讲得很真诚:“我一向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绝对没有种族之分,没有男女之别!我来自欧洲,从历史上学到,为种族歧视的理由可以杀死千万人口。正如希特勒,要消灭所有的犹太人。这种极端观点,竟成了杀人借口。有的人以宗教为借口杀人,这是人类自卫的极端方法罢了!
我对黑人的处境非常同情,所以我就去黑人大学当教师,想把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传授给黑人大学生,让他们也能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利益!你可能不相信,我还教黑人美国历史的。”
我问:“是真的吗?你来自奥地利,在美国只不过一年,又知道多少美国历史?”
“坦白告诉你,我临时抱佛脚,讲课前一天,自己拼命地看书。你还以为讲师很了不起吗?况且,有教育的白种人,都不喜欢到黑人大学里教书。那黑人的学问水平又如何得以提高呢?”
那一夜,我们一直聊得很晚很晚。
说来真奇怪,我和苏海文是第一次见面,却有说不完的话题。
细想起来,我们有太多的相似:共同的正义感,相似的同情心,同在异乡为异客的经历,同是奖学金的获得者,同样喜欢简朴生活,同样热爱音乐,追求同样的理想——用自己的知识,为推动世界进步努力。
后来,这位自我介绍为Helmut Sohmen(我后来替他起名苏海文)的先生,曾多次来电话约我出去。但因为我常在黑人区工作或去上课,从没有接听到他的来电(那时还没有电话留言服务),过了两个月后,我意外地收到他的来信,邀请我去一个研究生舞会。我当时忘了他是谁,只是出于好奇心,应约赴晚会。见面后才发觉,他就是与我共享免费晚餐的那一个人,也是大我七岁的奥地利人。他与我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富有同情心。
五个月后,他向我求婚,我拒绝了。因为我年仅21岁,未有结婚打算。尤其是与不同国籍的人结婚,一定会带来很多不必要的困难。连家中爸爸的司机老李也曾跟我说过:“和外籍人士出街的,都是香港下流的女人,是在男人身上赚钱的女人。大家闺秀是要和大家庭的人家来往,门当户对,才像样子啊!”
一星期后,他又提出结婚的事,我依然婉拒了他。
他却坚持:“地球是越来越小,人类是会越来越开明的。”
他说得的确对。1967年时,跨国婚姻确实稀有,但到了2008年,香港已有了不少的异国姻缘及混血子女。但我当时却免不了怀疑。
再经一个月的游说,又因他快要离美到加拿大就业,我最后被他说服了。到底他是个律师,有口才,也有智慧。我们决定在芝加哥结婚。
我打长途电话给爸妈。
因为妈妈的态度一向非常明确,每回离开香港返回美国时,妈妈千叮咛万嘱咐:“陪庆呀,你长大了,可以找男朋友了,但最重要是一个真心爱你的男人,而不是爱你的家庭背景,或爱你的钱。钱是肮脏的。”
在与爸爸每周一封的通信中,我曾经多次试探性地问过爸爸。爸爸说:“最重要的是人品,他有没有钱是不重要的。”
当我电话中告诉爸爸我和苏海文准备结婚的事,爸爸在电话里只说,慢慢再说,又给我发了一封特快信,他在信上写道:“尽管我们加入了英国籍,但我们永远是中国人,总是要为中国做些事情的,找个中国人当丈夫,就省去了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麻烦。
中国总有一天会开放的,做中国人,应该回去帮助中国发展,如果有一个外国丈夫,怎么办呢?你跟他去他的国家,还是忠于自己的国家?”
我心情很矛盾,很不愉快,知道妈妈一向反对嫁外国人,但想爸爸或许有可能支持我。因为爸爸是个通情达理的好父亲,一定会尊重自己女儿的决定。而且他和那么多的外国人交往,知道他们不是“异物”,一定会比妈妈开放及明事理。
所以,我飞回香港,从机场直接来到爸爸的办公室,在第一时间里,把自己要和苏海文结婚的消息再次解释给爸爸听,想请他“胳膊肘朝我拐”,帮助我一块说服妈妈。
爸爸听了神情凝重,面色难看,但没有说什么,只是挥挥手,让我从他的书房出去。
还是司机老李直说出来:
“你可是体面人家的女孩子,还在美国读了硕士,你怎么能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呢?!这让你爹妈怎么见朋友?
你是大小姐,不但有学问,又有背景,洋鬼子是没有背景的,配不上你的。”
说完老李先出门备车去了。
李司机从上海就在我们家给爸爸开车,一直和我们住在一块,爸爸待他像自己家人,他也把我们姐妹当晚辈管,有话从来直说,不用顾忌什么情面。
过去常有朋友奇怪,我从小在上海、香港长大,普通话怎么会有天津口音。其实,就因为刚来香港时,老李北方人学讲粤语,就像鸡同鸭讲话,怪腔怪调的。于是五岁的我说:“还是我学你的天津话,好过你学讲广东话!”于是,出车问路,常常是我听懂了广东话,再用天津话翻译给老李听。
我盯着爸爸追问道:
“爸爸,你不会也和老李一样看法吧?!难道你忘了,第一个向我介绍西方人有绅士风度的也是你啊!老李无知识,以为洋鬼子都是野人,但海文文静,又有三个大学学位,包括两个硕士在美国得的,一个博士学位是在奥地利拿到。说不定还可以帮爸爸的业务!”
这的确不是我强词夺理。
“陪庆,我从来不否认英国人的绅士风度,也十分主张你们姐妹要学习那种落落大方的处事风格。”爸爸尽量用平静的口吻对我说:“但结婚又是另一回事,何况你妈妈是大大反对的,因为他们不能沟通。”
“但妈妈懂的英文比我们想象的多,而且您也常鼓励妈妈要多学英语,那么有了外国女婿,不是可以常练习了吗?”现在想起,我是多么幼稚。爸爸的声音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们不管加入什么国籍,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我们总要为自己的祖国做事情的,你找个外国人当丈夫,他怎么可能把为中国做事,当成为自己祖国的事呢?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我一下子愣住了。
说实话,从14岁随爸爸参加社交应酬活动,尤其是16岁上了大学后,我自认为与爸爸除了亲情,更增加了许多朋友似的默契和认同感。爸爸也是我最尊敬、崇拜的男人。我找一个丈夫,也要和爸爸一样能干聪明。
对许多国内外的大小事情,对许多朋友亲属的看法,对某种事物的好恶,我和爸爸常常在各抒己见之后,发现各自的观点总是十分相近,甚至于完全一致。
父女真可算得上达到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地步。
但在这个婚姻大事上,我们父女永远有差距,永远有争论,永远无法达成一致。
说真话,中国、宁波,这些爸爸讲起来充满感情的祖国、故乡,从小在我脑海里,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在香港长大的我,只知道当时中国是非常穷困的。家中的广东保姆每年都要寄油寄粮去救济大陆的家人。
我听妈妈说,这些年来,前前后后,多多少少,爸爸寄钱寄物,尽其力量帮过家乡近百人。爸爸似乎也从来没有想过,日后能得到受他帮助过的人的任何一点回报……我对中国的感情,只是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上学来的,是从爸爸谈起中国领导人的贡献上学来的,也是因为对英国殖民地主义反感而产生的。记得我高中快毕业的那年,我跟随爸爸接待过卢家伯伯之后,发生了一次争执。
卢家伯伯当时是中国外经部的副部长,出国回来路过香港。
那时国内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十分困难。爸爸妈妈原想请卢家伯伯到家里好好吃顿饭,特意订了好多平日我们家也很少问津的东星斑、鲍鱼等高级海鲜。
卢家伯伯却婉拒了。
爸爸妈妈带我去宾馆看卢家伯伯,拿了一些糕点糖果,请他带给卢家妈妈和孩子们吃。卢家伯伯似乎生分了很多,不再像过去在上海时那样笑容满面,只是刻板地说:“国内东西虽然少,但还有吃的。”又推说自己行李已经太重,“你们的心意领了,东西不用带。”
最后临分别时,他和爸爸握过手后,说:“玉刚老弟,听说你加入了英国籍,我真的好生气,好失望!”
“其实只是为了谈生意方便……”爸爸想解释。
“加入英国籍,这当然是你的自由,不用解释,只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永远是中国人!”
“三阿哥,这点你放心!”爸爸回答得斩钉截铁。回家的路上,爸爸面色沉重,一直在深思。我知道爸爸一向最敬重卢家伯伯,心里猜测,被最敬重的人责备,爸爸心里一定不好受,我一定要安慰爸爸。
眉头一皱,计上心头。
回到家,我就跟到爸爸书房,他自言自语地说:“大陆领导人中,有许多像卢家伯伯这样热爱祖国,精忠报国的人,大陆一定能发展,只是时间问题!”
“刚被卢家伯伯骂过,你还说他好话?”我忍不住发起牢骚。
“哎,卢家伯伯说得不错,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他说得对,你为什么加入英国籍?他们英国人的殖民主义意识可强呢!很多方面看不起中国人。你不是自相矛盾嘛!”我大声反问。“是啊,这也是卢家伯伯不了解我的难处,他说我,我也不会怪他。
其实,加入英国籍也并非我的心愿,只是我们做航运的,满世界跑,拿着香港护照,无论到哪个国家,都被海关翻过来倒过去地查,太过费时又费力。拿这个英国护照也不容易,要靠很多关系。
拿了英国护照,许多国家免签证,到美国、日本、拉美都少了很多麻烦嘛!对于我来说,除了这本护照是英国的,只不过是一个通行证件,是改不了我的心的。”
我心里想,爸爸向我解释,但没有跟卢家伯伯辩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