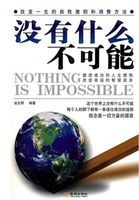那个小沙弥变成了风流浪子,他把人的本能发展了,发展向食色享受、物质享受、感官享受那个方向去了。这种本能的膨胀和发展,有可能发展出比动物更可怕的堕落与粗暴、掠夺与侵占,甚至走向犯罪。能够把他拉回来的,就是他的惭愧心。惭是尊重自己,愧是尊重他人;惭是向善,愧是拒恶;惭是自律,愧是他律。所以,惭愧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是人与畜生不共的德行。所以,有惭愧心的人,才具备做人的资格。
《论语》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西,曰:彼哉,彼哉。
问管仲,曰:人也。夺伯氏骈邑三百,饭蔬食,没齿无怨言。
有一天,有人问孔子:郑国的子产,这个人怎么样啊?孔子说:他是有恩惠于国家、有恩惠于人民的人啊!又问:楚国的子西,怎么样呢?孔子不愿说人家的坏话,不肯做褒贬,只是说:“他啊!他啊!”最后问管仲,孔子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这才是一个人,一个够得上是人的人啊!他把齐国另一重臣伯氏的食邑三百亩好田,都收为公有,伯氏一家人穷了,只能吃青菜淡饭,而伯氏一家到死没有怨言,口服心服,这就是管仲啊!孔子称赞他是一个能够称为“人”的人。这是多么值得深思的评价啊!
说到这里,我想我能回答我的第六个自问了,我不是什么?我不是禽兽,我应该是人,是一个能懂得惭愧,懂得感恩,能反省自己、总结自己的人,一个能改正自己、改善自己的人,一个直立的、有正知正见的人。
7.我没有去做的是什么?或者,我应该去做的是什么?
有一个盲人,在夜里走路时,他手里总是提着一个明亮的灯笼,别人觉得很奇怪,“你自己看不见,为什么还要提着灯笼走路呢?”盲人说:“对呀!我提了明亮的灯笼,不是为了照路,是为了给别人光明,让别人看清脚下的路。
别人看清了路,也就不会误撞到我,这是我保护了自己,当然,也帮助了别人。保护自己和帮助别人是一致的。”
盲人眼中没有光,但他心中有光。这光,就是智慧。
我们出家人一见面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译为中文,就是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是福德;无量光,是智慧。“阿弥陀佛”就是福德智慧。
人的一生,是一个求生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求,没有止境。小时候,要求学;毕业了,要求工作、求事业;人长大了,要求爱;有了老婆,要求儿求女;生下了儿女,要求财、求养家糊口;生活改善了,要求名求利、求地位、求待遇。求来求去,有一样,没有做,这就是我的第七个自问:我没有去做的是什么?或者,我应该去做的是什么?我说:就是求智慧。这才是人最应该去做的。
南怀瑾先生有一句名言:“人,究竟为了什么?”他说,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哲学上的老问题,我不这样认为。先说一个故事:
清朝的乾隆皇帝最喜欢游江南。这次,他来到镇江金山,登上江天寺的宝塔,看到长江里船来船往,他就问一个老和尚:“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了?”老和尚说:“住了五十年了。”又问:“你五十年来看这江上,每天来往有多少船只?”老和尚说:“我只看到两条船。”乾隆惊奇地问:“这是什么意思?五十年了,只看到两条船。”老和尚说:“是呀,一为名来,一为利往,人生就是两条船呀!”乾隆听了很高兴,认为这个老和尚回答得很不简单。
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文学家李笠翁,有一副对联:“人生两演员,天地大舞台。”在这个大舞台上,只有两位演员。没有错,一个是男人,一个是女人,没有第三者。
佛教讲人生就是两件事。叫“生死事大”。所以,出家人,为什么出家?就叫“了生死”,又叫“了生脱死”。怎么能说“人,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了什么”呢?
其实,孔子也知道人生这两件事,他在《论语》里说:“所重,民食,丧祭。”这个“重”就是重点、重心。一个施政者、管理者的重点,一是“民食”,这是生活,这是讲生。一是“丧祭”,要安排后事,这是讲死。生要养生,死要送死。一个是生的关怀,一个是死的关怀。
孔子的“所重”同佛教不是如出一辙吗?
如何知生知死,如何弄清楚“生从何来,死向何去”?如何才能了生脱死?恐怕有很多人从来没有思考过,甚至没有想到过。这是一种觉悟,人生的根本的觉悟;这是一种智慧,人生的最本质的智慧。
我应该做的还没有做呀。
8.我要防止的是什么?或者,我不知道应该防止的是什么?
人,懂得防止上当受骗,懂得防止自己不要受了别人的欺骗。
可是,人却不知道还要防止受了自己的欺骗。
宋朝有一位名臣,他是一位理学家,叫赵拚。他到四川去上任(相当于今天的省主席、省长),骑一头骡,随从只有一个老仆人,还有一琴一鹤。全城文武官员出来迎接,却找不到他。原来他已经进了城,坐在一家茶馆里慢慢喝茶了。后来,他不做官了,退下来了,回到家里,写了一首诗:
腰佩黄金已退藏,
个中消息也寻常;
世人欲识高斋老,
只是柯村赵四郎。
第一句,说:腰间佩的那颗做官的黄金印,已经退还,交上去了。
第二句,说:一生风云,已经过去,平平常常,不值一道。
第三句,说:他退下来住的地方,这里叫高斋,你想认识这个老头吗?
第四句,说:他还是那个当年住在老家柯村的赵老四啊!
非常平淡,非常宁静。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拚(赵清献公),他一生奉献国家、正直清廉,最后归于平淡、平凡。这样的平凡就真的不平凡了。不平凡就是他不欺骗自己,不受自己的欺骗。这才是真的不平凡,真的了不起。
人,其实是很容易被自己欺骗的。
人有很多的角色、身份。比如在家庭里,在父母面前,你是儿子;在爷爷、奶奶面前,你就是孙子;在太太面前,你是丈夫;在儿子(女儿)面前,你又是爸爸;在弟妹面前,你是兄长;在哥姊面前,你又成了弟弟。面对这些不同的角色、身份,又有了不同的做人要求。一个人角色迷误、身份模糊、位置不清,那就很尴尬,就要犯大错。在社会上也一样,在公司里,你是一个部门经理、一个白领;在老板面前,你是员工,是部下;可在员工面前,你又成了领导,成了领头羊。如果你参加了什么业余协会,你又有了社会兼职,你的角色、身份又完全不同了。你必须按照你的角色期望和角色认同,去处事、去做人、去调整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你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立身之道。
可是,这些角色、身份,不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时间、地点、各种因缘的变化,角色也会被置换,被转化,甚至消失。以我自己为例:我在佛学院当副院长(院长,是一位领导人兼任,并不住院,也不来院),我就成了实际上主持院务的住院的一位负责人。这个角色、身份是明确的。然而,副院长的职务是一个职称、头衔、位置、责任,在这个岗位上,我不可能以自己的个人意愿来说话、来处事,我必须以“副院长”的角色要求、身份规范来说话、来处事、来面对一切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我的社会角色所规限了的。可是,学生毕业了,学院已不再继续聘任了,我这个“副院长”的头衔固然还在,别人也称呼我“院长”,却已成虚职,没有任何的实存意义了。如果我还以一个“副院长”的虚衔、虚荣,来自满、自处,那就是一种自我欺骗了。因为离开了学生,离开了教学管理,“副院长”的头衔已毫无用途了。这个称呼,虚而不实。
有时候,当一个领导人,往往会被他的部下捧坏了,捧得晕头转向。尤其是年轻人,人生历练还不够,吹捧太多,明明说错了,下面还说对、对、对,是、是、是,捧到了自己也来欺骗自己的地步。
有时候,我去参加公开活动,因为我的特殊身份(代表了一个宗教),我被安排坐上了主席台,并且坐在显着位置,成了万众瞩目的嘉宾。可是,活动结束,我走下台来,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又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我。如果,我还以坐在主席台上做嘉宾的那个虚荣来自满、自炫,那就是一种自我欺骗了。因为离开了那个场合,我曾经的角色已毫无用途了。那个场面,已成过去。
一个借“背景”、“他力”或“刹那因缘”生活的人(比如:官员、老板、执行长、总经理之类),在他退休以后,他会很失落,因为从不平凡回到了平凡,从绚烂回到了沉寂,他就不平衡了,他还生活在对过去的自我陶醉、自我欺骗之中。更可笑的是,报载,还有因此而自杀、自毁的人,那就更是一种角色迷误,知见的虚妄了。
学佛,就是回归本然,回到真正的自我。走出那些角色的耀眼光晕,我们既不要被别人欺骗,也不要被自己所欺骗。这才是一个本色的人,能在任何情况下都独立自主的人。这是真正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