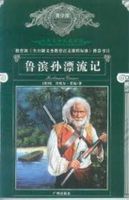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少不了要探讨批评家们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文学刊物。20世纪80年代,文学刊物在推动当代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世纪之交,它们虽然面临着不景气的局面,但并没有脱离了与文学批评之间的关系。“应当说,从出版学的角度讲,我们对期刊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但从文学的角度上看,研究就很不充分了。其实,我们的文学研究一直缺乏一个视角,即文学媒介与文学创作、文学生产的关系。”“期刊是‘活’的,是与文化环境、传媒系统、编辑思想、期刊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而编辑思想及其指导下的期刊行为可能就是某一时段社会意识、文化思潮、审美理想及文学观念的体现,事实上,这些观念性的东西要化为真。”可见,文学刊物不仅是登载文学作品、发表相关评论的场所,更以其独特的媒体作用影响着整个文学生态系统的正常发展。
因此,它也成为我们讨论文学理论建树不可或缺的一环。
江南地区历来文风很盛,带动了各地文学刊物的繁荣。它们博采众长,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同时,它们也利用本土评论界的优势,积极调动其积极性,使刊物在奉献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能有针对性地对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展开评价,从而提高大众的阅读欣赏水平。这样一来,高素质的读者群又可以反过来推动刊物的发展。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各地文学刊物充分整合了批评家的资源,组织座谈会、研讨会、笔会、沙龙等,争鸣不断,新理论新发现也持续不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第一节《上海文学》:思想的先锋性
在当代文学的评论和研究领域中,上海的评论界占据了突出重要的位置。同时,由上海而江南,形成了一个独领风骚的三角地带。
此处不可不提及《上海文学》及其麾下的批评家群体,在整个跨世纪的文学运动中,他们的姿态都是很积极的。
《上海文学》一贯走高品位的文学路线,在批评上强调思想的先锋性。它有一个跨越了许多年头的品牌栏目——“批评家俱乐部”,常常以笔谈、对话等方式,较为通俗地探讨文学前沿问题(特别是与“民间”有关的,这说明它的先锋性是以关注大众生存状态为旨归的),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如当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就是由该刊举办、王晓明主持的一次座谈而引发的。此外,当时不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批评文章的人,如蔡翔、吴亮等,其文字并不艰深,与文学、当下生活的联系也很紧密,表现出随性、浅显易懂的风格。
2003年下半年,《上海文学》改版,由陈思和出任主编,一批学院派批评家,如张新颖、王光东等出任编委。这说明《上海文学》在批评的格调上进一步提升,逐渐向学院派的趣味靠拢。陈思和曾谈到自己主编《上海文学》的思路:我上任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组成了文新编辑委员会,上海在思想理论与文学批评方面历来有较强的传统优势,请目前在上海最活跃的批评家和学者、编辑来担任刊物的编委会,是希望批评家们群策群力办好一家刊物,不但要引导刊物的编辑方向,而且也希望上海的文学批评在创作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建立了与复旦大学出版社联合办刊物的出版机制,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将由出版社来承担,这表明了我们面向大学校园,在大学生中发现作者和扩大读者的策略。由思想与文学批评来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由未来的文学生力军作为我们的主要作者与读者,是我主编《上海文学》的基本思路。
《上海文学》虽然改版了,但我们不难看出其始终如一的独立批判的品格和孤独守望的精神。时代在变,但刊物的办刊宗旨并未变。
在这之间,编辑杨斌华曾回顾了刊物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坚守信念的一贯精神:“90年代初期,《上海文学》秉承自己80年代以来所坚持的‘当代性、文学性、探索性’的一贯主张,发表了许多关注社会改革现实,富有历史凝重感,且注重艺术表达个性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显示了它始终不倦的文学追求。”“如何深刻体认和表现现实中国的真实状况,如何倡导凸现着作家艺术良心和人文责任的文学,成为《上海文学》多年来默默执守的一种文学信念和抱负。”在坚守人文精神的同时,《上海文学》尤其关注上海的本土文化,即关于市民社会与市民文化的研究。它曾以大量的版面推介有关的研究文章,这些讨论“更注重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学术思考角度入手,在学理层面上作出扎实细致的论述。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争鸣性讨论常有的浮躁风气,并且为当时文坛与之相关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历史参照和理论背景”。1994年它推出了“文化关怀”小说,意在“突出了两个主题:对弱者,关怀他的生存;对强者,关怀他的灵魂”。同年又组织“新市民小说联展”,关注“城市”这一“90年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在1999年推出的以“当下中国的‘市场意识形态’”为总题的批评文章,“将关于市民社会与大众文化的研究落实为当下现实的具体的形态分析,进一步显现了知识分子文化批评的介入性和批判性立场”。
可见,《上海文学》在突出海派文化特色、发挥本土批评优势的基础上,同样彰显出江南文化的精神特质,即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同时又大胆地开拓进取。它不仅利用地利人和营建了学术气息浓郁的“文学场”,为当代文学理论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地;还与《江南》、《钟山》等刊物一起,打造出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理论阵地的“金三角”。通过这巨大的合力,在更广阔的批评研究领域里收获了一个又一个硕果。
2003年改版后的《上海文学》显然提升了格调,它在栏目名称设置上就已显示出出身科班的编辑者的良苦用心:它“借用文学史上的名刊刊名作为栏目名称,意在承续先贤的遗风,立足民间立场,坚持文学理想,弘扬人文精神,以精致、朴素、创新、大气之风,开启《上海文学》新局面”。至于其中的理论文章,更是走深刻一路。这固然反映了它欲打造自己高雅品格的迫切心理,但过于急速的转型,也使《上海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原先的“化大众”的取向,有曲高和寡的危险。在2006年接近尾声的时候,陈思和辞去了主编的职务,这是否意味着《上海文学》在坚持文学尊严的同时又一次酝酿着变革呢?
在长期的理论探索中,除了学院派批评家为《上海文学》的理论版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之外,学院派之外的文人,如本土的蔡翔和吴亮,还有浙江、江苏等地作协、文联的专业批评家都在这一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批评。他们的文字与学院派的有所不同:理性思辨的色彩减淡了,主观精神增强了。在《上海文学》这面大旗下,他们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批评景观。可以说,像《上海文学》(也包括《钟山》、《江南》等)这样的文学刊物在江南文化坚守信念、开拓进取的人文精神的映照下,整合了江南的批评家资源,反映出江南学者某些共同的价值取向。
第二节《江南》:文化品位的追求
作为浙江省作协主办的刊物,《江南》一如既往的高雅的文学品位与省作协的指导方针有着莫大的关系。2002年,当时的浙江省作协主席黄亚洲曾表示:“2002年至2007年是至关重要的五年,浙江省作协规则了新的奋斗目标:建设一支有全国影响、门类齐全、风格个性突出、年龄结构梯队化的文学浙军;形成一种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地域文化色彩、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浙派文学;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建立和健全有利于文学繁荣的激励机制和必要的物质设施。”
省作协除了做好“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文学解读浙江创作工程”、“浙江青年文学之星”评选以及“青年作家讲习班”等工作之外,还将举办每年一次的“作家节”,它“集文学论坛、采风活动、签名售书、创作研讨、成果展示于一体”,“同时还将为市民和文学爱好者创办‘作家免费讲座’,义务讲解文学。这样可以让文学密切关注社会的发展,而且也让全社会密切关注文学的发展”,等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浙江省作协开放、进取、务实的精神,这也是在《江南》二十多年的办刊思路中贯穿了始终的。
那么《江南》的主要特色是什么呢?下面拟作三点归纳:
一、关注“前沿”
与20世纪80年代热衷于西方文学理论的热潮相合,当时的《江南》在推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方面也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它于1985-1986年间设立了“欣赏与借鉴”栏目:“专栏将逐期选载我国近代作家及西方现代主义各流派有借鉴价值的代表作,并加点评,以飨读者。”栏目主要欣赏与借鉴的重点在于现代小说的技巧,推出了如美国艾·巴·辛格的《可怕的问题》、《洗衣妇》,日本远藤周作的《钢琴协奏曲第二十一乐章》等作品,在刊登译作的同时也配以相关的短评,其焦点集中在作品的创作技巧上。显然,在当时“先锋文学”大背景之下,其紧追潮流、力图在文学的技巧上对别人进行借鉴从而开阔自己的视野的意图是显而易见的。与当时的名刊《钟山》、《收获》等相比,《江南》只是一个不显眼的后起之秀,但它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脚踏实地地从本土开始开发自己的读者群。从它对西方现代主义流派的介绍就可以看出这种务实的精神:不求大,但求精深。它刊载的有关赏析文章往往从一两点创作技巧切入,力求将这些“小”问题讲透彻。正是在这样“微言大义”的评介中,《江南》一步一步地走出自己的天地来。
当时,《江南》刊发的文章以中篇小说为主,在追求新观念新方法的大背景下,其相应的评论文章也以“中篇小说艺术谈”为主。如杜荣根的《耐人寻味的中篇隐层结构》(1986年第1期),认为近年来的中篇小说具有“双层型结构”的共性:“它的界定是在一个中篇里存在着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线索。一条是明层的,实写的……另一条则是隐层的,虚化的,象征的。”再如钟本康的《当代中篇小说叙事形态的变化》(1986年第4期)一文,从意识流小说、心态体小说、纪实体小说、象征体小说、神话、童话体小说、散文体小说、诗体小说、怪诞体小说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当代中篇小说在文体上的新变化,颇有见地。
虽说众多的评论并没有提出什么口号、流派,但却以朴实无华的论述影响着文学的热情追随者。
《江南》在80年代为追赶先锋文学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反映出新时期的江南,尤其是浙江人,在意识到自身被时代抛离之后准备迎头赶上的决心和信心。浙江在历史上曾是文化大省,文学巨星璀璨,思想观念前卫。“十年浩劫”之后,刚从噩梦中苏醒过来的浙江人惊讶地发现,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学上来看,自己都已经落后了。历史上曾有过的辉煌与眼前的寂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使浙江人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迎头赶上。这种向前追赶的心态无疑给本地的文学界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其后二十多年的发展中,不仅涌现了如李杭育、王旭峰、艾伟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也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创获。我们自然不能不对《江南》在80年代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推波助澜多作关注。没有它当时刊载的诸多研究成果,中国的文坛恐怕会寂寞许多罢。
二、打出“文化牌”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江南》刊登了许多本土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并配合相关的文学创作刊发评论,由此不仅为作家提供了一个展露才华的舞台,而且也促进了本地文学理论批评的进步;至2000年,它又突出“文化味”,开设了“江南别记”、“礼华视点”等专栏。在这些专栏所登载的作品中,张加强以追忆江南往事的散文为主,翁礼华以古抚今,主题定在古往今来的经济问题上,他们的散文流露浓郁的地域文化与历史特征,显示出《江南》地域特色的加强。
这些文化散文引起了评论家广泛的关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探索,在时机成熟的2003年,《江南》组织了“江南文化散文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文化一直在中国文化史中有着某种奇特的内在品质”,即“阴柔之美”与“坚韧甚至强悍的内在禀赋”的有机结合。会议以张加强、柯平的历史散文、翁礼华的财经散文及刘长春的文化散文为视点,详尽细致地阐发了各家的观点。如谢有顺认为“张加强理解了另一面的江南。
他的文字,最有华彩之处,都在那些理解后的体悟、沉思和感怀上;他用理解,把江南历史上最珍贵的精神碎片一一缝合到了伟大文明的气场之中”。南帆形容柯平的“《书生论剑》之中的那些文人镶嵌在古老的历史之中,越退越远,渐渐成为绝响。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