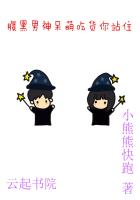2.语言所指与能指的断裂
在长期的现实主义写作模式中,语言的所能与能指之间已经建立起来了固定的近乎僵硬的对应关系,比如“太阳”、“土地”、“母亲”、“父亲”等等都有与之相配的隐喻对象。语言的定式与艺术形式的定式一样,会严重扼杀文学艺术创新的积极性。先锋作家的笔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固定联系被有意识的断裂、扭曲,造成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现实一种》中皮皮虐打弟弟时的情形:“禁不住使劲拧了一下,于是堂弟‘哇’地一声灿烂地哭了起来。”灿烂通常被用于修饰笑容、阳光,而在余华的创造中,它被用来强调哭的动作,这种有意识的能指与所指的错位,造成了读者阅读时巨大的阻碍,也带来了阅读时的延宕。诸如此类例子举不胜举,先锋作家们以充满个人经验色彩的语言使所指与能指之间产生了鸿沟,也使得语言拥有了无尽的可能性。
能指与所指之间的断裂,不仅出现在江南先锋作家的文本中,很多先锋作家都注意到从这一方面对写作常规定式进行突破。只是,这种突破出现在江南先锋作家笔下,除了写作常规定式的突破之外,又有了另外一重意义,即方言写作对于汉语普通话写作的冲击。由于北方、北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使北方语言也在中国的诸多方言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建国以后的为汉语普通话所规定的定义即是:
“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全国各民族能用的语言。普通话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着作作为语法规范。”在便于交流的前提下,将北方话作为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基础。众多作家用汉语普通话写作,并逐渐形成了汉语普通话的思维。文化的等级体制渗透在语言中,又通过语言对作家的影响扩散、渗透到了作家的身上。对于这些最初使用南方方言交流、思维,而后依照汉语普通话语法创作的作家来说,语言的转换之中包含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语言本身的范畴,它还隐藏着地域文化与文化整体之间的冲突、个人与体制之间的差异。当这些作家有意识的去将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进行割裂时,也同时体现着方言在文学写作的表达,虽然这些江南先锋作家并没有真正地使用吴越方言去进行创作,而是在语言中体现出了一种江南气韵。
正如余华在一次访谈中这样形容自己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语言风格:“尤其是我们浙江的作家,如果用我们家乡的语言来写的话,纸上就会堆满了错别字,北方人根本看不懂。我必须使用标准的汉语写作。所以那时我总在想,我怎样来完成这部小说。后来我对陈虹说,我找到了,就是越剧的唱腔。让那些标准的汉语词汇在越剧的唱腔里跳跃,于是标准的汉语就会洋溢出我们浙江的气息。”在作品的序言中,他这样总结自己的语言策略:“汉语的灵活性帮助了我,让我将南方的节奏和南方的气氛注入到了北方的语言之中,于是异乡的语言开始使故乡的形象栩栩如生了。这正是语言的美妙之处,同时也是生存之道。”从新文学的整体发展考察,创作性地将方言特色溶入文本语言操作实践的就不乏其人,而这种语言策略往往也多取得不俗的成绩。比如老舍对于北京方言的创造性使用,他的京味与其语言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另外张爱玲对于吴方言的提炼,赵树理对于晋方言的糅合等,都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也从不同角度,程度不一地为有着欧化色彩的现代白话文寻找民族化的途径。
3.形式的回归
先锋作家们在形式上的探索固然可贵,可是当他们在形式上越走越远时,与读者的接受能力、预期期待相距也越来越远。读者的反应引起了作者的思考,而在更大程度上追随西方理论的形式探索本身也带给他们沉重的压力。来自于外部与内部的共同压力,使江南的先锋作家们开始了形式上的重新探索,虽然这一次探索是以回归为其表相的,实质上却是形式上的又一次前进。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中国的先锋文学真正建立起来了体现中国精神的,属于自己的形式。
回归中最明显的是对于故事的重新发现。先锋文学初期在进行形式变革时,对于故事的注意力越来越淡漠。但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则是对故事有着特殊的钟情与偏好。于是先锋作家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创作中加入了“故事”的因素。只是他们的“故事”并非停留在复原“故事”本身,他们要赋予“故事”新的意义。因此在江南的先锋作家创作中比较集中地出现了“戏仿”。所谓戏仿,是指对某一种创作模式的形式上的模仿以及实质上的颠覆。在先锋文学的反叛阶段创作中,就有一些“戏仿”的作品,比如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格非的《敌人》对于侦探小说的戏仿,实质上却是侦探小说模式所体现的理性逻辑的解构。
“戏仿”本身就包含着一种对于旧有叙事形式的反叛。它不仅仅体现着一种技术上的变革,还包含了作家精神根基的改变。当先锋作家开始审视自己的形式发展极端时,依然利用了“戏仿”的手段,他们开始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的讲述:余华的《古典爱情》貌似一个才子佳人的温情故事,实质上却充满了血腥与冷酷;叶兆言的《状元境》仿佛是讲英雄美人,却给予了“英雄”最冷漠的嘲讽;苏童的一系列历史小说,《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借历史小说的形式却表达出了一种充满了个人色彩、充满了偶然性的历史观与历史发展。在这些后期的“戏仿”作品中,作者既照顾了读者的需要,也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既进行了形式的变革,又加入了传统的因素,不仅仅是“怎么写”,还将“写什么”带进了作品中,从而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局面。这时候“戏仿”即是激进的变革,又同时是对传统的回顾、审视,绝非简单的进步或者后退所能概括的。
随着故事的“复活”,人物也逐渐由抽象的符号变得逐渐丰满起来。余华的作品在经历了《世事如烟》对人物的抽象化与欲望化之后,开始了对人物的重新发现。从作品《在细雨中呼喊》开始,余华笔下的人物又重新鲜活起来。特别是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福贵、许三观都走进了一个新的境界。余华自己也认为:“在此之前我不认为人物有自己的声音,我粗暴地认为人物都是作者意图的符号,当我发现人物自己的声音之后,我就不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叙述者,我成为了一个感同身受的记录者,这样的写作十分美好。因为我时常能够听到人物自身的语言,他们自己说出来的话比我要让他们说得更加确切和美妙。”但是他们的人物也绝不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些人物形成了自足的世界,不再完全属于作者,也不只完全属于读者,他们体现着自己的世界与想象。
当故事和人物都有所改变时,作者的语言开始变得内敛。最能够体现这一特征的是苏童的语言,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的苏童的语言讲究意境,仿佛古典诗歌、传统山水画,葛红兵将这一语言特征定义为“意象性的语言”,并指出:“这种以意象性为基本特征的小说语式完全是苏童独创的,它对中国现当代小说来说是一份非常重要的贡献,它接续了中国古代诗词戏曲的传统,接续了中国古代文人画的传统,以一种书画同源的风格拓展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空间,而且在文学史上,第一次解决了南方作家如何在以北方词汇和发音为基准的现代汉语写作中参与文学语式之创造的重大问题。”而余华的语言也变得浅透、日常,却又显出一种特殊的越调韵味。通过语言,江南先锋作家们大都形成了自己的语言特点,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充满美感也能够为读者所接受的语言风格。
第四节与影视网络新传媒的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化、商业化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文学似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一呼百应的号召力,迅速地从中心位置滑向了边缘。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文坛忧心忡忡,各种各样的议论蜂起。但先锋作家特别是江南的先锋作家却用自己的行动对此给出了回答。他们生活在中国经济活动繁荣的江浙一带,而其所承袭的江南文化中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商业文化气息,所以他们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去接受商业化大潮的考验,并于实践中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首先,他们注重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尤其是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的结合。当商业化的步伐启动之时,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其中信息传播媒介的变化也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容。当影视将活生生的形象直接带到我们眼前时,当无形的电子网络仅仅靠电脑就能将无数信息传递给我们时,灯下阅读似乎就成为一种非常“奢侈”的怀旧行为。尽管我们至今仍执着地认为纸质的文本阅读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想象力,但如果文学无视这一切,拒绝必要的调整和改变,它无疑会失去了对现实呼应与影响的能力。90年代初中期,大批的文学期刊陷入了发展困境,一部分曾经有比较大影响力的文学期刊如《昆仑》等停刊,保留下来的期刊差不多也只是惨淡经营,不少刊物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直到现在这样的局面也没有根本性的扭转。
2007年,人民网“读书频道”为“‘文学期刊面临困境’的网上调查”所做的“编者按”中指出:“目前,在中国9000多家期刊中,文学期刊只占10%,即900多家,但文学期刊中生存状态较好的只有10%,不到百家。而在零售市场上有竞争力,能占有一席之地的大概也就不过10家。这些残酷的数字表明文学期刊生存状况举步维艰,纯文学期刊的不景气更早已是不争的事实。”而截止到2007年7月13日时,在参与调查的1268人中,有594人认为“文学期刊不会在不久的将来摆脱困境”,约占投票总人数的46%。而对这一问题感觉“说不准”的有355人,占投票总人数的28%,两者相加,对此问题不持乐观态度人占了一多半。而针对“你认为文学期刊遭遇困境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有276人选择了“报纸、电视、时尚类杂志冲击”,有246人选择了“互联网及网络作品冲击”,两者相加,共有522人,接近半数的参与者认为是新兴媒体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许这个调查还不够权威,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面对商业的冲击,文学的改变或许首先就需要从媒介上寻求突破。借助现代新兴的媒介,文学也许能保持并有可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文学所面临的整体性问题,当然也涉及一向以来以精英身份出现,甚至一度曲高和寡的先锋文学,它也不可避免地需要进行自我调适。
在与新媒介尝试合作方面,先锋文学是走得比较早的。早在90年代初期,为数不少的先锋文学率先与影视结缘。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影视无疑是20世纪以来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深刻影响的新艺术形式之一。而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文学就与影视艺术结下了不解的渊源。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起步之初就有不少文学作品被搬上了电影银幕。建国之后,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名着也陆续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根据鲁迅的《阿Q正传》、《祝福》,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等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都曾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新时期以来这种由文学作品到影视艺术的转换愈加丰富,曹禺的《雷雨》、《日出》,钱钟书的《围城》以及张爱玲等众多作家的众多作品都曾被改编或者是多次改编成影视作品。当90年代影视逐步地产业化、规模化之后,越来越多的当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开始受到影视艺术的关注。其中先锋文学作品因其题材的特异性,精神世界的复杂性受到了以“第五代导演”为代表的新锐导演们的青睐。苏童的作品尤其受到追捧,他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拍摄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0年),并获得了1991年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这部电影为张艺谋奠定了国际导演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