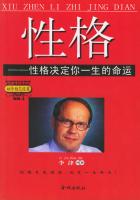二、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类型
1.中心城市辐射型
这是一个由增长中心向其外围地区发挥溢出效应(spill over effects)的过程。但和传统的增长极发展理论不同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如IMS‐GT,这是一个跨越国界的过程。在这种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参与方中,有一国或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与其相邻的其他地区,在产业升级和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有向边缘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寻求要素支持的需求,从而推动了区域一体化发展。这种区域经济圈的发展有可能导致城市圈和城市带的形成。如中国的长三角、IMS‐GT,以及珠-港-澳经济圈就是这一类。
2.自然经济区型
形成区域经济圈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具有自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比如语言、文化、地理特征以及经济的互补性,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经济部门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寻求经济合作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国的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等区域经济圈具有这一属性。
3.基础部门开发型
这是各国之间由于在相邻地区共同建设和使用基础部门的需要而进行的区域一体化合作。由于很多产业赖以发展的基础设施本身规模极为庞大,加上共同开发和利用能源、原材料等基础部门的需要,就促使国家或地区进行合作,共同进行基础部门的开发和维护,从规模经济中获取效益。如澜沧江-湄公河区域经济圈就属于这一类。
4.地理、政治协调发展型
这是各国由于地理上的相近性和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而进行的国际协作。
如果共同发展在地理上相邻的某一区域有利于维护相关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利益,或是区域一体化有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政治和经济中得到互利,那么相关国家和地区也会促成区域一体化的意向。如东北亚的图们江经济圈(“Growth Trianglesof South East Asia”Australia.East Asia Analytical U‐nit,1995)。
以上实际上是理论上的分类,现实中的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常常是同时兼有几种类型特征。
三、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结构特征
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结构特征以及促使其成功发展的主要因素为:
1.要素资源的互补性
要素资源的差异和互补有利于参与区域合作的各方更好地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这是促成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市场经济部门进行跨区域发展、启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最初动力。
2.地理接近性
尽管运输和通信技术在不断地进步,但是地理上接近性还是非常重要的。
地理上的接近性降低了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内部各次区域之间要素移动的成本,虽然在一些场合,对要素移动成本,最初也许并不是有关决策者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但由此引起的累积循环效应会使得产业集聚和扩散首先在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内部实现,并成为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
3.适当的政治协调
区域经济圈和成长三角最初的动力常常是市场经济部门的跨区域发展,但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在诸多政策上的协调依旧是促进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部门需要加以协调的几项重要政策有:投资政策;人员流动政策;贸易和商品流动政策;金融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社会发展政策;发展的规划协调;等等。社会发展政策和发展规划协调在国内区域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4.良好的基础设施
共同建设和管理良好的基础设施(包括生产和生活设施),是吸引国内外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缺乏这一点,将使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缺少内外投资的吸引力,进而失去进行区域内合作的基础(汤敏,1995)。
四、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成长三角(IMS‐GT)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成长三角,简称IMS‐GT,由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以及西苏门答腊省组成。作为东南亚最早出现的成长三角,IMS‐GT被看成是次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典型。
建立IMS‐GT的设想由新加坡首先提出。新加坡之所以倡导IMS‐GT,其原因主要有:(1)地价昂贵,期望利用柔佛州和巴淡岛廉价的土地资源,扩展经济活动空间。(2)劳动力价格较高,设想利用柔佛州和巴淡岛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3)淡水资源短缺,新加坡多年来一直靠马来西亚的柔佛州供应淡水,因而希望通过实施“成长三角”计划,增加柔佛州对其的供水量,并从廖内群岛获得新的水源。(4)美国取消了新加坡的最惠国待遇,因此新加坡想将部分企业转移到邻近的柔佛州和廖内群岛,以继续享受最惠国待遇(魏燕慎,1998)。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对新加坡的倡议做出积极响应也是各有所需。从马来西亚方面来看,柔佛是其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州之一,在马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进一步发展需要巨额的资金。参加“成长三角”计划,柔佛州可在资金和技术方面得到新加坡的帮助。从印度尼西亚方面来看,早在1980年就同新加坡签署了协议,合作开发巴淡岛,但进展一直不大。因此,印度尼西亚期望通过参加“成长三角”计划,加快巴淡岛的开发进程,进而促进整个廖内群岛的经济发展。
在IMS‐GT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有效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4年12月17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成长三角经济合作多边协议》,该协议对IMS‐GT的合作与协调机制做出了明确规定,认为政府部门的作用是支持、鼓励和促进合作项目的实施,并采取措施促进人员、信息、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还规定了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工作组、工商会议和工商理事会等机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层次的协调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会议,制定政策并监督政策的实施,协商和解决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第六节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构框架和基本属性
本节将以与IMS‐GT比较分析的形式,结合本章前几节有关成长三角和区域经济圈的理论分析给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结构框架和基本属性。
长三角指的是以上海为中心,以浙江和江苏为南北两翼的长三角地区。按照中国的长三角区域规划所框定的长三角区域范围是由包括上海全市、浙江省北部7市和江苏省中南部8市在内的16市组成。而一般意义上的长三角是指上海、江苏和浙江两省一市。
由于长三角的组成部分同处于一个主权国家的同一地区内,因而它和跨国的成长三角具有不同的制度背景。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对IMS‐GT进行过研究,但大多关注于这一理论对粤港澳地区的区域合作的借鉴意义。因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看,粤港澳地区的经济合作可能更像IMS‐GT。
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地方分权形成了地区间的相互竞争,引发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不同行政区域间合作的缺失和相互排斥。因而长三角各省市之间虽然不存在如IMS‐GT或其他亚洲成长三角中遇到的贸易和投资的国际障碍问题,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省际壁垒。因此,在解决要素的自由流动方面,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和IMS‐GT或其他亚洲成长三角所面临的问题是相同的。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殊背景来源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由此在市场利益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方面形成了两个独特的层面:一是企业主体,其中包含大量参与竞争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主要受制于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二是地方政府主体,目前其职能权限被界定过宽,市场功能依然十分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市场的利益主体和竞争主体。因此,在体制转轨时期,地方政府主体经常代替企业主体进行决策。在这种制度结构下的市场竞争,其目的必然是寻求地方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垄断利益最大化,或地方行政区域边界内的垄断成本最小化:一方面要防止区域内利益“外溢”;另一方面,最好是由其他主体承担区域内发展成本(刘志彪,2002)。
希望通过区域经济合作这样的一体化行为来获取周边地区的资源,或者通过一体化行为让周边地区来分担本地区的发展成本,这构成了地方政府层面的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同时,地方政府部门希望维持对本地区资源的垄断,防止本地区资源的外溢,这又构成了地方政府层面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障碍。这种制度安排和动力结构成为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殊意义所在。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但长三角江、浙、沪三地的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表现出对各自相对独立的地方利益的重视,以及围绕这些利益展开的合作与非合作的行为,是比较适合于采用成长三角的分析框架加以研究的。
从中央政府制定的2005-2010年长三角区域规划的范围来说,率先在长三角地区16市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可能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由此观之,上海、浙江部分地区和江苏部分地区的一体化,在形式上便相类似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组成的成长三角。
在中国转型经济的背景下,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指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长三角地区各次区域采取措施,逐步撤除限制本地区资源向域外流动的各种壁垒和障碍,实现产品和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使区域经济整体化倾向不断深化的客观进程;第二,长三角地区各次区域通过交流、会谈、协商、协议等形式在包括向区域内提供协调一致的公共产品(如全区域协调的规划、政策、规章制度、规范、标准等),以及社会资本的整备方面采取联合和合作的行为。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概念的内涵,是随着体制框架结构的变化而迁移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体制变化的函数。
在中央计划经济环境下,不存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整个中国经济都在中央计划体制框架内运行,地方经济调控机构是中央计划调控机构的分支机构和中继站,区域经济就是行政区经济,是中央计划经济体系中的基本没有独立意义的子系统。
1978年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地方分权开始的,改革最初的步骤是将经济调控的重心(计划的重心)从中央下放到地方,是财政分灶和地方分权,于是中国经济带有了“诸侯经济”的特点。在这种体制框架下,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开始有了最初的意义。20世纪90年代,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际,人们提出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概念。在当时的地区利益格局下,上海和周边省区对一体化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来的情绪涨落的主要标准,是在体制框架内如何利用一体化来获取更多的资源以达到实现本地区经济增长优先的目标。对上海市来说,一体化意味着能够支配更多的资源,或者说能在长三角地区确立上海的优先和中心的地位。对周边省区来说,一体化则意味着能分享中央政府给上海的各种优惠政策,以加快本地经济建设步伐。当时所谓的一体化的内涵,更多的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力量和行为,希望长三角区域内部各次区域的政府部门能够采取协商、协调以及其他博弈行为,分享彼此的资源,解决彼此间的问题,包括经济发展过程中因彼此相邻而产生的利益分配和冲突等。一体化的载体和成就是出现了一系列诸如市长会议、省级领导互访之类的组织和行为,建立了某种程度的谈判机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有了更深刻的内涵:首先是在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的互动过程中区域内各次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产业区域转移、要素流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区际产业分工也开始浮出水面,特别是当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地方政府转向企业(主要是指具有市场经济行为属性的各类企业)后,各次区域中的经济主体要求消除行政区域边界的壁垒,推动商品和要素资源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实现相互开放和相互融合的愿望开始在经济行为中强烈地表现出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也就由过去的相邻的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谈判机制,协调解决彼此的利益分配、利益共享和利益冲突问题,变为由市场经济主体主导的次区域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客观趋势和各级政府部门为顺应这种客观趋势而采取的消除妨碍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壁垒,提供区域协调的公共产品,促进区域经济进一步紧密化的主观行为。
20世纪90年代初,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和载体是地方政府部门行为和组织,即由各次区域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建立谈判和协调机制。
受当时经济体制框架的制约,这种行为和组织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