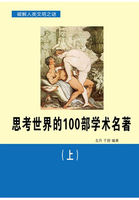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缺乏与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文学翻译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往。直到19世纪中叶,才开始零星介绍外国文学作品,而我国翻译文学的真正产生,则是在清末民初了。
在清末民初,文学翻译尚处于开创时期。文学翻译如同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最初的繁荣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当时的各具特色的文学翻译,使得中国文学找到了一条与世界文学接轨的重要渠道,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文学创作的发展,加速了传统文学观念的消解以及近代文学观念的生成。可见,文学翻译在我国新文学的发展以及整个文学的变革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正如陈平原所指出的那样:“域外小说的输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文学结构内部的变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发展的原动力。可以这样说,没有从晚清开始的对域外小说的积极介绍和借鉴,中国小说不可能产生如此脱胎换骨的变化。对于一个文学上的‘泱泱大国’来说,走出自我封闭的怪圈,面对域外小说日新月异的发展,并进而参加到世界文学事业中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特别是在关键性的头几步。”在翻译文学开始萌芽、茁壮成长以及与我国民族文学融会的过程中,浙籍作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尤其是狄更斯、笛福、契诃夫这些外国着名作家和经典名着,都是被浙江译家以文言文“意译”方式首次译介到我国。这些作品对我国文化界产生了极为重要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清末民初时期,浙江翻译文学呈现出良好的开端,主要以“蠡勺居士”(蒋其章)、魏易、沈祖芬、吴等人的突出成就为代表。
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应该始于近代。
确切地说,始于19世纪70年代。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虽然有汉语译作偶尔出现,如《意拾寓言》(1840)、《天路历程》(1853)等,但是,《意拾寓言》的译者是英国人罗伯特·汤姆,《天路历程》的译者是外国传教士,所以,这两部译作都不属于中国翻译文学。
因为中国翻译文学是指“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译的外国文学作品”。而被誉为我国第一部翻译小说的,是1873年初开始刊载的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昕夕闲谈》分26期于1873到1875年发表在上海的月刊《瀛寰琐记》上。发表在该月刊1873年1月的第3期至1875年3月的第28期上面。每一期上刊登两节,一共是52节。在28期之后,由于月刊更名,同时形式也作了调整,这部翻译小说的刊载也就终止了。1875年的晚些时候,增补了三节,并以书的形式出版。这本小说的英文原名没有被译成中文,而译者也是署的笔名“蠡勺居士”。根据美国哈佛大学韩南的研究和考证,《昕夕闲谈》的译者便是浙江人士蒋其章。蒋其章生于1842年,籍贯为浙江钱塘,1870年乡试中举之前是杭州府的廪生。1877年在会试中金榜题名,之后曾被任命为敦煌县县令。
《昕夕闲谈》这部小说是通过一个贵族的私生子康吉的生活经历,描写了法国波旁王朝后期伦敦和巴黎上流社会的光怪陆离的生活场景和种种丑恶现象。译者为此所作的《昕夕闲谈小叙》表达了他的翻译目的是“启发良心,惩创逸志”,译者在该文末尾进一步写道:“今西国名士,撰成此书,务使富者不得沽名,善者不必钓誉,真君子神采如生,伪君子神情毕露,此则所谓铸鼎像物者也,此则所谓照渚燃犀者也。”在“蠡勺居士”蒋其章之后,为我国翻译文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便是林纾了。在我国近代翻译艺术史册中,林纾(1852-1924)的翻译独树一帜,但是,翻译家林纾虽然译出的小说达一百七十多部,但他本人不懂外文,全仗合作者选材和口译。在十多位合作者中,以浙江译者魏易最为突出。在林译世界文学名着中,由魏易选定并担任口译者即达数十种,其中,英美文学名着就有英国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滑稽外史》(即《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贼史》(即《奥利弗·特威斯特》)、《冰雪因缘》(即《董贝父子》);英国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英国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即《格列佛游记》);英国兰姆改编的《吟边燕语》(即《莎士比亚的故事》);美国华盛顿·欧文的《拊掌录》(即《见闻札记》);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等。
更何况林纾自己的翻译活动也与浙江翻译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林纾虽然出生于福建,但是在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之后,他曾告别故乡,举家移居杭州,在杭州居住了三年之久(1898-1901)。在此期间,林纾翻译了第二本西洋小说——美国女作家斯土活(Harriet Beecher Stowe)的《黑奴吁天录》,奠定了他自己的翻译事业之路。1900年,他在杭州与魏易(1880-1932)合作,从杭州的求是书院借到英文版《黑奴吁天录》,由魏易口述,他执笔记录,把《黑奴吁天录》翻译成书。林纾为此书写了一序一跋,把书中所描述的美国黑人遭受奴役之事,与当时美国歧视、虐待华工的浪潮联系起来,从而警示国人,将文学翻译事业当成了维新改良的政治追求,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对于中外文化交流有着独特的意义。
在杭州,浙江译者不仅翻译了第一部美国小说《黑奴吁天录》,而且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丹尼尔·笛福的代表作《鲁滨孙漂流记》也是第一次由浙江译者沈祖芬翻译的(书名被译为《绝岛漂流记》)。此外,俄罗斯文学中的莱蒙托夫、契诃夫、高尔基等重要作家的作品,也都是由浙江译者吴(1880?-1925)首先译介成中文的。
与此同时,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也都是跨越晚清和民国文坛的着名翻译家。鲁迅自1903年开始自己的翻译活动,翻译了法国作家雨果的随笔和凡尔纳的《月界旅行》等作品。周作人则在1904年就开始翻译《侠女奴》等小说。尤其是1909年周氏兄弟合作选译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是我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成就。
除了小说以外,诗歌翻译方面在浙江也有一些零星的成果,如陆志韦翻译的英国诗歌。陆志韦(1894-1970),原名保琦,后以字行,浙江吴兴人,他在大学时代翻译诗歌,主要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着名诗人丁尼生的《哀波兰》(1913)、《波兰革命行》(1913),以及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贫儿行》和《苏格兰南古墓》(1914)等。英国诗歌的简洁流畅的用词风格和直抒胸臆的真挚情感,给我国诗坛带来了启迪和灵感,同时,从《哀波兰》、《波兰革命行》等译诗可以看出,当时的诗歌翻译是基于爱国主义思想的,是服从于争取民主自由的现实斗争需要的。
鲁迅早年在留学日本时(一般认为是在1906年左右)也曾翻译了外国诗歌,即用骚体翻译了两首海涅诗歌。该译诗最早由周作人收入到自己的一篇题名为《艺文杂话》的文章里,1914年2月刊发在上海的杂志《中华小说界》第二期上。鲁迅翻译的两首诗《余泪泛澜兮繁花》和《眸子青地丁》,均取自海涅1823年出版的《抒情插曲》(LyrischesIntermezzo),是其中的第二首(即《从我的眼泪里》)和第三十二首(即《蓝色的紫罗兰》)。
诗歌翻译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应时(溥泉)(1886-?,浙江吴兴人)所翻译的《德诗汉译》。全书共收入戈德(歌德)的《鬼王》(今译《魔王》)、翕雷(席勒)的《质友》(今译《人质》)、哈英南(海涅)的《兵》(今译《两个掷弹兵》)等10位诗人的11首诗歌,诗集前附有译者所撰写的《德诗源流》等文,以德汉对照形式编排,于1914年1月在浙江印刷公司印刷发行(该书并于1939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再印)。应时在选择诗人诗作时还是很有眼光的,他选择的诗人都堪称德国诗歌史上的代表人物,他选择的诗歌也大多为名篇。这部诗集也是我国第一部译自德文的诗集。
可见,清末民初时期,浙江译者为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以及翻译艺术的拓展所作出的贡献是十分显着的。
其次,清末民初,一些刊载外国文学译文的杂志在杭州创刊,推动了浙江翻译文学的发展。其中包括《译林》(1901)、《环球丛报》(1906)、《杭州白话报》(1895、1901)、《英语学杂志》(1908)等。尤其是《译林》杂志,于1901年3月5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在杭州创刊,林琴南、林长民、林白水、魏易等担任主编,共出版了13期,以翻译日本作家的作品为主,包括清浦奎吾(1850-1942)的《明治法制史》、织田一的《国债论》、镰田荣吉的《欧美漫游记》等重要着作。《译林》序言中说:“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尽管该杂志不是纯文学刊物,但是名人传、游记等栏目还是具有相当的文学性的。
最后,一些浙江学者在外国文学的理论研究和评论方面为浙江翻译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03年,鲁迅在《斯巴达之魂》的译序中就明确指出,他之所以翻译这篇历史小说,是因为被其生气所感动,想通过译介这部作品来激励中国爱国之士能够“掷笔而起”。可见,他在此所强调的是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
然而,1907年,鲁迅又写了题为《摩罗诗力说》的重要文学论文,论述了拜仑(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密茨凯维奇等“摩罗”诗人之后,又专门介绍了裴彖飞(裴多菲)等作家的创作。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在强调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的同时,又兼顾文学翻译的审美功能。
王国维(1877-1927),浙江海宁人,在1905年《教育世界》第96期上发表了《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在该文中,王国维陈述了新词语产生的必然性,对外来新词语在我国的传播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认为在现代社会,“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于是有了新学语的涌进。他认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他虽然所论及的是哲学翻译问题,但是,对翻译中语言问题的看法是很有见地的。
而浙江定海人胡以鲁(1888-1917)则是把西方语言学理论系统引进中国的第一人。他在译名方面,提出了译名的规范化以及意译和音译问题。他在1914年所写的《论译名》一文中,虽然力主意译,提出了“以义译为原则”的诸条要求,但也提出了不妨音译的十类词。这些都表明,术语的制定与规范化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他主张既不一概排斥日本新名词,又主张对这些新名词作具体分析,认为那些“不合吾国语法者”,“义虽可通”,也不宜袭用。
浙江绍兴人蔡元培(1868-1940)则提出了相对系统的译学理论。他提出了“横译”、“纵译”与“一译”、“再译”之说。他称异域语言的翻译为“横译”,古今语言的翻译为“纵译”,由意识而为语言为“一译”,由语言而为文字,则是我国当时言文不统一时所独有的“再译”。这一说法,也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的一个依据。蔡元培的译学思想“充满哲理,发人所未发”。受到译界的关注。
最后必须提及的是张元济(1867-1959),他是浙江海盐人,为我国翻译文学最初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张元济先生1898年因参与戊戌维新运动而被革职,以后去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1901年投资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长、经理、监理,1926年后任董事长。张元济在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以及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时,不遗余力,是翻译文学出版事业的积极的开拓者,正是在他的主持下,“林译小说”等许多外国文学作品才得以面世,从而为我国的翻译事业以及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清末民初的浙江翻译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开端,不仅为中国读者打开了世界文学的窗口,拓展了视野,同时也为英美文学以及俄罗斯文学在我国的流传和接受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开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