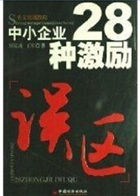问题还在于这些状况到了80年代中期,仍对浙江农村具有较大负面影响。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1984年的10村调查表明,其中有5个村的党支部,思想上还受着“左”的束缚,对“放宽搞活”政策很不理解。他们把率先致富的专业户看成“不三不四”,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活动当作“投机钻营”,把农业以外的经营收入视为“不劳而获”。他们认为传统农业是“正道”,办工业、搞商业、贩运,是“走邪道”。湖州市郊永丰村曾经是经营传统农业的先进单位,全村没有工业,没有商业,党支部书记张和青对此沾沾自喜,说“我们村没有村办工业,只有运输队,是靠劳动收入,门道正,不会错”。鄞县庙堰村承包大户张善龙,土改时被划为大佃农,十分怕变,1983年承包耕地21亩,净收入11500元,“生产再忙也不雇一个帮工,而且再也不肯多包1亩土地。”发展多种经营势必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这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发了相当多的争议,可以看到“以粮为纲”的影响依然存在。人们针对多种经营调减粮食种植面积,以及粮食减产,议论纷纷,怀疑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是否“过了头”。
当时在中共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的何土洪着文指出,确实存在着对于粮食战略地位认识不足的问题,但这是前进中的问题。1985年全省调减下来6.7%的粮食播种面积、11.4%的棉花播种面积,75%种的是一年生经济作物,取得了油菜、络麻、菜、瓜果等经济作物增产18%的成效。实践证明,这种调整是正确的、必要的,种植业正在向着进退裕如、丰歉调节的弹性结构发展。现在调整还刚刚开头,所谓“过头”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三)拨乱反正
所以说,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中共浙江省委提出“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其实并不是对于传统发展模式的突破,只能说是破除无知和盲从的极左思想,重新回到传统农业的正常轨道上。然而就是这一理性回归,却是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业发展进入新时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起点。从此,浙江农业渐入佳境。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林彪、“四人帮”反对商品经济,把发展多种经营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出现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很奇怪的论调。如“抓钱丢纲”,农民富了会变修,“抓粮食保险,搞多种经营危险”等。粉碎“四人帮”以后,虽然批判了他们推行的那套思想路线,但仍有人心有余悸,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商品经济。然而只有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壮大浙江的经济力量。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才能在人均耕地很少的情况下,尽快让农民富起来。
当年,绍兴县上旺大队人均耕地仅0.44亩,他们把全大队1400亩荒山全部种上了茶叶、树木、毛竹,办起了茶叶加工厂、畜牧场,收入大幅提高,集体建造了社员新村,户户搬进了新房。笔者曾于1979年去过上旺大队,群山环抱之中,绿树掩映之下,一幢幢两层小楼组成的社员新村,让我们顿时看到了明天的希望。要知道,这时的浙江省,相当多的城市居民的居住面积都相当小。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是落实党在农村经济政策的重要抓手。林彪、“四人帮”破坏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的原则,鼓吹取消自留地、家庭副业,抹杀集体经济的自主权,严重破坏了集体经济和多种经营。因此,发展多种经营,首先就必须落实政策,要求广大干部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纠正违反党的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的“土政策”。当时省委重申在不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社员有权经营家庭副业。可以自行安排自留地种植作物品种,可以发展畜牧业,也可以发展编织、刺绣、采集、渔猎、养蜂等,允许社会员自行销售产品。
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也是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当时东阳县六石公社的调查,1980年,这个公社人均耕地0.67亩,整半劳动力9135人,根据历史上出勤状况计算,实际消耗在农业上的用工,1977年128万工,1978年156万工,1979年134万工,平均每个劳力全年出工数分别为146天、180天和146天,如以每个劳力全年出工300天计算,则三年平均每人每年就有剩余劳力143天,占全年可出勤天数的47.7%,按此计算,全公社剩余劳力4353人,几乎是全部劳动力一半。因此,只有广开生产门路,才能妥善解决好剩余劳力问题。
1981年8月,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发展农村多种经营若干问题的通知》,就发展农村多种经营问题提出10条意见。提出要解放思想,扩大思路,克服“单一经营”的狭隘观点,树立大农业和大粮食观点,全面发展农村经济。
这一通知还强调指出,发展多种经营,是繁荣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性措施。
并提出要发挥集体和个人两方面积极性,有计划地建设各种商品基地,组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疏通流通渠道,促进商品交流,进一步搞活经济。
发展多种经营举措在短期内就取得了较好成效。1978年至1982年,在全省农业种植业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7%的情况下,林业、畜牧业、副业和渔业增长更快,农业产业结构大大优化。1978年,纯农业产值占浙江农业总产值的63.5%,1982年则下降到55.3%。与此同时,副业比重大幅上升,从1978年的13.1%,上升为1982年的23.4%,上升了10.3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对于推进制度变迁,对于农村、农业和农民,都产生了深远的积极意义。
第一,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改革开放初期,绍兴县自嘲是“稻草加稻谷”经济,农业产业结构十分单一。而到了80年代初期,这种局面已大为改观。农业总产值当中,林牧副渔业比重大大提高;农业种植业当中,粮食比重有所下降,农村产业结构趋于合理。
第二,强化了农民主体意识。1979年的时候,浙江尚未普遍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然而通过发展多种经营,至少农民在自留地,以及其他零星地块上,已经初步有了种植自主权。而在以前,即使是自留地,有些也统一由生产队安排种水稻。在那一时期,《浙江日报》不时会有农民抵制不合理种植安排的报道,并组织一些范围很广的讨论,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形成了农民最初的创业资金。农民家庭最初的创业资金,有相当一部分直接来自于多种经营收入。1981年,瑞安市金后村创办第一个合股企业,用废塑料再生加工,生产塑料编织丝,主要资金就是来自于村里的手艺人和货郎担走南闯北做小生意等劳务所得,而这显然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广义的多种经营收入。
三、从传统走向现代:率先实施市场化取向的效益农业
中国人是被饿怕了。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史,或许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人挨饿的历史,所以我们对粮食特别敏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农村起步的改革开放,对于农业生产领域的计划经济却一直较少触动。然而指令性计划之下的农业生产却由于难以实现要素最佳配置,因而导致效率损失;而市场化之下的要素最佳配置,能以少量耕地取得最大产出,且与其他地区形成优势互补,无疑是浙江农业的出路,同时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计划经济的“粮食堡垒”逐渐突破
农业发展模式创新和转型,还需要突破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对于粮食发展的束缚。然而由于粮食作为战略资源的特殊性,导致农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长期较难突破。
即使在中共浙江省委要求大力发展多种经营的1979年,“以粮为纲”政策仍未有较大松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1979年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说:“粮食是农业的主体,任何时候都要抓得很紧很紧,从全省来说,必须坚持以粮为纲”虽然这个时候的“以粮为纲”,与“文化大革命”时的“以粮为纲”已有本质区别,但至少这一口号仍在使用。
不过在当时形势下,仍然把粮食生产提到如此的高度,很可能也是一种唯一的选择。一是思想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二是当时全国粮食产量仍然不高;三是难以在国内外的范围内大规模采购粮食,这既是由于缺少必要的资金,也是为当时的内外贸体制所不允许的。所以也不能说当时的领导就是小农思想挂帅,有很多问题是他们的主观努力难以解决的。
由于推行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效率空前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增长。1984年,浙江粮食生产大丰收,总产量达到创纪录的1817万吨,比1983年增长14.8%,比产量较高的1982年也增长6.1%。
有意思的是,自此以后,浙江的年度粮食总产量均在1700万吨以下。当时全国普遍实现了农业大丰收,一时之间如何消化粮食成为报纸杂志的热门话题。
然而对于粮食生产,指令性计划的管理体制一直没有松动。播种面积有指令性计划,收购、销售及其价格均有指令性计划。虽然不再说“以粮为纲”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了“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的要求。这样的提法按理也没什么不对,因为任何一项经济工作都是不能放松的,问题是把粮食生产政治化,成为一块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区,成为走向市场化之中的一块“飞地”,就令人深思了。
所以只要认识没有根本转变,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强调粮食生产的问题。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省内抓粮食的声调又高了起来。有人指责“沿海可以进口粮食”这样的重大政策措施是不对的,要求“全党、全社会、各部门、各行各业重视农业”。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除了少数相关部门、相关行业外,大家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是对农业的最大支持,不可能所有的部门和行业都来重视某一项特定的工作。把农业提到这样的高度,最后得到的只能是一种哲学式的空洞重视,难收实际效果。
实际也表明,1989年要求“全党、全社会、各部门、各行各业重视农业”,并没有收到实际成效,是一场典型的农业秀。1990年至1992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比1989年有少许增加,但产量则除了1991年外,并未有较大增加。
与此同时,农业产业结构则出现了短暂的固化。这三年,粮经比例一直大致保持在74∶26的较高水平。
到了1995年,提出农业的工作重点要坚持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千方百计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强调“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要升温”。这时,全省粮食播种面积已经在1992年的水平上大幅减少,仅为1992年的88.9%,且这种状况已持续三年。不过粮食减产幅度则较小,1995年的粮食产量为1992年的92.1%,说明在播种面积减少情况下,单产有了一定的提高。这时还强调“经济强县首先应是农业强县、粮食强县,各地务必将总量保定购、保调拨、保供应”。这显然也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式的要求,如果这样的要求可以推而广之,那就没有区域产业差异,没有区域特色经济,也就没有要素最佳配置了。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关于粮食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松动,这时出现了一种以确保生产能力为主的政策主张。这里的理论根据,就是粮食主要是半年生禾本作物,只要保持一定面积的耕地,短期内就能使粮食产量达到一定水平。这一思路的特点,是不拘泥于年度种植面积和产量,关键是保证一定面积的耕地。这样,问题转变为到底确保多少数量粮食的生产能力,1998年前后,曾提出过确保200多亿斤生产能力的要求,这相对于直接抓面积和产量,显然是一个政策上的进步。
对此,魏芳勋和杨耀光于2000年提出了一个具体设想。他们认为,建立浙江粮食安全体系的总体框架是:确保2000万亩耕地,其中,标准农田1000万亩、现代设施农业基地200万亩、以养奶牛为主的牧草基地100万亩及一般粮田700万亩。在2000万亩耕地中,除100万亩用于牧草基地外,使其余1900万亩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310亿斤,200万亩牧草(其中,100万亩耕地、100万亩退耕还牧坡地)相当于30亿斤饲料粮生产能力,250万亩木本粮油基地(“九五”期间150万亩加上“十五”期间100万亩)相当于5亿斤的生产能力,总计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345亿~350亿斤。
2008年,浙江省政府提出,“全面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
显然,政府关于粮食问题的政策主张,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即不仅要强化粮食生产能力,还要提高经济效益。省政府提出“十百千万示范工程”作为保障措施,即在全面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的基础上,全省重点建设10个水稻高产创建示范县(市、区)、100个示范乡(镇)、1000个示范方,继续开展水稻优质高产万村示范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