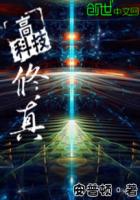这种对比在第二十三回起的连续几回中不下三四次之多。它们不是稍纵即逝的无意间的感情流露,而是作者郑重其事的精心铺叙。前一回退职回乡的杨尚书、乡绅李大郎和拾金不昧的小户农夫祝其嵩都是这个世外桃源中的代表人物,作者意在包括从上到下各个阶级。小说大多数篇幅的社会现实的生动刻画自然成为它的对立面。这个今昔对比也即作者身处乱世所怀的幻想和明末黑暗现实的对比。类似《老子》所描写的小国寡民的淳朴农村成为作者心目中的廉价乌托邦,它不是作者苦心经营的理想蓝图,而是现成的借用。归真返朴,回到明朝盛世,以至唐虞三代,当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但作者之意在于鞭策当世,这是他的可取之处。作者署名西周生可以如同《引起》的结尾七律所说:“关关匹鸟下河洲,文后当年应好逑。岂特母仪能化国,更兼妇德且开周。”它以《诗经·关雎》篇旧注所指的西周文王的夫妇之道作为纠正书中恶姻缘的模范,这是它的狭义;它的广义则在于第二十六回所说:“这明水镇的地方,若依了数十年先,或者不敢比得唐虞,断亦不亚西周的风景。”政治、经济以至社会风俗习惯都包括在内。可见婚姻问题只是作者所关心的社会问题的一个侧面,不是全部。它的批判的锋芒所指正是明末社会的各个方面。
就数量而论,悍妇故事在全书所占比重不及它用于反映其他社会问题的篇幅。长篇小说的结构,从来有两种。一是严密的有机组织,较大的情节和它的前后文因果相连,任何局部的改动都会影响全局。《红楼梦》
是它的典型。另一类小说,它的每个部分各有相对独立性,彼此之间关系松散,或增或减,对整体影响不大。它同西方以历险记为名的一类小说中的多数作品同属一个类型。《西游记》的八十一难与此类似。只要凑足数目,各个难的具体故事大体符合唐僧师徒的个性就行,这样写,那样写,关系不大。《醒世姻缘传》介于以上两类小说之间。作为第一个类型,它和恶姻缘很少有关的相对独立的故事可说已经多到喧宾夺主的地步;作为第二个类型,它的恶姻缘却又俨然是全书的中轴。主宾分庭抗礼的这个独特结构正好配合作者的基本构思:婚姻问题只是作者所要探讨的社会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整体。
就质量而论,悍妇故事大多数陈陈相因,平庸无新意;精彩处极少;粗俗不堪的情节不时可见;出人意料的是全书比较成功的描写反而多半和悍妇故事无关。这是作者基本构思的又一证明。
第六十二回狄希陈捉弄友人张茂实,使他误以为妻子不贞,引起一场殴打。接着下一回,张茂实妻假手于悍妇,向狄希陈进行报复。虽然境界不高,而情节紧凑,有一定的喜剧性。可惜在本书所有的悍妇故事中,连这样短中见长的片段也不多见。
第六十六回,狄希陈在宴席上被友人拉住手臂强留,深恐悍妇怪罪,拿刀割断手臂才得脱身而去;第七十六回猴子抠损悍妇的眼鼻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片段,情节离奇而不合事理,形象丑恶,趣味索然。这些都是为宣扬迷信果报而粗制滥造的章节,它们说明作者构思悍妇故事已经技穷于此,再也写不出一点新意了。
然而《醒世姻缘传》并不缺少精彩篇章,它们是和悍妇无关的揭露社会黑暗的一些场景。如第六十七回医生为敲诈病家,用药使病情恶化,然后进行勒索,最后被识破的狼狈情况;第八十到八十二回,刘振白乘人之危,借机敲诈,步步进逼,却落得人财两空的故事。它们都是以前长篇小说中未经涉足的领域,开后来谴责小说的风气之先。
晁秀才捐了一个监生,碰上官运亨通的老师,一举选上大县的肥缺(第一回),后来又通过戏子走上太监的门路,升为京畿重地北通州的知州(第五回)。被判处死刑的他的儿子宠妾,上下行贿,公然将监牢改装成藏娇的金屋(第十四回)。这些描写夸张而不失真,怪诞而言之有据,它们为极端腐败的明末吏治留下有声有色的记录,成为后来《官场现形记》的先声。又如第十回县官下判:“也免问罪,每人量罚大纸四刀。”什么叫大纸?
原来按照旧规,每刀折银六两。“六八四十八,共该上纳四十八两。库里加二秤收,又得十两往外”,非六十两银子不能对付。前文所引今昔对比的那段话:“不似如今问了罪,问了纸,分外又要罚谷罚银。”所谓问纸,只有联系第十回才能理解。细枝末节真实到如此地步,简直可以作为史料看待。又如第八十三回官员穿戴衣帽靴子的通行顺序,第八十四回皮帽匠人的作弊手段,都是当时社会风习的忠实记载。而第四回的童山人、第三十五回的汪为露等人物,又给后来的《儒林外史》以有益的启发。
作为社会问题小说,《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并不满足于栩栩如生地揭露社会黑暗,他还要探索这一切不合理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应该怎样加以纠正或消除。天地之间怎么会有恶姻缘?狄希陈的前生晁源射死了狐狸,狐狸投生为薛素姐,她变成狄希陈的凶老婆。作者提出了问题,然后又自己作了解答。晁源的父亲是赃官,为什么倒有一个遗腹子,替他重振门庭?因为晁夫人乐善好施。可是这里留下一个漏洞:老爷做尽恶事,是不是只要夫人积下“阴功”,就足以挽救?第二十一回有一段韦驮尊者的话可以看出作者为什么这样安排他的书中人物的命运,而自以为公正不阿:“晁宜人在通州之年,劝她的丈夫省刑薄罚;虽然丈夫不听他的好言,他的好心已是尽了。这六百两的米谷,两年来也活过了许多人,往后边的存济正没有限量哩,不可使他没有儿子侍奉。”这一段话又在第二十二回重复出现,足见作者对它的重视。其实这六百两银子以至后来施舍了的更多的田地财产都不过是贪赃枉法的部分所得。为什么好端端的明水镇突然会被洪水淹没?因为居民奢纵淫佚,得罪于上天。总之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作者没有科学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高超理论作为凭借,他只是敷衍塞责地从轮回果报中找到现成答案,用不着自己动脑筋。尽管上面已经指出,这个解释有不少破绽,难以处处自圆其说。它往往偏袒有权势的上层人物,实际上是在替他们辩解,提供借口,减轻或豁免他们的罪责。
如果小说作者的探索仅仅到此为止,那就和封建迷信的《玉历至宝钞》一类通俗说教书没有区别了。
《醒世姻缘传》如实地反映了明末政治腐败,特别是各级地方衙门贪赃枉法,土豪劣绅和流氓地痞在他们庇护下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的种种情况。作者指出政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宦官擅权。书中的太监头子王振正是现实中不可一世的宦官魏忠贤的投影。作者愤愤不平地在第十五回提出他的除奸大计:
依我想将起来,王振只得一个王振,就把他的三魂六魄都做了当真的人,连王振也只得十个没卵袋的公公。若是那六科给谏、十三道御史、三阁下、六部尚书、大小九卿、勋臣国戚合天下的义士忠臣,大家竖起眉毛,撅起胡子,光明正大,将出一片忠君报国的心来事奉天子,行得去,便吃他俸粮,行不去,难道家里没有几亩薄地,就便冻饿不成?定要丧了那羞恶的良心,戴了鬼脸,千方百计,争强斗胜的去奉承那王振做甚?大家齐心合力,挺持得住了,难道那王振就有这样大大的密网,竭了流,打得干干净净的不成?却不知怎样,那举国就像狂了的一般,也不论什么尚书阁老,也不论什么巡抚侍郎,见了他,跪不迭的磕头,认爹爹认祖宗个不了!依了我的村见识,何消得这样奉承。
上面那段话有一点遗漏,他没有提及东林党和正直朝臣的抗争以及他们的悲惨结局。他们此起彼应,前仆后继,但毕竟是少数人,因此作者不加考虑。作者设想的是整个朝廷群起而抗争,不成功就来一个总辞职。
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魏忠贤当然非倒不可。然而这样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抗争只能是空想,丝毫没有实行的可能。想法很幼稚,同时也很深刻。当时没有第二个人想到这一点,这是作者的独创,可见他对社会问题的探索并不都是人云亦云,不曾认真下工夫。
在作者那个时代,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是土地问题。国家安危,天下治乱,包括魏忠贤和东林党的斗争在内,它是这一切矛盾的根源和归宿。当张献忠、李自成以及各地闻风而起的农民起义军横扫大河南北时,一切土地占有者以及和他们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文人学士,没有一个人能心安理得地把这一个实际问题置之度外。《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也不例外,例外的是他把自己深思熟虑之所得形象化地转变为小说的故事情节,保留在《醒世姻缘传》中。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也是它作为社会问题小说的立足点。只见悍妇而不见她所立足的土地,这是对书名望文生义而造成的绝大误会。
下面是小说第二十二回《晁宜人分田睦族,徐大尹悬匾旌贤》的故事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