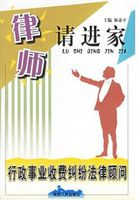今天一早,营地里穿过了一只漂亮的黑尾鹿。这是一只雄鹿,头上有着宽宽鹿角,展现出了叫人钦佩的优雅和活力。野外的动物兴许是在大自然的眷顾之下所以才具备这么惊人的美貌、力量和优雅的举动。可是动物驯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些野生动物很可能会由于被忽略而退化。不过有了大自然,这些动物会在它的哺育下慢慢地越来越完美。和其他的野生动物一样,鹿也纯净得同植物一样。在警觉或是休眠时的所有动作,相比弹跳时蓬勃的力量更让人无比惊讶。一举一动都完全是仪态万方,都是诗歌本身。通常我们在谈及大自然母亲并不是现实当中真正哺育万物的母亲,但是也会提到它该怀着怎样的睿智、严厉和温柔的关爱去关心和照料野地里的这群孩子啊。越是接近这动物,就越是会拜倒在这登山能手之下。它们走进荒芜之地的中心,非常顺利地依赖提取自己的能量,它们穿过的有布满倒下的树木和巨石而寸步难行的浓密灌木丛和树林,还穿过峡谷、溪流和雪地,一直都带着明丽和勇敢。它们在这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生存。在佛罗里达大草原和山冈之上,还有加拿大的森林里,甚至是遥远的北方,那些长满了青苔的苔原之上,它们游过了湖泊、河流还有海湾,在拍打着波涛的岛屿之间,它们还曾经爬过堆满乱石的山峦,不论是什么地方都表示出健康和干练,增添了山水的美感。唯有让人真真正正钦佩的生灵才称得上是大自然最显赫的荣耀。
营地东面几百码的花岗岩山脊,有一棵银杉树伫立在那儿,我始终在给它画素描,因为它好像在对我讲述着一场非常独特的雪暴。这是100英尺左右高的银杉树,长在了赤裸的岩石上面,由于风化的作用,它的根插在了尚不足一寸的裂缝当中,那地方还因为膨胀承载了这棵树的重量。就在它还是一棵小树的时候,北方的风暴来了几乎要把它吹倒。我们似乎可以从那已经枯死了的、向外倾斜的老树干上看出曾经发生过的那场可怕的事情。不过折断的地方它又重新找出了新枝,有了现在活着的树干。现在这新生树干的年轮早已超过了原来死去的小树,无疑也暴露了暴风雪曾来过的时间。这棵树还可以长出无数的水平枝丫,当中的一枝居然还可以向上弯曲又笔直生长,这就是长出来的新树替代了原来的主轴。实在是太神奇了!
这场暴风雪不仅在这棵树上可以看到痕迹,其他的譬如松树和杉树也是它的见证。有几棵树高大概在50~70英尺的树也折倒在了地上,而且被掩埋了。整个小树林被清理得再也没有一根树枝或是一根针叶,一直到了春天来临时这才出现。那些具有弹性还没有完全死去的幼苗借助着风的力量,再一次顽强地生长着,有一部分还长得很是笔直。折断了主干的树木也在尽可能地从断裂处的下方生出旁枝,从而让自己有发育新的主干的可能。这仿佛是一个断了背的人,他只好弯着腰,但是居然在骨头断裂的地方又有新的脊梁骨在生长,发育出了新的胳膊、肩膀和头,而原有折断的部分则慢慢死去。
到了中午,云顶和云山还是照例出现,云的山脊和山脉还是在变幻着自己的风貌,就像大自然从未停止过爱这份工作那样,所以每一天都在重复着相同的工作,不厌其烦地创造出美丽,从来不说辛苦。就在闪过几道锯齿一般的闪电和5分钟持续的阵雨后,云层和雨块开始消退,天空也慢慢地晴朗起来了。
7月23日
正午时分,再度出现了云乡美景,无论看多少次都看不厌的力量和美展现着,我感到了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无奈的感觉。很多人都在赞扬云彩的美,可是他们究竟说出什么呢?就在绞尽脑汁去思考如何描述那耀眼的云丘、云脊,还有那阴沉着的云的海湾和峡谷,如羽毛一样的沟壑的时候,云彩就转瞬即逝,丝毫没有任何一丝一片在空中留下痕迹。不过,同那些经历了千百万年仍旧不灭的花岗岩岩石一样,这些瞬间消失的空中云峦也一样的坚实且无可忽视。它们有兴亡之变,上帝的历法当中存亡的时间无所谓长短。在惊异、崇拜和赞扬当中,我们只能幻想,此时我们的快乐,和那些有着远大眼界且具备相同感受的朋友所说出的内容相比要更强烈。而且我们还因此了解没有一颗晶体或是水蒸气的微粒真实地消失了,这和软硬没有关系,它们只是通过蒸腾和暂时的消失升华了自己高洁的美感。而我们的工作、责任和影响启示不过是在尘世间用忙碌掀起的尘嚣,可是就算是我们也和地衣一样保持沉默的话,天空的云彩还会有相应的效应。
7月24日
中午的天空有一半是云彩,下了半个多小时的大雨,清洗出了这世间最干净的一块大地,这是一场多么酣畅淋漓的清洗啊!所有的路面、山脊、圆顶丘还有峡谷,结冰让它们闪闪发光,那远远的山巅好比是用雪筑起了藩篱,也好似带着泡沫的波浪,和大海的洁净几乎没有差异。天空当中最后几片像薄膜一样的云也消失了,树木就此清新而宁静。过了几分钟,树都在兴奋地向咆哮的暴雨弯腰表示敬意,它们有着对上帝膜拜一样的热情,充分地挥动、旋转自己的枝丫。只是在耳朵听来,树已经是安静了,可它们的歌唱还没有停止。肉眼无法看到的细胞都同乐曲和生命一样在悸动,纤维也如竖琴的琴弦在震颤着,那富含香脂的花冠和叶子不断地涌出浓浓的香气。也难怪上帝的第一圣殿在这片山丘和树林上了。砍倒树木建的教堂越多,就离上帝越远,看到的上帝身影就越模糊。即便是石头造的教堂也是如此。
就在营地树林的东边,就有一座大自然的教堂伫立着,生机勃勃的岩石经过砍劈之后形成了传统构架的它,大概有2000英尺高。它被锥形尖顶和石塔高贵地装饰着,阳光如潮水一般激动颤抖地照射着,和所有树林形成的殿堂一同生机盎然,给它最合适的名字就应该是“大教堂峰”(Cathedral Peak)。即便是一直对岩石都置若罔闻的比利,这个时候也常常忍不住会多看它几眼。在烈火中拒绝融化的冰雪也很难比在面对如此拥有上帝光辉之美全然没有反应更叫人惊奇。我希望比利也能到优胜美地的山谷边上去观赏一下,我愿意为他放一天的羊,他可以腾出时间来和其他地方的游客一样去欣赏美景。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愿意去,就算是仅仅只有不到1英里的距离他也始终没有出发。他说:“优胜美地有什么,不过就是一个峡谷,很多很多的石头,还有一个地上的大洞,掉进去多危险你知道吗?还是要离它远一点。”我坚持像个传教的传教士一样劝他还是可以去看看:“比利,你知道那些瀑布,想象一下,那天我们穿过的大溪,大概从空中直下半英里左右。那场景,那声音,你应该能看到、听到吧,就好像是大海在咆哮一般。”比利似乎对此还是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说:“那么高的地方,我站上去会害怕的,我会头晕。那不过就是石头,我觉得没什么好看的,这儿不也有很多?花钱去看石头和瀑布的游客真是傻子,没什么稀奇的。我在这地方待的时间够长,你是骗不了我的,我也不会去的。”在我看来,比利的灵魂已经睡着了,或者说卑微的快乐和烦恼已经蒙蔽了它。
7月25日
天空又有了云景,不少地方的云好像都成熟过头了,已经变得脏兮兮的,还开始腐烂了,在风的拉扯作用下成了小碎片,天空因此变得非常邋遢。内华达的夏天,正午不会有这样的云彩,因为光滑的轮廓和曲线让它们在视觉上好比是冰川打磨过的圆顶丘那样,十分秀美。从11点开始它开始形成,站在高山营地上,仿佛触手可及,清晰到让人忍不住要站到更高的地方去看它,去追寻那像瀑布一样从幽暗泉水喷流而下的溪流。它们一般会带来暴雨,和顺着岩石而下的瀑布那样威严。我此前的旅行中,我还没见过比变幻着的它们更新奇的呢!那么美好的颜色,清晰可见的瑰丽生成过程,变幻着的景致和整体效果,我实在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来形容,或许只有雪莱的那一句诗:“我把白雪筛落到下面的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