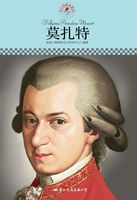汪恩甲的一去不归,不仅加剧了萧红的绝望,亦让东兴顺旅馆的老板失去了耐心。他对萧红说:“一定得有个办法 ,太不成事了,7个月了,共欠了400块钱。汪先生是不能回来的。男人不在,当然要向女人算账……现在一定不能再没有办法了。”
萧红拿不出钱,被从客房赶了出来,搬到旅馆二楼一间发霉的储藏室里。店主担心萧红负债潜逃,于是派人将其严加看管,并威胁萧红,如果再过一段时间汪恩甲还不回来,就要把她卖到道外的“圈儿楼”(妓院)抵债。
囚禁与虐待再度降临在萧红的生命中,她写信向好友李洁吾求助,但没有得到回应。
萧红知道,这一次,她不能再依靠任何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店主的催逼也越来越紧,她不能再无谓地等待下去,得想办法救自己和孩子。
此时,萧红能获取到的唯一外界信息,来自哈尔滨的《国际协报》。这份报纸萧红从上初中时起就喜爱阅读,尤其是该报的文艺副刊,曾让萧红受益匪浅。
1932年7月9日,萧红向《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寄去了一封求助信,信中以激烈的笔调详陈旅馆老板的恶行,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呼吁社会的同情和救援。
这封信立即引起了副刊主编裴馨园的重视,他带着几位记者和编辑一同去东兴顺旅馆探望萧红。他们向旅馆老板出示了记者证,警告老板不得虐待孕妇,并要求他正常供给萧红的伙食,一切费用均由报馆负责。
第二天,萧红打电话到报馆,想要几本书看。
裴馨园不在,电话是当时正在帮他处理稿件的一位年轻作者接的。当天下午,在裴馨园的委托下,这位笔名“三郎”的作者带着报馆为萧红准备的两本书和一封安抚信,来到了东兴顺旅馆,敲开了那间阴暗的储藏室的门。
1932年7月12日,这一天,三郎的到来改变了萧红的命运。
窄小的房间里,只有床、简单的被褥、破旧的书报和一个柳条包。三郎眼前的这位年轻女人,衣衫破旧,睁着两只大眼睛,脸色苍白,头发散乱地披在肩头。
三郎把书和信交给她,本想完成任务后马上就离开,可是她的身子紧偎在门旁,挡住了他的去路。她实在太孤寂、太无助,仿佛害怕他离开她似的。
萧红双手颤抖地捏着信,双眼定定地读了几遍。得知来人是作家三郎,她的脸上现出了惊喜。“你就是三郎先生,我刚刚读过你的文章,可惜还没有读完。”说着,她拿起床上的一张旧报纸指给他看,三郎看见,那是自己正在连载的小说《孤雏》。
“这里边有几句对我脾胃的话,我们谈一谈……好吗?”
这句请求将三郎留住了,也将两人的缘分留住了。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他们第一次相见的这个下午,正印证了那份古老的情愫。
三郎看到了萧红的字,那是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写的几个“双钩”大字。三郎看到了萧红的画,那是用铅笔头画成的清丽的素描画。三郎读到了萧红的诗,他几乎要激动地惊呼:“谁说哈尔滨没有女诗人!”
令三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首叫作《春曲》的小诗: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在两人的畅谈中,一下午的时光很快溜走了。三郎眼中的萧红,已不再是那个狼狈不堪的落难女子,而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有才华的女人。他在心里发下誓愿,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这个美丽的灵魂。
萧红的春天真的来了,这位三郎正是日后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萧军。
萧军原名刘鸿霖,又名刘蔚天,1907年7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曾在东北讲武学堂学过军事,因打抱不平触犯教官而被开除,后在东北军中任下级军官。“九一八”事变后,气愤于东北军不抵抗而离开部队,与好友一起赴吉林舒兰,冀图策划当地驻军抗日,事败,携家眷潜入哈尔滨。哈尔滨沦陷后,因无经济来源而陷于困境,不得已将妻子许氏和两个女儿遣回老家,自己则准备伺机参加抗日游击队。其间,以“三郎”的笔名卖文糊口,因向《国际协报》副刊投稿,受到裴馨园的赏识,被请去协助处理稿件和一些其他的编辑事务。
与萧红相识时,萧军的处境其实并不比她好多少,他没有自己的住处,借住在裴馨园家中,稿酬和编务费是他仅有的收入,只能勉强靠此果腹。萧红亦对他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绝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一定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竟也这般落拓!”
天色向晚,萧军与萧红从文学聊到人生,又从人生聊到爱情,他几次起身欲走,又几次重新坐下。
几十年后,年过古稀的萧军在回忆起这个下午时,笔端依旧满怀着深情: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她初步给予我的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泯灭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临走前,萧军问萧红每天吃什么。萧红将桌上两只合扣着的粗瓷碗揭开,里面只有半碗粗硬的高粱米饭。萧军心头一阵酸楚,他搜了搜口袋,掏出5角钱放在桌上,对她说:“留着买点什么吃罢!”
他没有告诉萧红,这是他身上仅有的5角钱,给了她,他就没有搭车回去的钱了。
他穿着一双破皮鞋,在夜色里踏上了漫漫归途。
而她,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陷入了百感交集的漫漫长夜。
这爱来得像一场及时雨,却又像一场不真切的梦,让她醉,让她恍惚,亦让她忧虑惶惑。
她提起笔,续写起她的《春曲》:
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
因为诗人的心,
是那么美丽,
水一般的,
花一般的,
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
但又怕别人摧残。
那么我何妨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