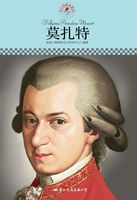1940年1月14日,端木和萧红来到城里,托在银行工作的朋友帮忙购买去香港的机票。通常,赴港的机票都非常紧张,往往要等一个月左右。意外的是,这一次,朋友竟然帮他们买到了1月17日的两张机票,是给中国银行预留的机动舱位。
近在眼前的行期打乱了夫妇二人的一切计划,他们匆匆收拾了需要随身带走的东西,来不及去向朋友辞行,甚至来不及写信一一告知朋友他们的去向,连退房、辞退保姆等杂事都是端木之后打电话托二哥的同学帮忙料理的。
然而,尽管事后端木一再解释,他与萧红的不辞而别实在是由于行程太过匆忙,但他们的这一举动却依然遭到了纷纷非议,这些怀疑和误解,甚至是来自萧红昔日里最好的朋友。
胡风写道:
她忽然没有告诉任何人,随T乘飞机去香港了。她为什么要离开当时抗日的大后方?她为什么要离开这儿许多熟悉的朋友和人民群众,而要到一个她不熟悉的、陌生的、言语不通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我想也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目的和打算吧?
靳以甚至是大骂:
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
不解之余,他也为萧红感到担心: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
而绿川英子和梅志则都认定这是萧红屈从了端木的主意。
对于萧红和端木“谜样的香港飞行”,绿川叹惜道:“喜欢和朋友一道的她,不能不和朋友分离了。”言下之意萧红是被迫与内地的朋友分离的。
梅志亦分析道:
是呀,所有的朋友听到这消息无不表示惊奇,怎么会想到离开抗战的祖国到香港去?后来我才约摸的懂得了她当时的心情,她是以屈就别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去香港的。这里表现她为别人牺牲的伟大,也表现了她跳不出她已感到桎梏的小圈子的软弱。她只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拉住她,不让她去。但她终于远离了抗战的祖国和人民,到那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亚热带的香港去了!
萧红去世不久,张梅林在回忆她的文章中,就赴港一事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她的飞港颇引起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她来信说明飞港原因,不外想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抗战以后她只是写了点散文之类的。其次,也是为了避开讨厌的警报吧。
联系萧红对待创作的一贯态度,梅林的解释无疑道出了她的真实愿望。早在1937年冬天,在武汉时,萧红就有了写作《呼兰河传》的念头,无奈战火连年,她不得不辗转多地避难,又遭遇了感情的剧变,始终没有一个长久的稳定环境或心境让她从事长篇创作。而身体的每况愈下,也让她想尽早留下一部长篇的心情变得更加迫切。
可悲的是,这样一颗朴实的、纯粹的创作者的心,却得不到挚友的理解。在萧红悲剧的一生里,这无疑又是一重深重的悲剧。
1940年六、七月间,萧红得知胡风曾致信许广平,信中称她“秘密飞港,行止诡秘”。萧红和胡风一向交谊深厚,本以为胡风能同情她的处境,谁知,他非但不同情,甚至还语含讽刺。一向看重友情的萧红,被这件事深深地刺伤了。在7月28日致华岗的信中,她忧愤地写道:关于胡之乱语,他自己不去撤消,似乎别人去谏一点意,他也要不以为然的,那就是他不是胡涂人,不是胡涂人说出来的话,还会不正确的吗?他自己一定是以为很正确。假若有人去解释,我怕连那去解释的人也要受到他心灵上的反感。那还是随他去吧!
想当年胡兄也受到过人家的侮陷,那时是还活着的周先生把那侮陷者给击退了。现在事情也不过三五年,他就出来用同样的手法对待他的同伙了。呜呼哀哉!
世界是可怕的,但是以前还没有自身经历过,也不过从周先生的文章上看过,现在却不了,是实实在在来到自己的身上了。当我晓得了这事时,我坐立不安的度过了两个钟头,那心情是很痛苦的。过后一想,才觉得可笑,未免太小孩子气了。开初而是因为我不能相信,纳闷,奇怪,想不明白。这样说似乎是后来想明白了的样子,可也并没有想明白,因为我也不想这些了。若是越想越不可解,岂不想出毛病来了吗?您想要替我解释,我是衷心的感激,但请不要了。
华岗是萧红在港期间书信往来最频繁的朋友。1938年秋天,萧红在武汉等待入川的船票期间,参加了一些文艺界进步人士的聚会,因而与他相识。同年10月,也即是萧红抵达重庆不久,《新华日报》迁至重庆继续出刊,当时身为总编辑的华岗亦随同来渝,萧红与他亦时有来往。1939年春天华岗离开了《新华日报》,经组织安排,在大田湾乡下养病。离开重庆前,萧红和端木为了征询华岗的意见,专程从北碚前往大田湾探望。
到香港后,萧红常常把自己的心事与华岗商量,或许不仅因为华岗是她颇为敬重、信赖的朋友,也因为华岗是当时少有的获知她来港的决定,并且支持她的朋友。
来香港半年,由于湿热的气候使萧红的肺病有了加重的症状,也由于没有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她萌生了返回内地的想法,只是因为想写的作品还没有写完,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如此,有一段时间,她都在去与留之间彷徨摇摆,举棋不定。
6月24日,因为对自己身体状态的担忧,她给华岗寄出了第一封信,信中说: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
或许华岗的回信促使她正式考虑了回内地问题,她在7月7日的信中便向华岗报告她的“打算”:近几天正打算走路,昆明不好走,广州湾不好走,大概要去沪转宁波回内地。不知沪上风云如何,正在考虑。离港时必专函奉告,勿念。
然而,萧红想要完成创作的心,终究还是战胜了想要离开香港的心。7月28日,她写道:香港似又可住一时了,您的关切,我们都一一考虑了。远在万里之外,故人仍为故人计,是铭心感切的。
她终于使自己留在了这里,并渐渐发现了香港的美——
1941年1月29日:
香港天气正好,出外野游的人渐渐的多了。不知重庆大雾还依旧否?
2月14日:
香江并不似重庆那么大的雾,所以气候很好,又加住此渐久,一切熟习,若兄亦能来此,旅行,畅谈,甚有趣也。
对于萧红和端木在是否离港一事上的徘徊犹豫,张梅林在文中亦曾提及,他认为,他们的离港之念,更主要的是基于人们对香港未来局势的预测:在1940年下半年,正是国际问题专家们拼命讨论“日本南进乎,北进乎”的时候,因之香港的空气是疟疾式的。每次空气紧张,萧红即来信说正在购飞机票回重庆,希望能给先找便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延宕下来,以长篇《马伯乐》未完成和有病为理由。
端木和萧红初到香港时,暂住九龙尖沙咀金巴利道诺士佛台3号孙寒冰处。刚刚安顿下来,一位身材高大的客人突然造访,见面后自报家门:“我是戴望舒。”端木和萧红在重庆时就与戴望舒有书信往来,文事合作,见到神交已久的朋友自是十分欢喜。三人一起出去吃了饭,第二天一早,戴望舒又专程来接端木和萧红到他所住的“林泉居”做客,并诚邀他们搬过来一起住。“林泉居”是一幢背山面海的三层小楼,四周林木环绕,旁有小溪,四邻多是作家、教授,环境幽雅,适合静养和写作。然而当时端木腿关节风湿病发作,不能上下山坡,只好辞谢了戴望舒热情的邀请。
不久,为了方便编辑《大时代文艺丛书》,端木和萧红搬到了乐道8号二楼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小房,与大时代书店为邻。
除了出席一些香港的文化活动外,萧红的大部分时间主要是在写作中度过的。1940年4月,她完成了短篇小说《后花园》,这篇小说与《呼兰河传》有着明显的关联性。“后花园”是《呼兰河传》中最为重要的场景,小说里的冯二成子亦是《呼兰河传》中冯歪嘴子的前身。外在的安宁和内心的寂寞,使得萧红的神思飞回了遥远的故乡,呼兰河畔的往事在记忆中不断发酵、涌现,化作了笔底浓郁的乡情。《后花园》正是这样一首温情而凄美的思乡曲。
1940年5月27日,几十架日机猛烈地轰炸北碚复旦大学所在地,教务长孙寒冰等百余人遇难,《文摘》主编贾开基身负重伤。消息传来,香港文化界人士纷纷感到强烈的愤怒与悲痛。端木想到孙寒冰生前对自己和萧红的帮助,沉痛地写下《悼寒冰》一文,遥寄对亡友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