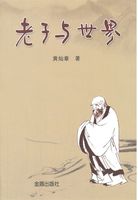虽然我把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写作,但我发现自己很少能在梦中作任何创作。某次当我在睡觉的时候,写下了一首奇特的伊丽莎白抒情诗,诗的题目是“凤凰”,或许你能够在《牛津诗选》里看到这首诗。在这前后的时间里,我都没有写过类似的作品。这个梦发生在1891年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那时候我正在与一位朋友住在威斯特摩兰郡的一家旅馆里。梦醒之后,我立即写下了这首诗。之后,因为感觉这首诗并不完整,因此我又对这首诗做了一些补充。随后,我把这首诗编入了我的一本诗集中一起出版,并向一个朋友指明了证据。但朋友看过之后,却指着新增的那一节诗对我说:“我想,你一定遗漏了什么,你所增加的这节诗和整首诗完全不搭!”
但这是一次特别的经历,此外我还梦到一场施坚信礼的宗教仪式。在之后我记起来在仪式上吟诵的一首非常特别的赞美诗,因为这首诗太过特别以至我没办法将这首诗写出来。整首诗本来就是献给主持仪式的主教的。但是,梦中的我也似乎被这首诗所感动,似乎这首诗本身也是唱给我听的。
偶尔在我睡觉的时候,会被梦中某种巨大的声响惊醒,可这种近乎真实的梦境却十分难以理解。有人说过睡觉做梦会让人筋疲力尽,但这在我的经历中却总是得不到佐证,可说我在做梦之后却产生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于我而言,睡觉深沉往往就是身体状态不佳的一种表现,假如我做了很多有趣的梦,通常会感到自己身心得到了放松,神清气爽。这样的梦让我整个人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又或者我梦到在做客期间受到了良好的款待也会产生这种感受。
这些不过是个人散乱的一些经历而已,站在哲学的角度去看,我无法提出任何关于梦的理论。根据我的情况,这是一种源自于遗传的能量。我父亲是我所见过的最主动且固执于做梦的人,他总会做很多高质量的梦。他的梦往往会让人大吃一惊,生动有趣,我并没有遇到第二个梦能与父亲的梦相比。我父亲做了很多富于创造力的非凡的梦,其中我从未听过的最有趣的梦是他在梦中找到了提图斯·欧莎的马的墓地,在谈话开始之前他并没有意识到那块石板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个梦,我已经写在父亲的传记当中了。
在父亲的梦里,他正与斯坦利院长站在西敏寺里,他看到了一块有裂痕的刻着一些字母的石板。斯坦利对他说:“我们找到了。”我父亲应声道:“是的,但对于这个你知道些什么的吗?”斯坦利答:“什么?我认为之所以立碑纪念一匹马的无辜,正是想向后人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无论主人如何劣迹斑斑并不会影响到他的坐骑。”我父亲应和道:“当然!”但即使到这个时候,他依旧无法意识到墓碑上的墓志铭所指向的是谁。我父亲看到石板上写着TIT CAPITANI这样的一些字母,因此知道这块墓碑属于一匹名为提图斯·欧莎的马,其完整的名字应该是EQUUS TITI CAPITANI。最终还是“上尉”这个军衔让我父亲回想起,提图斯·欧莎曾经还做过民兵团的上尉。
而我唯一能算得上非凡且表现了我特异的预知能力或洞察力的梦,发生在1914年12月,在梦中所发生的事却不能单纯地归于一个巧合。
在1914年12月8日那个夜里,我梦里正走在一条乡间小路上,在路旁种树篱。在其左侧我看到了一座花园,有一幢房子竖立其中。梦中的我正想要去看望我的一个老朋友阿迪·布朗小姐,当时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但梦里我依旧认为她还活着。
在我前方有四个与我方向一致的人正在路上走着,我就加快脚步赶上他们。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年纪稍长的人,另一个人则显得年轻一些,有着一头红发,步履轻盈,穿着一条灯笼裤。另外两个男孩,看起来似乎是那个红发男人的儿子。我认出其中那个年龄稍长的人好像是我的一个朋友,只不过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他面带微笑地朝着我点了点头,我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我刚加入的时候,那个红发男人说:“我想要去看望一个老人,正是我的表姐,她就住在这里!”不过,他是对他身旁的人说,并非针对我,但我却意识到他的表姐正是阿迪·布朗小姐。年龄稍长的人对我说:“我为你做一下介绍。”只见他把年轻的男人向我引见,道:“这位是拉德斯托克勋爵。”随即,我们握了手,我说道:“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拉德斯托克勋爵是一位颇有年纪的人,这次见面让我非常惊讶。”
我并不能回想起很多关于这个梦的细节,可是梦里的场景却一直非常鲜明生动,因此当我再次回忆起来的时候,总是能在脑海中浮现出梦里的场景。当几分钟后的12月9日,我从我床前被送来的一份《泰晤士报》上,我看到了关于拉德斯托克突然死亡的消息。一直以来我并不知道他有患病,并且很久没有再想起这个人,可奇怪的是他竟然是阿迪·布朗的表弟。很久以前,阿迪·布朗曾经给我聊过一些关于她表弟的趣闻,在她去世之后我就不再听到任何人提起过拉德斯托克这个名字,并且我们也并没有见过面。因此,事实上在我做这个梦的时候,老拉德斯托克已经过世,他的儿子——54岁的小拉德斯托克则继承了爵位。或者我应该说,在我梦中出现的那个年龄不过45岁的男人,我并没有太深的印象,唯一记得的就是他仿佛长了一头红色的头发。
我不曾订阅过报纸,但我也并不认为在报纸上曾经出现过关于拉德斯托克前一天患病住院的消息。事实上,他的死亡来得相当突然,出乎意料。假如说这并非巧合,那么合理的解释或许正是我在大脑中存在某种特殊的心灵感应,我与亲爱的老朋友阿迪·布朗小姐心灵相通。因为,在梦中我确实想起来她,或许我还需要假设她的心灵同样地感受到了表弟拉德斯托克勋爵的死亡。这虽然并非唯一的解释,但从我角度看来,这可以算得上一个重大的神秘事件。
尽管并不尽如人意,但我依旧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理性和道德在梦境中总是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且完全由一个人的本性中的原始因素在发挥作用。似乎在梦境中创造力非常强大,充满了活力,可以将记忆中各种要素融合组装夸张进行创造,然而,创造力所涉及的主要是非常原始的情感、形状、颜色,或者令人记忆深刻的名人、重要人物或者激动人心的不寻常事件,或者一波三折的冒险事件等。例如我在一个赶火车的梦里并不清楚自己要去哪里,这次旅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又例如我在梦到盛大仪式的时候,很少关注那场仪式所举办的目的是什么。
对于我们完全有意识地回避大脑创造部分,特别是在观察部分特别急切、警觉地试图去看到正在发生的事件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另外,我也并不明白,为什么在梦中清晰的场景会在醒来之后消失无踪,我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假如你能在醒来之后根据记忆重新演练一遍梦中所见的场景,就会发现梦境早已不再是当时的情景。假如你不抓紧回顾梦中的情景,就会立马让这个记忆黯淡下去,并且哪怕你对于梦中丰富的冒险经历还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但在一两个小时后,你就不可能再回想起自己梦中的经历。梦醒后,我完全不能回顾、想想自己在梦中所看到的神奇场景。虽然我可以回想起实际的风景,但在我的幻想当中所看到的风景鲜明的色彩和神奇的形态却再也不能再我大脑中重新构筑出来。
最奇怪的一点事,梦里的创造力似乎有一定的范围和强度,当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这种范围和强度也随之消失无踪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做过的梦本身就不存在任何真实或者重大的意义,更不会从梦中得到任何警告或者预感,更遑论与生活中问题相关的梦,即使最低程度上的相关性也没有做过。
在但丁《炼狱篇》里,有一段描写黎明的美妙诗句,是这样写的:那个时候,
黎明将至,燕子向我们展现了它悲伤的歌喉,偶然间古老记忆中的悲伤,重构;
而我们的头脑,更多的来自肉体的漫游,
却很少受到思想的限制,换句话说,
他们在梦中得到了神圣的预言。
在我看来,我们可以象征性地对一个梦进行解释。可以我的经历为例,我所做过的梦似乎完全属于除我本身以外的另一个我。梦中的我是一个快乐、无忧、天真的人,生机勃勃,好奇心很重,同时富于活力,无所顾忌。不论是对未来的展望,还是对于过去的回顾都是如此的令人心满意足,没必要负任何责任或者具备怎样的责任,仅仅享受着运动的快乐是完全无害且友好的。总的说来,梦中的我是一个享乐主义的人。但这丝毫并不能体现梦醒之后的我,这种状态和感觉有时候甚至会让我的内心陷于不安状态,似乎梦中的我更像是真实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