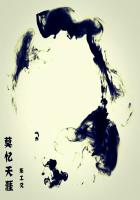师傅说平生最喜欢两种人,拿剑的和不拿剑。
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从出生到现在我并未见过剑,我只见过师傅。
师傅还说,这个世界很危险,但年轻人还是得出去闯一闯。
我仍然觉得奇怪,但奇怪归奇怪,师傅的话还是要听的,因为我知道师傅不会骗我。
这一年,我的父亲蛮刚刚统一了天南的所有部落,声望达到了空前。不可否认,父亲是个强大的男人,据部落巫医青说,父亲年轻的时候是有名字的,但后来改了名字,只叫蛮。而我们山字部便成了蛮部。
说实话我讨厌巫医青身上布满刺青花纹的脸,尽管他对着我说话的时候是和颜悦色的。这个东西真的没办法改变,喜欢一个人不需要理由,讨厌一个人不需要借口。
印象中,十岁那年,我的成人礼,巫医青熬了一大锅十分难闻叫做巫泉的东西,在我身上鬼画符似的画了整整二十条线。画前十条的时候还好,身体就像泡在温水里一样舒服,但画到第十五条的时候,我的身体开始发烫,甚至我可以感觉得到我的头上已经是热气蒸腾了。
尽管十分难受,但师傅在八岁的时候就对我说,忍。
坚持到二十条的时候,终于力竭而昏。
后来,我才知道,族中和我同样年龄的人,都坚持到三十条甚至靠上。
父亲对此表示沉默,尽管他身边的四大神将,风、雨、雷、电四大神将,一再表示,即便经脉不通也可将我调教成部落中最厉害的战士,但父亲依然固执让师傅教导我。
但师傅从来不和我讲修行的事情,只是教导我礼仪方面的事情。为此,我也问过父亲,但父亲的回答却是坚决而又有力的,“你不学,老子废了你。”
因此,从十岁那年开始,我便跟着师傅读书。这在部落其他人的眼中确实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了些,因为同样在他们十岁那年,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在野外才能生存,如何才能在火狐发怒的情况下顺利逮到它。
十三岁的时候,师傅为我缝了件衣服,月白色长衫。我也束了长发,挽了发髻。为此我也伤心过,族中我暗恋的蛮夜,自打看见我这幅打扮后,便再也没有和我说过话。但父亲显得格外高兴,看着我就像看着瓷娃娃一般,手欲抬又放。最后说了两个字:“好,好。”
十五岁的时候,师傅对我说,年轻人就应该出去闯一闯。
我知道师傅的话必有深意,就像我印象中的师傅总是站在窗前,一袭白衣望着天南山。
我曾问过师傅,“师傅,山的那边有什么?”
师傅眉头微蹙,答道:“山的那边有人。”
我又问道,“除了人,还有什么?”
师傅又道,“有血,有水,还有你三个师兄”
我又说,“只有师兄?”
师傅道,“对了,差点忘了,有一个人,你也可以叫她师姐,但我保证不了,她喜不喜欢师姐这个称呼。”
师傅说这句话的时候,总算低着头对着我一展笑颜。
这些年来,师傅从未教过我修行,但我却知道,山分南北,水分阴阳。北林,南山,东海,西泽。当然了,这是从一本名叫《山海经》的书上看来的。
而这修行的境界又可以分为,潜龙、卧渊、通幽、知泉。每层又可分上中下三境界,而在这四大境界之上,从未见过第五境界的出现,因此,即便如师傅渊博,师傅也不知道在这四大境界之上,可有其他。
我曾问师傅,“师傅见过在这之上的修行者吗?”
师傅道,“未曾见过,只知那是诱惑。”
原本以为,我会安稳地过完我在这世间的第十五个年头。
但师傅递给了我一个纸鹤,说,“拿着。”
是夜,群星闪耀,迸发前所未有的光芒,父亲站在祭台上,犹若神祗。第一次我才觉察到父亲的强大。
祭坛上闪耀着非同寻常的光芒,是红光,我非常确信师傅说的诱惑便是指此。
祭坛周围密密麻麻跪着我的族人,露着身上或多或少的线条,看起来凌乱不堪,但又隐隐是一个整体。说不出的怪异。
只有师傅一人和父亲对视。
师傅道,“真的要这样做吗?”
父亲说,“对。”
师傅又道,“你不怕遭天谴?”
父亲道,“那不是还有你吗?”
说这话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师傅的身体微微一颤。
师傅道,“你知我的剑,剑下从无活口。”
父亲道,“你没试过,怎么知道你的剑下会没有活口?”
师傅说接道,“那好,我试一试。”
父亲开始凝神,有风自无名处生出。紧接着,风便灌满了整座祭坛,却没有一丝风落在族人的身上。
红光和线条占据了我的视线,当然,还有师傅白衣胜雪站在父亲的身旁。
群星已被父亲的身上的红光压得低了一头,风接着便吹了起来。族人们一动未动,而我却被吹出好远。喉咙已隐隐泛出血腥味儿。
紧接着,发生了我很多不理解的事情,族人们蜂拥而起杀向父亲。父亲依旧强大无敌,巫医青死在他的拳下,四大神将死在他的拳下,巫夜死在他的拳下,然而这不是结束,仅仅是开始。
我想逃离,但怎么也动不了,那是我的族人,是我至亲的人,那些死去的人中有我喜欢的,也有我讨厌的,但他们都是我的族人,终于,那看起来有些破烂的歪歪扭扭的线条在我身上闪烁了起来。
祭坛上的红光越来越盛,群星也越来越暗淡,一团白色的影子自空中降落。
父亲出拳,便朝那团白光击去,紧接着父亲便吐了一口血,紧接着父亲吐了第二口血。
这时,祭坛上的红色光芒已似囚笼困住了父亲。
师傅出手,也是一道白光,自她身前起,至红光落。“噗”地一声,囚笼已开,而看似无敌的父亲,身上已是血迹斑斑。
父亲这时笑了,师傅也笑了。
父亲身上开始燃起红色的光芒,而师傅身上开始燃起白色的光芒,他们化成了一团影子,半红半百,但射向白色影子的气劲,却如虹一般。
师傅说的对,她执剑的样子很好看,尽管剑身已有些破了,但仍然好看。父亲则显得更加狼狈,身上的巫纹开始变得潦草了许多。
群星依旧暗淡,那影子已是不见。
师傅的声音从我衣襟处传出,我低头望着手里只剩下半只身子的纸鹤,十分诧异。
师傅说,“你终究是败了。”
父亲道,“败了吗?至少我看到了它的样子。”
师傅又道,“那还是败。你蛮族已破败。”
父亲接道,“败了吗?我感觉和它的赌局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