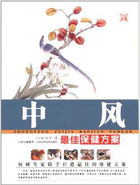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井下全是死尸和血肉模糊的伤者。我从血泊和死人堆里爬起来,企图逃出矿井,但吓得两腿发软,怎么也跑不动……惊叫一声醒来,方知自己做了一场噩梦。
我作为政府办公室秘书,随市政府调查组,来到财源煤矿调查矿难事故。也许是参与了这次矿难调查,也许是平时看多了矿难事故的媒体报道,才使我做了这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噩梦。
这是一个开了又关、关了又开的个体煤矿,安全条件极差且违反操作规程,最终导致了矿工死伤各一人的矿难。
调查展开后,调查组听汇报、看材料,当地县乡两级政府和矿主都很配合,主动汇报了相关情况,做出了深刻检查,并对遇难矿工家属以优厚的抚恤……三天过去,调查结束了,我这个当秘书的,根据调查组领导定的调,已经把调查报告的腹稿打好了———一死一伤不算重大事故,罚款、通报……
明天,我将随调查组游览当地名胜,之后就要打道回府交差了。
噩梦醒后很难再入睡,我干脆坐起来抽烟。随身带来的香烟已经抽完,好在矿主送有一条未开封的,便打开来。谁料那条香烟里竟然夹带着三万元钞票!矿主对我这个小秘书都如此大方,对调查组的其他大员会怎么样?这是为什么?
正在我胡乱猜想时,客房里的电话铃骤然响起。已是天寒地冻的冬夜零点,谁会在这时候往宾馆客房里打电话?
来电话的是我初中时的同学二柱子。我听声音不太像,对方说多年不见面,声音哪有不变的?我问:“十多年没有联系了,你怎么知道我现在的行踪?”
“同学串同学,哪个老同学的行踪我不清楚?———你大学毕业后当官了,可我,沦落成了财源煤矿挖煤的打工仔。”
上初中时,二柱子是年级的学习尖子,后因家境贫寒,交不起学费而辍学。二柱子在电话里说他前年结婚了,眼下一家人全靠他外出挖媒挣钱糊口:“你什么时候回老家了,顺便代我看看我老娘,她老人家卧床不起几年了,全靠我媳妇苦撑着照料;还要请你代我看看我儿子———那小家伙可招人喜欢了!”
旧情唠过,我问他这么晚打电话有什么事,二柱子这才说:“你们前来调查,就听听县乡政府和矿主汇报就算完了吗?”
“我们走访过劫后余生的矿工……”
他在电话里叹道:“矿工们一怕政府‘秋后算账’,二怕矿主豢养的黑社会打手报复,谁敢透露真情?”
“你什么意思?难道说我们调查的情况不实?”
“这次矿难何止一死一伤———多数遇难矿工被销尸灭迹了!还有,矿主为了掩盖真相、少付、不付抚恤金,还把一些重伤者活埋了!”
我心头一颤:“可是,当地县乡政府向我们汇报……”
“财源煤矿是当地的纳税大户,矿主又重金买通了各方头头脑脑,县乡政府能说实话?一切都掩盖就绪了才请你们来的———要不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他们连发生矿难的消息都不会往上报告。”
我虽然也在仕途上混,但天良没有丧尽;揭破真相、为遇难矿工申冤的欲望升上了心头:“你住在什么地方?我明天找你再作了解。”
二柱子说他现住黑石沟,住所前面有棵弯腰榆树;同室居住着五个打工仔,找到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证明真相:“多年不见,你可能不认识我了。不过我的鞋垫是我媳妇缝的,上面有棉线缝的‘2004.1.3’字样,那是我儿子的生日。”
我还要再往下问,但二柱子那边把电话扣了。我房间里的电话没有来电显示功能,想回电话过去也不知道他使用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我借故没有去游览名胜,独自找到黑石沟。这是条无人烟的荒沟,既没有工棚也没有房舍。但是,二柱子说的那棵弯腰榆树;榆树下面是一片新土;新土旁边有一只半旧的胶底鞋,鞋子里面有鞋垫,上面有棉线缝的“2004.1.3”字样……
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鸡皮疙瘩“呼啦”起了一身。
我结结巴巴地把情况向调查组作了汇报,招致一片讥笑。但后来调查组还是到黑石沟挖开了那片新土———下面埋着五具尸体,其中就有二柱子……
他的眼睛定定地瞪着,直视着他家乡的天空———二柱子在看什么?也许,他看到了正扶门框朝他这里张望的白发的老娘;也许,他看到了蹒跚学步、“招人喜欢”的儿子,正向他这里一步一晃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