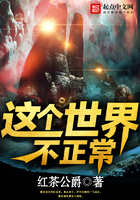很多年后,我重游晚歌城的时候,脑海里想到的只有一个画面。一个小孩站在城楼上不住奔跑,点燃一座又一座烽火。
抵达晚歌城的时候,我们见到了极为荒诞的一幕。
被苔藓染得发绿的城楼上空空荡荡,没有任何值守的士兵。细看的话,有个穿着邋遢蓬头垢面的人在来回走动。那个人似乎有些眼疾,直到我们走到护城河边的时候,才一个哆嗦跳起来大声叫嚷。他的嗓子好像被刀劈过,带着呼呼的风声。
我仔细听了下才挺清楚他叫的是“狼来了”。
只有个三个字,反反复复。
我有些摸不清楚情况,便下令军队停止前进,等待城里出人来交涉。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叫了很久都没人出来看一看。后来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很兴奋地多叫了两个字。
“真的狼来了。”
没想到这一声就奏效了,陆陆续续跑上来一堆士兵。他们骂骂咧咧,忙着披衣戴甲。看得我直皱眉头。过了约半刻钟,那个看起来像是领头的才说:“开始吧。”
我看他们已经准备完毕了,也说道:“开始吧。”
战争开始。
过了十多年,我终于习惯了进去外城那种简单粗暴的传送方式。整个人被巨大的外力像拔萝卜似的拔起,又倒栽葱似的被放到地上。有些新兵还摇晃了几下身形。看了几眼身后,我便把目光抛向正前方的城墙。我用右手拔出跨在腰间的刀,在千万人的注视下缓缓挥刀。
大地开始颤动。原本静立不动的人群刹那间如同离弦之箭,向着前方飞奔而去。对面刚才还乱糟糟的军队也重新找回了纪律,随着领军的号令展开了反击。
轰隆隆的马蹄声直欲刺破人的耳鼓。金属兵器碰撞,发出尖锐的鸣叫。被烟沙迷红了双眼的士兵齐齐张大了嘴,整齐的“杀”字排山倒海。但最刺耳的,其实还是兵刃破开铠甲划过人血肉的声音。轻微却致命的哀鸣。
随手格开向我当头劈来的两把剑,然后一脚踢出,面前两个眼神狂野的敌兵便横飞了出去。经历过太多场祭祀洗礼的我实在不是这些一看就许久未曾战斗过的可以匹敌的。这让我稍稍有些失望。涌起的战意消散大半。
司马说我这是妇人之仁。我不否认。面对这种输赢在开始前就毫无悬念的战争,我实在懒得挥动我的刀。司马常说,如果我在这种战争里能够多出一份力的话,那么会有相当一部分年轻的士兵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我还是不否认,却也不想因此改变。
这就是战争。总会有人死去。
很多年前,我也像司马那样耿直,是非黑白都是如此清晰简单。只是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不是你一个人的战争。这是所有人的战争。每个人都有挥刀的权利,也就必然有挨刀的觉悟。你可以阻止一些人挥动自己的刀,也可以阻止一些人挨刀,但这不公平。我当时问他:“为什么?”他笑着告诉我:“因为我实在挥不动那么多刀。我就看不惯你可以那么轻而易举地获取战功。你这样的人存在于战争之中,就已经是对别人的不公平了。”
对于这个答案,我当然觉得很白痴,没做任何理会。但是后来说这话的人死了。死因是,存在就很不公平的我被很多人围观,我挡住了数不清的攻势,但还是漏了一刀。厮杀一直都是不公平的。你打赢无数次,没用。你只要输了一次,就没有以后了。
于是危急之下,他替我挡了那一刀。我当时想推开他,但是被他推开了。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发现了我的一些异样之处。我好几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受过的致命伤对于别人来说命多硬都得死了。可我还是活着。我相信那一刀就算砍中了,也不过是换我在混着血液的沙土上多躺一会。明天我还是活蹦乱跳,好汉一条。可他还是推开了想推开他的我。
他说:“能不能让我也做次英雄?你都死过那么多次了,也该我死一回了。”然后他就死了。
之后我很认真的想了那个问题。他说的很对,这不公平。我走了太多别人的路,让太多的人无路可走。
抽了个空,我还看了眼晚歌城。我忽然发现,刚才的那个人还在城楼上。他并没有穿铠甲。我之前以为他是个平民。现在才发现,他居然是个军人。此时的城楼上只有他一个人。风扯的晚歌城的旗帜猎猎作响。
他弯腰低头,在垛口的位置弄些什么东西。不一会儿,他换了个垛口,继续弯腰低头摆弄着什么。过了一会儿,我看他待过的地方全都冒起了烟。有的地方的烟只冒了一点就没了,他又不厌其烦地回去重新摆弄。看到重新冒烟后,他会直起身端详一会儿,擦擦汗,再去往下一个垛口。城下数万人的厮杀似乎与他毫无关系。他就那样一个人来回奔走在城楼之上。
又有人向我冲了过来,我重新加入战斗。
看来晚歌城太久没经历战斗了。战争比我想的还要结束的早,伤亡比以往小很多。这场战斗里,我并没有看到晚歌城的城主露面。不过我也没什么疑惑,以前遇到指使将士拼命自己却躲起来的城主也不少。这样的人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倚着城,他是城主。没了城,他什么都不是。不过,自从遇到小羽之后,我对这些城主有了别的兴趣。
完成简单的收编后,我找到了之前那个领军的人。在了解到他叫烽火后,我问他城主在哪儿。
他表情有些不自然,犹豫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才说道:“晚歌城已经很久没有城主了。硬要说的话,那就是他了。”他伸手指了指城楼。我一下就想到了刚才那个忙碌的身影。
我很轻易地就找到了身形微胖的他。他还在忙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我发现了他原来是在点火。差不多每个垛口都燃着一堆篝火。篝火似乎并不只是在今天燃起。城墙的大部分都留下了长期被火熏烤后的痕迹。这些篝火又是为什么而燃呢?
我走过去问他:“你在做什么?”他好像没有听见,直接就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把一堆已经熄灭的篝火重新点燃。烽火走过去拉住他,向他说道:“人家在和你说话。”烽火的语气很不客气,可所有人都仿佛习以为常。晚歌城城主也不是很在意,只是顺着烽火手指的方向看着我。
他的额头和右侧脸颊上沾满了因擦汗而染上的灰烬,但这并不影响他眼睛投射出的清澈的眼神。那是一种不染世事的澄澈。
我把问题重复了一遍。他才磕磕巴巴说道:“我在……点……灯笼。”我又问他为什么要点灯笼。他这下到不磕巴了,很流利地说道:“娘亲说的。”不远处,有处篝火又熄灭了,他连忙跑过去,嘴里还说着:“娘亲说的。娘亲说点了灯笼回家就不怕了。”似乎说到了他喜欢的话题。他这回一边添着柴火,一边嘴里念叨着:“孩子……贪玩……回家……不怕黑。”
我可以确定他确实没有经过世事的渲染了。
烽火有些羞愧,说:“他就是个傻子。”我转过头看他,想知道他话语之外的意思,但一无所获。我看着那个点燃篝火后拍手大叫的身影,一句话吐口而出:“不是。他不是。”低沉的声音被急劲的风吹到篝火里,瞬间燃烧殆尽。
烽火说:“他以前常常玩的很晚才回家,他娘亲总是在府前点了很长一路灯笼迎他回家。”我问他:“他一直都是这样吗?”烽火点点头说:“他一生下来就这样。他娘亲以前在城里的挂满了灯笼。因为他娘亲待人很好,经常做些善事。城里百姓看到他玩的晚后都会帮着点灯笼。他只要跟着灯笼就能回到家。他,只是个傻子。”
“他娘亲?”
“有次她在城门口布施。城外来了个乞丐,在接近她后变成了一头城门高的巨狼一口把她叼走了。没找回来。他当时就在旁边玩耍。”
“狼来了?”
“嗯。他后来就天天站在城楼上。只要有人从城外来就喊狼来了。所以你们来的时候,我们才没什么反应。”
“篝火?”
“一次看到守城的士兵晚上点篝火守夜之后,他就一直在晚上点篝火。他把那当灯笼。他以为他这样做父亲和母亲就会回来。”
“他父亲?”
“死了吧。出城去寻找巨狼再也没回来。留下个傻儿子城主。”
我绷起脸盯着烽火看。他看到我盯着他看,身体站的很僵,拳头松开握紧重复了好多遍,胸口起伏很大。他看我不说话,张口想说些什么,一个我字在嘴边饶了半天。我笑了笑,说道:“我不会杀他的。”
他脸一下涨的通红,才低低说了一句谢谢。我摆摆手,往城楼下走。他没有和我一起离开,反而是直直跑到了那个傻孩子跟前。
“你看你,又弄的这么脏。”他诡异地掏出一块手帕替傻孩子擦汗。他原本就瘦削的身影被火光映在墙壁上,快成麻杆了。
傻孩子不理他,只用劲挣开瘦孩子抓着他的手,眼睛盯着又一处灭掉的篝火,嘴里焦急地喊着:“火……火……灭了。”
瘦孩子追着傻孩子的脚步,也着急地说道:“哥,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慢点。”
我回头看了一眼。两个孩子蹲在地上。两个孩子蹲在墙上。围着同一团篝火。两个孩子伸手挑动火焰,神色专注。两个孩子帮另外的孩子擦脸,神色同样专注。漆黑的天空上闪着密密麻麻的星星,像一片灯笼的海洋。
后来我知道晚歌城前城主有两个孩子。大的傻了,当了城主。小的聪明,却从不越位。
走的时候我问了瘦孩子:“为什么不取而代之?”瘦孩子看着不远处的傻孩子,微笑说道:“娘亲说哥哥太善良容易被人欺负,要我好好保护他。父亲说,这是我欠哥哥的。”
我闭上了眼,想起了我的娘亲。
那天桃山上桃花全谢了。娘亲躺在床上,我跪在床前。娘亲笑着,我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