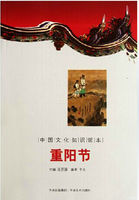父亲苍白的脸色、下陷的两鬓和双腮、没精打采的眼神使他看上去衰弱不堪,吃惊之余我赶紧给他炖鸽子汤、羊肉汤吃。我照例撇去浮油舀上几块肉和胡萝卜再加满汤端给父亲,但每次他都不听劝阻只吃下一块肉。吃完一小碗,父亲便悄然躺下了。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直吃肉少喝汤多,而且习惯于滗去泡过馍馍的肉汤,重新盛入热的才吃,总是放下饭碗就忙活去了,而且经常要在午饭前加一餐的。
上千里的旅途劳顿让父亲卧床了三天,第四天父亲扣上棉帽说要出去走走,我赶紧扶着他,他说不用,并用干枯的大手推开我。走了几十米,父亲拄着拐杖停下来,无声地站了一会儿说回家吧。从前父亲是很能走路的,家里拉麦捆的毛驴车走上坡路时,即使五六里路他也会靠自己的两条腿走完,就是前两年他也能一气走二里多路。
父亲患便秘有十年了,可他连蜂蜜水也不肯喝,更别提茶水了,我只好每顿饭必做汤,两星期后我就江郎才尽无计可施了,于是我买了豆浆机帮忙。一天,父亲向我要果导片,我才知道他一直没通便,算算已有十二天了。我很自责就把药瓶给了父亲,傍晚他告诉我好了,我心里一下放松了,原来没啥大不了嘛!可是没过半个钟头,父亲开始一趟趟地去卫生间,到后来干脆不出来了,我害怕了,让他躺在床上,换成我一趟趟地去卫生间。一问,原来他一次吃了四片药,天哪!我不敢给他吃止泻药,喝了好多糖盐水,第二天中午总算停住了,谢天谢地!经此一场我变得唠唠叨叨了,顿顿劝父亲多吃饭,经常询问他通便的事,还好总算有一点点效果,再没发生过类似的事。父亲的精神渐渐好了些,我也忍不住有些小小得意。
不经意间我的手触到晾杆上的父亲的毛巾,却是水淋淋的。很奇怪,看向父亲的手:骨节突出、僵硬多斑,这还是我熟悉的那双手吗?拧毛巾的姿势仍然是将毛巾折叠放在掌心,两手合实一扭。多少年来父亲就这样拧毛巾、拧我们的小衣服!记忆中父亲的大手光洁而有力,这双手能蒸出暄暄的大馍馍,能搓出长长的芨芨草绳,能焐热孩子被冻僵的小手……我泪意阑珊。
给父亲剪指甲,翻转手掌很费劲,指甲又厚又脆,居然越打磨越糙。父亲的头发和胡须长了,理发店他是从不去的,晚饭后,我用一把小梳子篦着用剪刀剪,没想到居然理得很平整,正自得意,觉得剪下一软,看了看,还好没破。·第二天我心虚地再看时,发现父亲的鬓间凹坑边沿果然有一块伤痕,怪他怎么不吭气,他淡淡一笑说没什么。
给父亲搓背时,我看到曾经熟悉的那个大瘊子疙瘩竟然瘪塌塌的了。曾几何时,弟弟和我一左一右睡在父亲身边。玩闹够了我就给父亲抓痒痒,手里玩弄着瘊子问东问西,总有说不完的话。
和父亲在一起的半年,我看到了他的老迈,真正体会了看到亲人生命的活力在一点点暗淡却无能为力的悲哀和痛苦。
(作者现供职于巴里坤县保密局)
我的骑士我的爹
柴雪琴
一身红色的骑行服,面戴飞巾、防风镜,骑着很拉风的公路自行车风驰电掣,这老头还挺酷。没错,他就是我爹。
我和我爹,最好地诠释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句古语。他是固执的蓝,作为女儿,我的固执则已升级为青。也许是他血液里的不可驯服流淌到我的血管里时,已经得到了提炼升华,三十多年后,在经过无数次的横眉冷对和唇枪舌剑后,爹终于无奈地向我认输:你行,你比老子厉害!
小时候,对于经历了九死一生后依然体弱多病的我,严峻冷面的爹格外宠溺,以至于我对他的放肆已经到了蹬鼻子上脸的地步。只要爹瞪我一眼或吼我一声,我就会以刘胡兰大无畏的精神和他冷战到底。每次,都是爹微笑着向他这个不懂事的小女儿亮出小白旗。
不知怎么一晃,我就工作了,成家了。爹好像也突然发现了这个女儿的不成熟和不理事,这分明就是家庭教育的失败范例啊,一贯以严谨治家骄傲的爹顿觉老脸蒙羞。毕竟,女不教貌似也是父之过啊。
爹大概是觉得有必要为我补上落了几十年的课,常常对我的不通人情和不懂世故进行劝诫和训导。可是晚了,我的心智已经成熟,早已过了启蒙的阶段,长此以往,焉能不烦。于是,往往是爹冲我一瞪眼,我就对他拉下脸;他思想政治课的铃还没打响,我就给他扔下一句“你别管”;老头子一吼别人能吓得抖三抖,我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刘胡兰,看你能奈我何?日复一日,父女关系不断恶化。不过有时候爹不经意的一句话,对我还是颇有教益的。这么多年,除了年龄和容貌,我似乎从来没有改变,性格不曾变,就连多病多愁也不曾变。每次生了病住了院,爹马上会忘记前仇旧恨,寸步不离地守在我身边。
2008年,肿瘤医院。爹对他的太太不放心,对他的女婿也不放心,一定坚持要亲自陪护在我的病床前,甚至全然忘了女儿已经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一勺一勺地给我喂饭。
一个月前,红星医院。爹放弃了他退休后最钟爱的骑自行车活动,每天清晨在我还熟睡时就来到了病房。CT室,胃镜室,化验室……爹在前面走得雷厉风行,我在后面赶得气喘吁吁。一瞬间,时光就像退回了许多年,或者时光一直停滞在许多年前,爹始终是那个英姿勃发的年轻父亲,我还是那个年幼胆怯的懵懂女儿。
不管多么恨铁不成钢,爹严厉的外表下,永远跳动着一颗慈父的心。
几年前,爹在哥的鼓动下,毅然投身于近年来风靡于许多人中的骑行活动,从此视车如命,并且立下环游全国甚至全球的凌云壮志。一贯与爹以互相打击为乐的我,则对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风言冷语,对他的活动百般阻挠。其实,我内心真实的想法是对爹的出门在外担忧不已。这一点,我不说爹也不懂,我说了爹也未必领情。在这个家里,似乎青与蓝多数时间都在对立。
后来,看着爹每天骑着自行车精神焕发,乐此不疲,我的想法渐渐有了改变。是啊,人这一辈子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才是最大的快乐。我骨子里对自由的迫切向往,其实也是爹给我的。
今天是父亲节,爹正在往返三千多公里的骑行路上。在路上,他体验着艰辛,也收获着快乐。作为女儿,这次是我认输,爹,一直以来,还是你厉害。
也许,在每个儿女的内心深处,父亲都是一位勇敢的骑士,危难时刻,骑着战马拔剑相护。
我的爹,花甲过后依然骁勇善战,他何尝不是我的骑士?也许今后的日子里,青与蓝的征战还会此起彼伏,可是我永远都是赢在表面输在心底。
一路顺风,我的骑士我的爹!
(作者现供职于哈密开发报社)
生命中的宝贵财富
杜文霞
巴里坤生火炉的燃料是焦炭,经久耐烧火力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运输焦炭的主要工具是毛驴车。
我们村去县煤矿拉焦炭约有二百里路,赶毛驴车拉炭,至少也得三天时间。若是热天,时间再久点也无所谓,但农民们大都选在冬天,因为冬季里没有其他更多的农活。
记得那是1976年的隆冬,爸爸要我和他一块儿去拉炭。那年我十一岁,第一次出门,何况是赶夜路。兴奋得我钻在宽大的皮袄中一丝睡意也没有,把皮袄领子拉紧了蒙住头只露出眼睛,瞅天上的星宿。记得奶奶教过的,那银白色的长带是天河,天河那边有颗很亮的星是织女,这边一颗亮的星是牛郎,牛郎前后两颗小星星是他们的孩子。
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总算到了煤矿。远处低矮的山包上泛出一层黑黝黝的光晕,空旷的大戈壁上零散着几墩红刺,几座竖起的井架东一个西一个地在风中咝咝尖叫。炼焦池中冒出的浓烟引领我们到装焦炭的地方。
“懒人不出门,出门天不晴。”大概是应了这句老话,老天爷见我这“小懒人”·第一次出门,果然变脸。西北风带来的浓云黑压压地盖住大地,炼焦池中扬起的煤灰让人睁不开眼睛。装好焦炭,我看爸爸只有白眼球还保持原色,脸上抹了一层黑,皱纹里的黑灰得用指甲才能抠出来。我想我一定和爸爸一模一样,一个姑娘家这咋见人?
快走吧,天气不好,能在下雪前走出山就好办些。爸爸说着抹一把脸赶车就走,脸比天更黑。我已经累得走不动了,手紧紧抓住车辕由车子拖着向前迈步。爸爸把我抱上车,我坐在焦炭上立刻睡着了。后来,爸爸把我抱下了车。我睁眼一看,大片的雪花已经纷纷扬扬,快到地面又被风卷·起不知带到哪里去了。“‘人算不如天算’,急也没用,还是消停些好。”爸爸说着卸车喂驴,在路边的避风处抓几把雪擦擦手脸,我也照他那样抓起一大团雪。爸爸说,多擦一阵,手脸就不会冻坏。我连续换了好多次雪,使劲地擦,雪全变成了墨汁,不过手脸反而不再僵硬。
我和爸爸围着火堆烤化了冻得石头似的馒头,填饱了肚子。雪下得更大了,路上的雪没到脚面,松软得像刚弹过的棉花,踩上去绵绵的。可毛驴拉着千斤多重的车在雪中就更费劲了,鼻孔里喷着白雾,艰难地迈动四蹄。我不忍心再坐车,也因为坐车太冷了。我问爸爸,这得走到啥时候才能回到家。爸爸说:“走路不要算,跟上车轱辘转。”
正说着话,走在最后的那辆车“嘭”的一声,车胎爆了。我“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常听妈妈说“瘸腿上拿棒敲”这句话,这次真让我碰上了。其实毛驴车爆胎的事很平常,可现在爆得也太不是时候了。爸爸忙哄着我说:“不怕,一会儿就补好了。老天爷想叫你多看看下雪呢。”谁知他去车上取补胎的工具时,才想起工具包忘在焦炭池旁了。
天全黑了,只能看到四辆毛驴车像四座小土地庙,爸爸急得围着“庙”转,又不敢让我看到他愁苦的样子,嘴里还一个劲地说:“霞霞,不要害怕,瓜娃子有天保呢。”
突然,我听见了车轮碾压雪地的声音,心止不住怦怦地跳,爸爸也听到了,高声呼叫。不一会儿,迎面照来的手电筒光柱穿透风雪,把爸爸的影子拉得奇长。一拨毛驴车少说也有十几辆,停在了我们的车旁。四五个小伙齐刷刷地拥过来,问清情况,三下五除二扒开外胎、补好内胎。他们七嘴八舌地对爸爸说,咋叫这么小的丫头干这么苦的活?接着又拿出食物让我吃。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爸爸千恩万谢,问他们的名姓。其中有一人朗声笑道:“相逢何必曾相识,走好你们的路就是了。”那时的我还听不懂他的话,爸爸大概也不全懂。记得我们走了没多远,爸爸意味深长地说,这个人文墨深呢。
从此以后,我生火用炭可细心了,养成了过日子节俭的习惯。而那个漫长的雪夜也成了我生命中一笔价值不菲的宝贵财富。
(作者系巴里坤县花园乡农民)
父亲和哈密
谭悟远
说起哈密,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我的父亲,总觉得他们的很多品质是相似的,父亲也总是把他在哈密奋斗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他说他以这座城市为荣耀。
总想把爸爸和哈密联系起来写一篇文章,却又不知道怎样下手。想来想去,觉得任何体裁的感觉都不对。后来想,干脆就把这些记录在纸上的、点点滴滴的事情都写在一起好了。
最初的时候,父亲还在四川山区,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之后,却因为没有学费,无法继续学习。当时的他,仅仅十六岁,为了不再给家人增加负担,就倾尽自己所有的财力,搭上了来新疆的火车,第一次踏上了哈密,开始了自己的热血青春。父亲说,他当时没想过什么“建设边疆”之类的理想,只是在这个地方生活得越久,就越觉得离不开了。
父亲刚到哈密,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当小工,帮着施工队盖锅炉房。因为身体瘦弱,搬不动沉重的水泥砖块,所以只是干一些相对轻松的活儿。大家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他用自制的竹笛,为工友们演奏乐曲,调节大家的情绪,放松他们的身心。后来,工友们也渐渐记住了这位四川来的小伙子,到顺利竣工的时候,都舍不得与他分别。直到现在,父亲路过那座锅炉房的时候,还自豪地告诉我们,那是他修的。
年轻人的心总是闲不下来的,为了维持生计,父亲利用大家午休的时间去卖报纸。那一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在零下三十四摄氏度的严寒下,因为手指被冻僵,无法伸展,父亲就托着报纸卖,一天卖一千张,但是,一张只能赚到四厘钱。最后,父亲用十个手指甲全部被冻掉的双手,第一次为爷爷奶奶寄回了新疆打工的第一笔钱。
父亲说,当时他决定来新疆的时候,爷爷奶奶并不知道,为了不让他们操心,就骗他们说是出来上学的。那时父亲就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爷爷奶奶过上好日子,让家里人过上幸福生活。现在的父亲,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爷爷奶奶也以自己的儿子为骄傲。
和父亲同期打拼的那些伙伴,现在依然和父亲是好朋友。他们逢人就说,我为了建设哈密怎样怎样;而父亲逢人却说,哈密对于我怎样怎样。
当时到哈密的时候,这里一个亲戚也没有,父亲也是从那时开始严于律己,不抽烟,不喝酒,也从不和别人一起打牌、打麻将。他把业余的时间用在学习上,后来,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从学徒奋斗到大师,从打工到管理,是哈密这块甜蜜之地给他创造和带来了甜蜜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