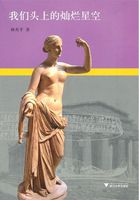在卧室柜子的一面玻璃上,有一张婴儿的照片,大姑姐一看就喊老公,“快看,你小时候的照片。”老公拿起来说:“这是大哥嘛!”大伯哥已经故去近二十年,据大姑姐说,公婆很早就离婚了,四兄弟归公公,大姑姐归婆婆,公婆相继离家后,留下无人照顾的兄妹,当时最小的孩子,也就是小叔子才七八岁,老公也只是个初中生。于是大伯哥担起了家里的重任,一人带着几个弟弟妹妹。为了给弟弟妹妹们交学费,他拼命打工挣钱,终于有一天在天不亮就出车时出了车祸,死时还不到三十岁,为了弟弟妹妹,他一直未娶,成为弟弟妹妹们心中永远的痛。正因为这样,在弟弟妹妹们的心目中,他才是真正的“父亲”。据说,离婚后就很快“失踪”的公公在大伯哥去世后专门回去看了一趟。
有些遗物在我看来很奇怪,有几张毛主席像,看年代已经相当久远了。一个皮质相当好的手拎包,装着些过期的票据。老公说,公公年轻时很能干,从内地来新疆后,在农场里做过连长,当过厂长,离家后,在新疆和内地都辗转做过生意,曾经也风光过。后来可能做生意赔了,身体也在恶劣的环境里糟蹋坏了,等到在乌鲁木齐市的房东驱车百里赶到芳草湖找到二伯哥,告诉他去接人时,看到蜗居在小宾馆的公公已经浮肿变形得几乎无法辨认。我想起来,平时公公在家里看的电视节目,很多都是农村致富类,看来他在求富的路上从没有停止过追求。可能正因为如此,当他因严重肺心病不得不天天窝在床上时,才会不时发些火,那些火不是对他人,而是对自己。经常在半夜,我们都上楼睡了,他因为呼吸困难、心跳加剧无法入睡,就一直守着电视,对着电视大发脾气,骂这个人,骂那件事,老公有时候不解,说和他一起看电视很烦,我说:你要理解他,他也着急呀,好强了一辈子,现在连生活都快无法自理了,他当然很着急,很烦躁。
没给出去的红包
整理遗物时,大家发现了四个红包,老公把钱抽出来数了数,每个红包三百元,总共一千二百元。老公转身对大姑姐说:姐,这是爸过年时给你们一家三口包的,你们没回来就放下了,这另外一个是怎么回事呢?大姑姐佯装整理床头,没有转身,只是不时发出叹息,可能还有抽泣。我知道老公这样说有些残忍:公公离家二十多年,大姑姐再没见过他,2006年,公公被接回家,住在外地的大姑姐有几次机会去乌市学习,与公公只是相隔一百多公里,她却一次也没有回·去看,今年春节本来说好要回,可又因事拖延,等到赶来,已经是公公去世的·第二天,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想起过年前和过年期间我几次让老公打电话催促她,她一直不回,我虽知她家里情形复杂,但一想到公公心里那巨大的遗憾,心里还是有些不忍。
年三十那天,因为二伯哥一家也来哈密过年,公公的心情大好,他走出卧室,坐在沙发上一直看完了五个小时的春晚,吃团圆饭时,他吃下了五个饺子,几小时后又吃了一小碗面,他的表现让老公有些害怕,提醒说:“爸,你可不能好一点就这样吃,别吃坏了。”中间有亲友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用少有的高声说:“今年过年,我该见的人也都见了,我真的心满意足了。”我似乎听出了遗言的味道,心里开始隐隐地不安,我想到了该回而未回的大姑姐。作为家中唯一的女儿,我想公公曾经是很疼爱她的。
公公去世第二天,大姑姐赶乘下午的飞机回来,我一直不安地揣测:她会放下那些怨恨吗?她会后悔没有见上父亲最后一面吗?当我从卫生间出来,突然听到本来冷清的灵堂里传来阵阵哭声,我知道她到了。走进灵堂,看到她跪在公公的遗像前,哭号声中夹杂着痛悔的告白:“爸,我过年应该回来的……”大家好容易扶起她,她又哭倒在老公怀里,不停地捶打着他,很久才平静下来。出殡那天,瞻仰遗容,她又痛哭不止:“爸,对不起……”事后在家里,她还在不时叹气。
清理遗物时,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就告诉大家:那另外一个红包,可能是给小叔子的女朋友的。公公在过年期间,可能太渴望儿孙都各得其所,可能也是病入膏肓产生的幻觉,他曾追问小叔子是不是答应要在过年期间给他一个惊喜,也就是带女朋友回来准备结婚,对此,小叔子坚决予以否认,事后小叔子还对公公的“糊涂”觉得很可笑。当听到这最后一个红包是给他女朋友的,小叔子眼圈红了,再不说话了。守灵的几天里,小叔子几乎没有吃过一顿完整的饭。
头七那天,老公把红包给到了要给的人手中。
跟岁月和解
公公最后的日子是在我家度过的,前后不到半年。
因为婆婆的唠叨,我一直对公公有先入为主的差印象:脾气暴躁,吃饭挑剔,而且花心。所以,去年老公说要接公公来住,我犹豫了之后虽然答应了,但一直心里打鼓:能和这样的公公处好关系吗?
去年刚入秋的一天,女儿兴奋了一夜,我则紧张了一夜,终于迎来了公公,当老公扶着极度瘦削的他走进屋,我被震动了:他面容清瘦,神态淡然而疲惫,尤其是一头花白的头发浓密而厚重,带着太多岁月留下的沧桑,让我莫名的不安和嫌隙瞬间冰释:原来那个暴躁张扬的公公如今只是一个虚弱无力需要人照顾的老人了。我的心立即柔软了,那一刻我想起一句话:跟岁月和解。
刚来时,公公身体还好,可以自己烧烧水,煮个面,有时候还能帮着洗一下碗,这让我比较宽慰:原先我想他可能已经无力自理,在他来之前一直在四处找保姆呢。看他身体好,精神也不错,我也放松下来,每天回·家,炒上一两个荤素菜,为他煮个粥,他似乎也挺高兴,在谈话中不时不着痕迹地表达他的满足与感激,看电视节目时,他经常会很清晰地分析事理,谈自己的观点,当然也不时犯老人的通病———偏激。有时候他还会拿些笑话逗孙女玩,从他的谈吐中依稀还能看出他年轻时的精明与智慧。
对公公的好感主要是因为他的安静,和泼辣饶舌的婆婆相比他实在是太安静了。有段时间,公公身体不错,经常早起到自家院子里转转,那可能是他最好的状态了。平时,他几乎没出过大门,出去就是上医院。现在,站在楼梯上,我好像还能想象那种情形,当然那并不多:晨曦中,公公背着手,站在院子里看那棵大梨树,看没有亮的天空,看我看不见的许多东西……微明的天光中,他枯瘦单薄的身影安静而又孤单。
整理遗物时需要箱子,我去楼上腾箱子,看到了一箱子红艳艳的干辣椒,那是公公晾制的。去年仲秋前后,他觉得自己身体还好,就让老公买来几袋青辣椒,自己动手晾干辣椒,每天坐着要干一两个小时,这样连着干了几天,身体吃不消,病倒了,一连躺了几天才缓过劲来。
现在,想起他的安静让我十分难过:住在这个异乡城市,守着我家这座陌生的屋子,他度过的这最后一百多天,有多少天就是这么安静孤单过来的。我只希望,在那个世界里,多个贴心的人陪他,让他的世界里多些欢笑。
晚上,如果老公不在,我也陪他聊聊天。聊天中,我越发厘清了婆婆的误解:年轻时,公公做一个工厂的领导,泼辣的她疑心重,经常上门找女工的麻烦,几乎和所有女工都打骂过。为此,公公很生气,下狠手打过她,她却根本不悔改,而且怨恨了公公一辈子,甚至教我年幼的女儿记恨爷爷,以至于女儿前几年第一次见到爷爷时,第一句话就是:“爷爷,我恨你,因为你打奶奶!”说起此事,公公泪流满面,我安慰他:“她说什么,孩子也不一定全信,孩子也有判断力呢,当时小不懂事才那样说,现在你看她,和你不是很亲吗?你来前一天,她高兴得不得了,前一天晚上都兴奋得睡不着觉。”想起女儿平时和他挤在沙发上,非要和他手拉手时他幸福的笑容,我知道他是欣慰的。
公公在医院里抢救时,我带女儿匆匆赶到,公公已经走了,女儿眼泪汪汪地求我:我想看看爷爷。当时护士正在给遗体消毒穿衣,女儿不能进去,她就走到一边悄悄抹眼泪。回到家里,卷走铺盖的床显得很空,床头的一张高脚椅上是他吃过的药和一些小吃,有许多是女儿拿给他的。床脚边是一根自制的拐棍,那是一根弯曲的毫无装饰的木棍,棍头上缠着一块红线包裹的黄布,简陋粗糙,很扎人眼。女儿看着,轻轻地说:爷爷太可怜了。
不称职的儿媳
其实,追念公公主要是源于自责:天气转凉后,我因为做了两次小手术,不敢太动凉水,也不宜多做家务,中午晚上都回娘家吃饭,就少了对他的照顾。为了照顾公公,老公天天中午要匆匆赶回去做饭,加上单位事不顺,脾气也大了,我只当他嫌我懒散,想着自己没有恢复的身体,也来了火,两人就常吵,有一次我又带气出门,临走还对他发狠说:我就是不想再过这样的生活了!事后才想起,敏感的公公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以为是我嫌弃他在这里。再回到家里,我照顾他又主动了些,可又值年末,事情众多,无心去为他做更多事。有时候我问他想吃什么,他怕我麻烦,就问:你们吃什么了?我说我们吃过了,他就立即说:那就不用做了,我不想吃。我知他怕麻烦我,就坚持去煮面或者煮粥,有时候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累了,就当真他不想吃也就不做。有时候心情不好,回到家就连招呼也不打。想着他成天出不了门,一个人在家一闷一天,我也不是没有愧疚,于是经常在做饭时让女儿去替我问候,女儿贪恋电视,常常省去了这道程序……我曾经想给公公解释一下,可一想自己得的是妇科病,和公公说不合适,就放弃了。
公公去世前两天,可能出现了幻觉,有一天晚上我进屋问他想吃什么,他突然指着墙说:“你们的梁坏了。”我一看墙,没有发现任何异样,他又说:掉土,掉我裤子上了。我看裤子上确有一点点白灰,就说:没事,就是墙皮掉了一些,经常这样。那天,他很奇怪地提出要开着灯睡觉,说自己害怕,我听完感觉诡异,打开灯就赶紧上楼去睡了。后来,母亲提醒我,我才发现,公公去世前脚肿得很厉害,加上幻觉,这就已经是病危迹象了,可我们当时还是没有太重视,以为送医院就可以了,也没有在跟前多陪陪他,想想自己的自私,现在还觉得心里发冷。
追悼会上,在瞻仰遗容时,看着痛哭的老公一家兄妹,我也眼泪直流,我真想对老公和他的姐弟们说:对不起,我在最后的时间没有照顾好爸爸。可我不敢也不忍。
最后,我还是想对公公说一声:爸爸,走好,原谅你不懂事的儿媳吧。
祝公公在那个世界里安宁快乐!
(作者原名任江梅,哈密地区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哈密地区邮政系统)
追梦的公公
天街小雨
接到丈夫的电话,我立刻打车前往地区中心医院。七十多岁从未住过院的公公突然晕过去了,并且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全家人围在公公的周围,紧张、焦急地看着医生对他实施抢救。终于公公苏醒了。当医生问他叫什么名字时,公公竟然回答:“左宗棠。”医生感到莫名其妙。这样的回·答也只有家人知道。因为他正在写关于左宗棠的传记。据婆婆说,公公就是在写作时晕倒在桌子旁的。我想:这大概就是他晕厥时大脑中仅存的名字吧。
公公这个人除了写作好像没有什么别的爱好了。多年来他笔耕不辍,过着常人看似“苦行僧”一样的爬格子的生活。而他却心无旁骛,每日都徜徉在文字的海洋中,乐此不疲。退休前,作为高中语文教师的他白天到学校上班,晚上和休息日就进行创作,可以说是兼职的作者。退休后,他就成了全职的创作者了。公公整日坐在家中创作,可以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他的人生字典中仿佛就不存在打打麻将、休闲度假这类退休养老的生活内容。
公公对自己是十分严苛的。一个退休的人,每天的工作时间甚至比上班的人还要长。时间在他这儿总是被充分利用。七十多岁的人了,每天写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有时一坐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婆婆说:“写起来什么都忘了,就连吃饭都要叫他好几遍。”子女们劝他不要长时间坐着,要多活动活动,对身体有好处。他总是当作耳旁风,仍然我行我素。
就这样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公公的电影剧本终于大功告成了。望着一本本装订整齐、书写规范的手抄稿,我惊叹不已。这些都是他经过一遍遍修改,又一笔笔抄写出来的。其中凝聚着公公多少的汗水和心血啊!满怀着希望的公公背着这沉甸甸的手稿踏上了内地某个电影制片厂。洽谈顺利,并签订了合同。心中有了着落的公公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家中。他只需等待自己的剧本被拍成电影在全国播放。漫长的等待终于换来了电影的正式播映,而且此电影还获得了全国性大奖。公公那高兴劲就别提了。可是当他看到字幕中编剧并不是自己的名字时,他惊呆了。谁知等待自己的竟然是一个骗局。这对公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所有的心血就这样付诸东流了。他怒发冲冠,声称要去讨个说法。可翻出合同,仔细查看后也只能作罢。原来在他签合同时就已经被人家骗了,只是自己还浑然不知。长期闭门不出的公公哪里知道这些人的心已如此险恶,竟然公开掠夺别人的劳动果实而不知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