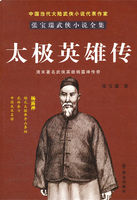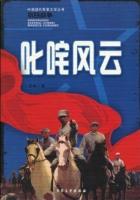林荫道边极窄的人工草坪,无名花开得鲜艳又茁壮。一个瘦且矮的男子蹲在栅栏边,自得其乐地调理着一只绒线鹅。你看他自如地左右抖动右手上的调节杆,鹅的脖颈往前一抻一抻,贝壳的蹼掌便一右一左向前大腹便便地迈动。绒线的鹅有乳黄的冠、颀长的颈、丰满的向后撅挺的女人味十足的臀部。绒线的鹅是只天生俊秀、端庄、伶俐的鹅小姐,男人都会为之倾心。
想要吗?那矮且瘦的青年问。
其实它不过是用红绒线穿起来的玩具,那根绒线在石板地上像根鸡肠。它的原理不过是来自木偶的启发。村平走过两步。哎,便宜点卖你,那青年在后面喊,没事在家很好玩的,边说边赶着鹅小姐追上来。
那鹅小姐一颤一颤的,红着脸,气喘吁吁。村平动心了。
技巧很好掌握。因为脖颈、胸腹、蹼掌的提线都一同系在调节杆上,只需提起绒线,鹅小姐便亭亭玉立,左右晃动调节杆,鹅小姐便姗姗而行。
村平蹲在地毯上,自己的脸与鹅小姐几乎在同一水平面上。他怀着十二分的兴致欣赏鹅小姐的步态,一会儿是宫廷仕女,一会儿似时装模特儿,一会儿如现代白领丽人,一会儿像体操运动员。倘若累了,她便彻底蜷成一团,把头、胸腹、蹼掌都平放在地上,宁静地进入梦乡。她才是无忧无虑的乐天派,永远有快乐,永远有生气。
哈,你在跟谁逗乐呢?小许开门进来问。
一位小姐。
小姐?
喏,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鹅小姐,这位是许小姐。
什么呀,一团绒线。小许大笑起来。
你不要笑,你看。村平熟练地操作调节杆,鹅小姐跳起了欢快的踢踏舞。那双贝壳蹼掌踩点准确有力,姿态优美。
嘿,有意思,让我玩玩。小许抢过调节杆。
左右晃动。村平教她。你看她走起来了,像个贵妇人。
小许饶有兴致地领着她满屋转。你从哪儿领来的?
路上。
瞎说。
真的,在皇苑酒店旁边的林荫道上,一个又矮又瘦的小伙子在那里逗她,我看着好玩,就给你领回来了。村平说。
谢谢你。小许停下步,双眸温柔地凝视一下村平。这是村平熟悉的眼神,小许真情洋溢时,就是这样。
村平若无其事地说,我也喜欢她。来,鹅小姐,到这里来。
小许便领着她到村平跟前,轻轻一鞠躬,说,见过陛下。
免礼,请平身。村平假模假式地说。
那一晚,两人少有的开心。关于结婚纪念日引起的隐隐的不快很快淡忘了。
第二天,村平下班回家,开了房门,不禁愣住了。一条两米来长的铁轨横亘在客厅的中央,小许正蹲在地毯上垒一个车站。哎,你回来得正好,第一列火车通车典礼就要开始了,快请上车。
村平乐了,蹲下身子问,你哪儿弄来这么长的铁轨?
你先上车。小许边说边推村平一把。
好好,村平说着跨过机车的头顶,蹲在小许对面。商场有卖这么长的铁轨吗?
小许拍了拍手,说,好了,剪彩开始。
我说你是怎么弄到这么长的铁轨的?村平又问。
小许抬起头,看了村平一眼,等通车典礼完了再告诉你行吗?
那好吧,村平禁不住用手抚摸着锃亮的机车头。
还别说,现在做的这些玩具就跟真的一样。又端详挂着的三节车厢。哪一个是软卧?我想坐软卧。
都是,你随便挑吧。小许边说边启动遥控器。呜!
呜!火车鸣叫着,徐徐驶出车站,逐渐加速,咣吱咣吱向前驶去。
再见,村平说着向小许招招手。
小许也立起手掌向驶远的机车挥手。
哎,你还记得头一次送你回家的情形吗?村平问。
还说呢,差点误了车。
那可不赖我,地铁不走,足足耽搁了半小时。等赶到北京站时,还差五分钟就要发车了,差点都没让检票上车。小许瞥了村平一眼。
不管怎么说,是上车了。
都没来得及挥手道别,所以体会不到月台相送的浪漫滋味。
第二次就好了,从从容容,提前两小时就到了车站。
可是候车室里的空气却让人憋得难受。
进了站,又在月台等了二十几分钟。
好像我还不是靠月台的位置,一会儿过来支着茶几说几句话,其实那些话都不知说多少遍了。
然后你就说,干脆你先走吧。我说没几分钟就开车了,再等等吧。
可是等到开车时,我却不能坐在窗口,从从容容地跟你招手道别,只能斜着身子,尽力伸长手臂,象征性地挥两下。不过,那次我还真有点担心你一个人留在学校过春节会不会出事。
能出什么事。村平不以为然地说。
火车的机车从相反方向又驶回了起始站。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怎么弄到这么长的铁轨的呢。村平又说。
也是凑巧,刚巧有两套机车头都出了毛病,卖不出去,我就说,干脆把铁轨都卖我吧。售货员很爽快,她巴不得赶紧处理掉那些残次品。
我突然有个主意,我们再去买几套回来,把三个屋子都用铁轨连结起来,搞一个复线,两部机车,我们分别操纵,既可以比赛,平时,还可以用小火车运一些东西,比如从厨房运一杯奶到卧室,这样,我们甚至在床上不起来就可以吃上早餐。
太好了。小许兴奋得脸上泛出酡红色。两人出了门直奔西口那座奶白色的商场。
还是那个女售货员,她一眼认出了小许,诧异地问,你们家有几个孩子?
小许与村平对视一眼,说,两个。
售货员边从柜底下抽出成品包装盒,边说,现在的孩子难缠,说要什么就得给买什么,还特自私,自己喜欢的玩具就是不让别人碰。
我们家的也是那样,没办法。不过,你们用得着买这么多副吗?
我们跟孩子一起玩。村平说。
两人兴冲冲回到家,很快将卧室、客厅、厨房用铁轨连接起来。
小许在厨房,村平在卧室。村平问,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小许回答。只听,呜!呜!两列火车从卧室和厨房同时开出,咣吱、咣吱,逐渐加速,风驰电掣,在客厅墨绿的草原上相向行驶,然后交会,擦身而过。从厨房,小许给村平送去一小杯奶;从卧室,村平给小许送去一枝还未枯萎的月季花。两人整晚乐此不疲。火车汽笛不停地鸣叫着,好似整座大楼都在火车的鸣响和铁轨的震动中战栗。邻居纷纷猜测,北京西客站大约是通车了。
随后,村平给小许买了一个自动娃娃(他负责守卫车站和监督列车运行)和一副玩具对讲机。小许呢,给村平买了辆遥控赛车。
两人下班后,草草吃完饭,小许便领着绒线鹅和自动娃娃沿铁路线巡视一周,检查铁轨是否平整,然后用对讲机通知村平可以发车了。
村平启动开关,列车便徐徐出站,村平用遥控器驱使着赛车与火车展开了紧张激烈的角逐。初时,地毯对赛车来说太柔软,毛茸茸的,要么发挥不出速度,要么受到图案和纹理的障碍,动辄转向甚或翻车。村平说这不公平,火车有铁轨,赛车也得有跑道。于是,就在地毯上用三合纤维板裁了一条笔直的车道。村平得意地说,顶级的高速公路也未必能与之媲美。果然,再比赛,赛车便风驰电掣一路领先,村平得意忘形。小许说,我的机车也得技术改造,换原子列车,至少也得像欧洲快车那样。可惜的是,这种型号的国产玩具尚未研制,只好作罢。赛了两天,小许对村平说,总你赢,不玩了。
一天,两人在商场玩具部闲逛,发现新进了一种微缩的小型拳击台,直径也就二十厘米。洁白的拳击台用棕红色麻绒绳圈着,一个肌肉发达身材健美的黑人与一个人高马大一头金发的白人对峙着。一个着白色运动短裤,一个穿红色运动短裤,初时都文质彬彬,一揿按钮,便做出拳击的姿态。两个拳击手分别由两人操纵,操纵者摁动电钮,拳击手就霍地出拳。按钮分两类,由两只手分别控制,一类管出拳速度,一类管位置移动。谁操纵得快,操纵得巧,连续击中对手胸部三次,对手便颓然倒下,连续三次,便判定对手为输。或者,击中对手头部一下,对手便亮起红灯,同时发出“嘀”的一声响,表示被击中要害,如果连续击中对方头部三次,便判定为赢。
两个售货员操纵着己方拳手,你来我往,全神贯注,吸引了不少成人、孩子津津有味地驻足观看。村平一问,二百三十八块,两人二话没说掏钱买了下来。兴冲冲回到家,就在客厅里摆开了阵势。
村平对小许说,这是游戏,你就尽情地出手,往那致命的地方打。
小许笑着说,我本来就不打算怜悯你。
村平说,那好,谁也别怜惜谁,都使出浑身招数。
村平喊,开始!小许咚的一拳就击在村平拳手的头部。村平这方亮起了红灯,同时发出“嘀”的一声响。村平说,你这是偷袭,不算!
小许说,这怎么算偷袭,你都喊开始了嘛,是你自己反应慢。
村平说,好好,我们往后瞧,看谁厉害。
一场拳击恶战就此拉开帷幕。两人全身绷紧,手不停地快速抖动,一会儿小许一方亮起了红灯,一会儿村平一方发出“嘀”的声响。
第一场,村平输了;第二场,小许输了;第三场,又是村平输了。三局两胜,小许扬扬得意。村平不服,非得再来一局。小许说,算了,今天挺累的。不行,村平说,不信我今天打不倒你。小许看村平认真的样子,心里好笑,只好说那就再来一局。
这次村平全神贯注,憋足了劲,两眼死死盯着对方,两手快速抖动,近乎痉挛。村平凶狠地出拳,小许一方频频亮起红灯,很快,直落三局,村平获得完胜。
小许像哄孩子似的拍拍村平,你赢了。
这玩意儿还挺让人较劲的。村平有些窘意。
这倒是一种宣泄的方式,小许说。听说日本人有的在公司里设有一个出气室,里头有各种模型人,可以让员工自由打骂撒气,求得心理平衡。
你不跟你老板也建议一下,设一个出气室?村平说。
用不着,我要是在外面受了委屈,就回来修理他。说着猛地揿动电钮,白人拳手一下出拳击在村平黑人拳手的头部。红灯一亮,接着“嘀”的一声响。
村平说,还不如直接修理我呢。
想得美。小许娇嗔地说。
那我就修理你。村平一下将小许拦腰横抱起来,往卧室便走。
小许钩着村平的脖颈,笑嘻嘻地问,你要怎样修理我呢?
用最残忍的方式。村平咬牙切齿地说。
随后两人又买了飞镖,微型台球桌,激光手枪(带电子靶的),能自动起飞、降落的仿真飞机。
村平和小许就像一对过家家的孩子,在纯粹的游戏中,彼此感受到对方的存在与可爱。
冬天很快就过去了。开春的时候,除了铁轨还横亘在卧室———
客厅———厨房之间外(却早已不通火车了),拳击台、台球桌、飞镖、赛车、激光枪,还有飞机(它已不再能起飞),都散乱地堆放在书房。
村平的律师事务所又开始忙碌,小许的公司新设了一个金融证券部,老板想让小许出任总经理。小许回来告诉村平,村平说,那还用商量?
两人又开始忙乱。常常是村平刚出差回来,小许又飞走了,两人难得在一起吃顿晚饭。即使有时间坐下来,除了各自业务上的事(彼此又不太感兴趣),似乎没有什么更多的可谈,只有看看电视,连最酸最俗的那种肥皂剧竟也能硬着头皮看下去。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眨眼又到了结婚纪念日。这是第六个年头。这次倒是小许显得积极主动,头两天就征求村平的意见,采取什么方式纪念呢?
村平也犯愁。
要不,还是搞一个Party,请郭林、小印他们来?
小许说。
还搞化装舞会?村平突然想起了丽娜。
不,搞一次玩具大奖赛,设家庭团体冠军和个人全能冠军、个人单项冠军三个奖,一定别开生面。小许不禁雀跃道。
村平当然不反对。于是重新把那些玩具找出来,擦洗了一遍。
那只绒线鹅却是怎么也不如先前伶俐乖巧了,好像衰老了许多。
自然,你完全可以想象到,他们的玩具比赛有多么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