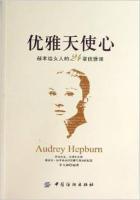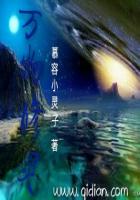按法律规定,刑事拘留不得超过24小时。于子三等人被拘留时间早已超过规定,保安司令竺鸣涛、警察局长沈溥却一再推诿拖延。
学生们行动了起来,他们发出警告:限当局立即无罪释放被抓同学或送交法院审理,否则,将全体罢课以示抗议。
竺可桢找到浙江省府,省主席沈鸿烈却告诉他说,于子三已畏罪自杀。
竺可桢悲愤难当,他责问沈鸿烈:
“于子三有何罪?他为什么要自杀?”沈鸿烈无言以对。竺可桢立即返校召集校医和学生代表一同赶到保安司令部。他们找到保安司令竺鸣涛,质问于子三的死因。
竺鸣涛说:“于子三是用玻璃戳破喉管自杀的。”说着,竺鸣涛找人拿来一块血迹斑驳的玻璃:“讯问时,要他交代策划学生暴动的阴谋,他觉得事情严重,回到牢房没有吃晚饭,在下午6点20分左右自杀身亡。”
竺可桢反驳道:
“你们的说法太离奇了。我了解于子三,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哪有无罪而畏罪的道理?再说,他死在你们看管森严的牢房里,牢房哪来的玻璃?”
竺鸣涛与他的手下面面相觑。竺可桢接着说:“不管于子三死因如何,你们都责任难逃。”这时,已近午夜,夜雾裹着寒气一阵阵袭来,竺可桢由法医陪同前往监狱,查看遗体。
阴森森的牢房里,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于子三仰卧在监狱窄小的木板床上,喉管被割裂,颈上、胸前和床上大片的血迹已变成了黑褐色,一双眼睛大睁着,直瞪瞪地仰望着半空……
见此惨状,竺可桢一阵眩晕。从清晨到深夜,他连续奔走于各部门之间,水米未沾。现在,又亲眼看到自己的学生死于非命,悲痛和愤慨一起撞击着他的心,令他几乎昏厥过去。陪同前往的校医忙给他注射了一针强心剂,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气来。
这时,地方检察官拿出一份早已填写好的“于子三于狱中用玻璃片自杀身亡”的尸检证书,对竺可桢说:“竺校长,现场你也看过了,请签个字吧!”竺可桢瞟了一眼证书上的文字,当即拒绝道:“我只能证明于子三已死,不能证明他是用玻璃片自杀的。”
他在《验尸报告书》上写下了:“在狱身故,到场看过。”
10月30日,于子三被害消息传遍浙大校园,千余名学生冲上街头示威游行。合众社、新华社把这一消息播发到全国各地,笼罩着国统区的白色恐怖首先在杭州被突破。
10月30日夜,杭州宣布戒严。
31日,浙大的教授们集会,竺可桢报告了于子三事件的经过。
学生的无辜惨死激起了教授们的极大愤慨,教授会议发表宣言要求主张公道、保障人权,处理事件责任者。
一向不赞成学生热衷政治的老教授拍案而起:“我就不信我们不能罢教!”当即,大家一致通过罢教一天。这是浙大有史以来教授们唯一的一次罢教。竺可桢又来到了南京,他在司法行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奔走呼号,要求他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
他还向上海《大公报》、《申报》的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对于子三之死,政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要求政府查明事实真相,惩办杀人凶手。他对记者们谈道:这一事件的最后结局,将使人们看到,政府是否真的有诚意依法治国,是否真的愿意保障人权。
竺可桢对记者的谈话在报上发表后,当局十分恼火。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电告蒋介石,说竺可桢有意“煽动学潮”。蒋介石接电后,令教育部长朱家骅要求竺可桢在报纸上发表“更正”,竺可桢毫不犹豫地回答:“报载是事实,我无法更正。”
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面对全国各地此起彼伏的学潮,在向国民党中央的汇报中说,学潮的根源“乃在浙大”,在于浙大竺可桢这个“国内第一流校长,在学潮中持第三者之态度”。
教育部长朱家骅给竺可桢发来密电:“闻浙大近来又开始罢课,实属目无法纪,不容宽贷。学生自治会应解散,为首滋事者应严惩,所以救浙大,亦所以救全国大学。”竺可桢据理力争:“学生如有越轨行为,学校自然可以处理或解散自治会。否则,做事无根据。”他给朱家骅复电道:“尽快复课,电令暂缓执行。”
黑云压城城欲摧。面对巨大的压力,竺可桢对前来看望他的学生说:“……一本过去的理智态度、求是精神,决不以利害得失而放弃是非曲直。”
他在日记里录下了明朝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因反对宦官专权险些遭杀害,而被贬谪途中乘舟又遇飓风时所写的一首诗: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百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竺可桢在日记里录下这首诗后,赞叹王阳明在诗中表现出“何等沉毅的大勇”!
在光明与黑暗的激烈搏斗中,竺可桢同样表现了何等沉毅的大勇!
浙大于子三之死引发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学潮,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最后一次全国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前后持续了近半年的时间。在这场斗争中,竺可桢以一个正直爱国的科学家、教育家的正义感、是非感,出于对学校和学生的责任和爱护,以他对民主、自由的强烈渴望,始终站在斗争的前沿,坚决抵制反动当局对进步学生的迫害。他不顾个人安危,深明大义、追求真理的精神,成为广大师生心目中的一面旗帜。
1948年3月14日,于子三在凤凰山安葬,这是竺可桢校长为学生亲自选择的墓址。
那一天,数千名学生胸佩白花,手持挽联、横幅,在学校广场追悼于子三。广场一片素白,回荡着低沉悲愤的挽歌:我们抬着你的遗体向前走,走在祖国的土地上。仇恨的人们听着记着,今天将烈士埋葬,他日开出民主之花。
4.在风雨如晦的日子里
1948年除夕。这是一个极为黯淡的春节。浙大的教职工生活艰窘,无以为继。他们纷纷来找竺可桢,向学校借钱度日。夫人陈汲也对竺可桢诉说,家中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竺可桢苦笑着和夫人打趣:“人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回,看你这个巧妇怎么办?”大年夜,他们全家吃的是霉米饭。
只有天真的孩子不知道发愁,院子里不时传来松松、彬彬和宁宁清亮的笑声。听着孩子们的笑闹声,竺可桢回想起自己的儿时。在故乡绍兴,从腊月二十六祭祖祝福,就开始过年了。孩子们换上了新衣新鞋,天不亮就起来放鞭炮、吃年糕,那是过去的岁月里最快乐的记忆。而如今,面对三三两两脸色青黄前来拜年的教职员工,竺可桢和他们谈起时局,大家只有相对叹息。
这时的国民政府,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军事危机和经济危机。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钞票面额最大已达百万。抗战前一石米六七元,如今已涨到五六万元。全国各地都有饥民抢米的风潮发生。号称“天堂”的杭州,市面上商品奇缺,各种食品被抢购一空,大街上不时有抢劫事件发生。
竺可桢多次主持校务会议,研究学校捉襟见肘的经费开支和师生员工的生活问题。一心想抓科研、抓教学的竺可桢不得不面对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他叹息道:校务会议讨论柴米油盐,恐怕中外教育史也没有先例。
1948年的紧急校务会议决定,分别派人到杭州周围的萧山、兰溪、富阳等地去购买一批黑市米、高价食油和木柴,以备不虞之需。
为人诚厚、认真的数学系著名教授苏步青,连日奔波在富阳乡下的集市,为浙江大学购回了130担劈柴。
国民党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败局,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高压政策和法西斯专制。
1948年6月,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论,社论的题目为《操刀一割》。
文中指责浙江大学是京、沪、杭的学潮中心,认为当局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加以解决,“与其养痈遗患,不如操刀一割”。
这篇社论其实是一个信号,表明反动当局已经对浙大、对竺可桢十分不满,准备动手了。
1948年8月21日后半夜,浙大校园一片静寂。睡梦中的竺可桢朦朦胧胧听见几声哨音。
清晨,校警和学生代表来向他报告:凌晨4点左右,200多名军警分乘5辆卡车闯进了浙大校园。他们封锁了所有通往学生宿舍的路口,在一些身穿风雨衣、用雨衣帽子遮挡脸面的特务学生的带领下,抓捕了吴大信等三名学生。
竺可桢立即动员一切力量组织营救,除吴大信外,另两位学生获得保释。
这件事发生过后不久,一份教育部的密件摆到了竺可桢的案头。
这是一份关于浙江大学及竺可桢的情报:
“自8月22日特刑庭拘捕吴大信后……竺可桢甚至包容奸伪匪谍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问不闻,而对于特刑庭之传讯则加以拒绝。
“……无怪社会人士称浙大为共匪之租界。“综上各情,浙大当局包容匪谍学生之非法活动,实责不容辞。”
这份情报直指竺可桢,内容咄咄逼人。而教育部却将它送给被检举人竺可桢,用心更是十分阴险。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结束,全歼国民党军47万余人。
国民党的全面崩溃开始了。
在急转直下的政治形势面前,每个人都在考虑和选择自己的出路。
1948年11月13日,蒋介石的心腹谋士、侍从室二处主任、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布雷因痛感“时局艰难”、“前途无望”,服安眠药自尽。
竺可桢在杭州九溪参加了陈布雷的葬礼。
陈布雷与竺可桢是同乡,也是绍兴人。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上海办《天铎报》、《商报》宣传民主革命,名噪一时,被称为“如椽大笔,横扫千军”。但自从他跟随蒋介石后,正派的文人品格与“士为知己者死”的效忠思想始终使他处于矛盾痛苦中,最后走上了“自绝人寰”
的道路。
竺可桢由陈布雷力荐而被任命为浙大校长,他出任校长一职后,与朝气蓬勃、富于革命精神的青年学生朝夕相处,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最后追求民主、进步,走上了与陈布雷截然相反的道路。
1948年12月,南京政府指示各大学准备“应变”迁移。
浙江大学在全校教职工中进行了调查,96%的教职工反对迁校。12年前,为了抗战,全校师生不畏艰难,四迁校址。如今,全校师生团结一致,反对南迁。
有人告诉竺可桢,国民党特务手中有两份黑名单,一份是“反动分子”名单,一份是所谓“和平分子”名单,竺可桢的名字列在后一名单中,他已被国民党列入“另册”。
1949年元旦,竺可桢收到了“中国共产党杭州工作委员会”的新年贺信,贺信中希望他坚持工作,保卫人民财产,参加新中国建设。
在这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竺可桢下决心留在学校等待大变革的到来。
决心下定,心情反而平静了。
竺可桢每天除了公务之外,把时间都用在读书和研究学问上。他查阅资料,讲演《地缘政治学与世界霸权》;他拟写《18世纪末中国之人口压力及马尔萨斯所倡之学说》,在研究这一问题时,他还把清代学者洪亮吉有关人口问题的论述《意言·治平》译成英文。
4月28日,当时的教育部长杭立武从上海来电,要竺可桢“尽快莅沪”,并称“教授愿离校,到沪后可设法”。接着,催促的电报又接踵而至:“有要事相商,速来沪。”
竺可桢到了上海,果然不出所料,杭立武是要他尽快去台湾或广州,竺可桢当即拒绝。他托回杭州的人转告夫人陈汲,他决不去台湾或广州,请她放心。
竺可桢留在了上海,他避开了一切耳目,住在朋友家中。偶尔,他打开报纸,只见报纸上赫然登着:“竺可桢已飞往台北。”他笑了一笑,把报纸扔在了一边。
一天,竺可桢外出,遇到了正四处找他的蒋经国。
蒋经国对竺可桢说:“家父从舟山派我来上海,就是专诚迎接先生去台湾。”
竺可桢婉拒道:“经国先生,历史兴替,大势已去,台湾能维持多久?”
竺可桢还劝蒋经国说:“依我看,您也不必去台湾了。”
蒋经国没想到竺可桢会是这种态度,悻悻地说:“人各有志。”
两人不欢而散。
5月25日,上海解放了。
清晨,竺可桢走上街头。淡淡的晨光下,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席地而坐,纪律严明。
他兴奋地来到闹市区,只见沿途人山人海,欢迎解放军的群众排成了人墙。人们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女学生把鲜花插上了解放军的衣襟。
5月27日,上海解放的第三天,竺可桢在日记中写道:
“当年国民党自广州出师北伐,人民也像今日一样欢腾。但国民党自己不振作,包庇贪污,赏罚不明,才造成今日的倾覆。
“解放军之来,人民如久旱之望云霓,希望能苦干到底,不要如国民党之腐化。科学对于建设极为重要,希望共产党能重视之。”
竺可桢怀着欣喜和希望,还带有几分陌生和迷惘,迎来了新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