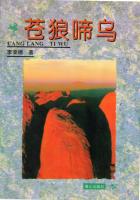从混沌的睡梦中醒来时,时间已经是半上午了,天还没有完全亮开,还像清晨五六点钟的光景。原来又是个雨天,在昨夜满月温柔恬静地升起的地方,是一片灰蒙蒙的云雨。
天气预报说西伯利亚的寒潮来了,但起床时并不见得冷,从窗缝中挤进来的风竟有了春风扑面的感觉。看桌上的日历,原来立春都好几天了。
春夏秋冬就这样一季季一年年地在窗前流转,那窗口凉幽幽的感觉叫师姐心潮翻涌。师姐记得去年立誓把自己嫁掉的时候,也是在立春前后,师姐在窗口端望,但仔细一想,却已是前年的事儿了。窗前那株光秃秃的黄桷树,又萌发出了一树星星点点的绿。
对面青年教师公寓楼顶上的鸽群,呼啦啦地起飞,以固定的半径绕着楼群盘旋几圈再飞回来。因为两栋楼离得近,每次起飞时那惊天动地的阵势,像是要把屋顶掀翻似的,闹得师姐心里也好一阵扑腾。
师姐有些害怕春天,什么都苏醒了,包括她的身体。
门窗严严实实地关了一个冬天,世界就是映在窗前的一幅画,灯红酒绿的却声息全无,像无声电影,师姐也就心安理得地坐在电脑前。一开春,外面的世界就轰隆隆地由远及近地开过来,那画面也就活过来了,就是立体的有声电影了,师姐也就有些坐不住了。
师姐心里空落落的,起身去超市买了点零食。其实并不想吃,又总感到有些空虚,想有一个什么东西来填满这种空虚。师姐买完瓜子回来,对着瓜子发呆,剪刀横在半空又住了手,就是剪开了也没有想吃的欲望,瓜子显然是搔不到痒处的。
那天师姐很寂寞,寂寞的师姐想出点儿什么事。寂寞像一瓶烈酒,师姐被灼烧得心下难耐。其实只要忍那么一会儿就没事了,可师姐那会儿特任性,她不想忍,她想发疯。
一个人患重感冒的时候,普通的感冒药是止不住的,就像零食完全止不住她的寂寞,对她完全失效。总之,她要发疯,没有理由。
可是,跟谁去发疯呢?室友阿美在被窝里跟老公打电话,师姐不知道该给谁打电话,师姐不想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也是一个寂寞得要命的人,现在一心盼望着她找对象结婚。母亲以前只担心女儿早恋,没想到她自己一阵折腾后,竟然在三十岁的门槛上还落单了,母亲心里那个急啊!
马导说师姐适合做学问,做学问的人就是要耐得住寂寞。马导近年来的一系列与寂寞厮守抗争的动作给日益浮躁的学术界带来了不小的震动。
马导资格老,做了好多年的学术带头人,本该是志得意满。不料在年届退休之际,突然来了个大动作,从热闹花哨、频繁变脸的小说领域转向一向沉寂的诗歌研究这块不毛之地,有心坐冷板凳,想安安心心地做几年学问。
这十年来,马导忙于开学术会议,当大奖赛的评委,出席新书发布会、小说研讨会,成了地地道道的“学霸”。可扪心自问,自己的学术水平似乎还停留在十年前,还吃着前几十年的老本,这是当他的弟子们在“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旗帜下发出自己的声音时,马导才逐渐意识到的问题。
看来不仅爱情要时时更新,这做学问更是吃不得老本,需要像恋爱那样,全身心地投入,需要勤于思考的头脑。
创见是做学问的根本,来不得半点虚假。
马导辛苦了大半辈子打下的江山也还不够他十年的休养生息,临到退休了,还得跟年轻人一样,从头开始。
当然,他也可以混日子,反正都快退休了,但马导生性刚硬,如残兵败将般谢幕,那不是他的性格。
对马导的这一转向,反对的居多,尤其是他的弟子们,为导师的身体着想,认为是吃力不讨好。
马导表态说,他弄诗歌走的是旁门左道,抱着玩玩的心态,不是非要另立个山头。在他看来,诗歌是去除一切浮文之后的最纯粹的文学形式,马导退休在即时转向诗歌,也就有点叶落归根之感,他早年本就是诗人出身。
转向后的马导门下的招生从爆热到爆冷,从门庭若市到门可罗雀,有一年竟然是靠调配才招满了名额,都知道诗歌专业的毕业生出去除了教书,就只能喝西北风了。
一想到马导对她耐得住寂寞的信任,师姐决定去图书馆。
刚开学,学校人气不旺,宿舍还相对冷清。灯光雪亮的教室,那一排排座位却空荡荡的,只零星地坐了三两个人,还主要是一个假期没见的一对对相互缠绕的恋人,全没有放假前的那种紧张和忙碌,篮球场上也没有往日的人声鼎沸,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练习投篮。
在桥头,师姐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给他们开过文艺心理学的罗教授,近几年在学术界发展势头强劲的青年才俊,据诗人从他们廖导那里得来的小道消息,因才华着实超群,一路破格晋升职称的罗教授也是文学院院长的热门人选。
罗教授正在指挥男男女女的一路人马搬家。师姐放慢了脚步,犹豫着是绕道走开还是前去打招呼甚至搭个帮手。师姐在搬家队伍中还看到了好几个熟悉的身影,其中就有她的大师兄。
马导最看不起罗教授。前天在有几十人参加的马导生日宴上,马导以祖师爷的身份指名道姓地公开讨伐说:“罗教授这个人写出来的文章倒是蛮漂亮,就是做人太差,心眼比针尖还细,这样的人怎么做学问呢?我给我每一届的学生的第一句话就是——做学问先得学会做人。”
满屋的人都频频颔首,表示赞同。坐在马导身边的大师兄补充说,罗教授做事就是心细,罗教授是博士班的班主任,有一次他们几个班干部和罗教授一起去吃饭,请他点了菜,服务员通知菜上齐后,罗教授不放心,对着菜单一份一份地检查有没有上漏的菜,埋单时又亲自拿自带的计算器重算了两遍。
大家哄堂大笑。
在学校出版社工作的辣妹也为马导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最新佐证。前年学校在校外大规模修了几处集资房,根据学校的政策,申请了集资房就得退出以前分的老房子。大多数老教授因为舍不得退出在老校区内环境幽雅的老房子,放弃了集资房。而新来的年轻人因为很少有住教授楼的,老房子的条件不好,几乎都申请了带小区的集资房。罗教授是学校破格引进的人才,不到四十岁,一来就在以前的院长楼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老房子,和马导的房子一样大了。马导可是在学校工作了三十多年啊,这么一个年少轻狂的后生跟自己一个级别,马导对学校的人才待遇政策很是不满。
罗教授对院长楼以及绿树环绕的周边环境很满意,但感觉唯一的欠缺就是没有电梯。罗教授是从农村出来的,家里就他一个儿子,老父老母得跟着他。好在他们长期在农村劳动锻炼,腿脚都还利索。罗教授把十万块钱的安家费全都用来搞装修了,打算长住。谁知道还没住满三年,学校就开始集资建房了。是否申请集资房,他犹豫了很久,他当然舍不得退出现在这个花了十万装修费的住房,虽说住了三年,因维护得好,墙壁四周洁净如新,还像刚装修出来的一样。有一次他儿子不小心把墨水弄到墙壁上去了,他还狠狠地把儿子揍了一顿,那是儿子长这么大第一次挨他的揍。
可是母亲帮他做出了决定,母亲突发脑溢血住院,住院出来就半瘫了,没有电梯的老房子对母亲进出门和看病都极不方便。没办法,他只有忍痛申请了集资房。搬家前夕,罗教授在屋里转了几转,想不出什么可以减少他装修损失的办法。不能白白便宜那没花一分钱没出一份力的新来者呀!他当初装修时为了尽量节约成本,跑了全城的装修市场,买的几乎是全市最低价,几番轮回地讨价还价,跟装修工人吵了多少架,怄了多少气,付出了多少心血啊。罗教授为这个事情寝食不安,他决定去房管科找分到他这个房子的新房主,商量一下给他装修补偿的问题。他刚找到新房主的电话,还没来得及去找人,对方就主动找上门来了,是后勤集团的一个中年妇女,说要来看看房子,准备装修。
进门一看,中年妇女喜形于色:“装修得这么漂亮啊!”
罗教授马上补充说:“才装修三年呢!”
中年妇女高兴地说:“装修得这么好,搬进来直接住就是了,太省事了!”
罗教授说:“我正想找你商量这个事,你看这么办吧,装修这些东西又搬不走,直接花在装修上的钱就有六七万,你补偿我一万五,怎么样?
中年妇女一听眼睛瞪大了:“什么?我在学校待了二十几年,还从来没听说过哪家要补偿装修费的,又不是我让你装的!”
“再不一万?”
中年妇女摇头。
“再不五千?”
“你别说了,我是一分钱都不出,你把你的装修搬走得了。”中年妇女是后勤部的工人,没什么文化,嗓门也大。
罗教授急了,说:“你讲点道理行不?你实在不愿意,我搬不走,把它打烂也不留给你。”
中年妇女说:“请便!”说完扭头就走。
事后中年妇女有些后悔,怕罗教授真把装修给砸烂了,过了两天又来看房子,打算适当给罗教授一点补偿,没想到已经晚了,木地板已经被撬得稀烂,墙上连开关都是拔掉了的,只剩下了一些散乱的线头,中年妇女气得脸色铁青,找到学校和中文系领导告状,说一个教授竟然做得出来这么下作的事情,告罗教授损毁公房,闹得满城风雨的。
马导兴奋地问辣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没听说?”
辣妹说:“就这几天啊,我们出版社有那么多学校领导夫人,每个人叙述的版本都不一样,但基本事实可以认定,我这个版本是综合各家说法的。”
师姐在路上碰上罗教授搬家,可见辣妹讲的笑话不是没影的事情。师姐正想绕道走,搬家队伍中的憨豆发现了她,朝她挥手,她只有硬着头皮上前。
大师兄看到她,有些尴尬,嘟哝说:“我也是路过,顺便搭个手。”
憨豆揭穿他道:“大师兄别谦虚了,我们这些人都是大师兄前几天就约好来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