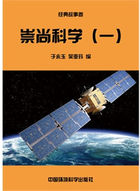六、九十九溪畔的那些事儿
A
公元1436年,大明正统元年,九十九溪。
“咿咿呀呀……”年轻的蔡山坐在穿梭于丛丛水草的木船上,静静地看着艄公手摇大撸,在碧绿的九十九溪上划出一条条水纹,将一个又一个石拱桥的桥洞抛在身后。
船行渐缓,再往远处细看,往来船只如织,熙熙攘攘,还有一望无垠的棉田和甘蔗林。突然,摆渡的艄公高声道:“凤池到了!”
“这就是凤池啊,大富豪李五的凤池?”蔡山睁大眼,四下张望,一脸茫然。
艄公抬起头,啧啧赞道:“可不是?富不过李五!单这一份热闹便非别地可比!”
望着船来船往的渡头,蔡山也是感叹连连:“没错,听说这里是晋江北岸最富庶的小镇,繁华了几个世纪的安海码头也没有这么多船只。”
“这怨不得安海码头,是大明王朝的一纸禁海令给废了的。”艄公倚靠着船栏,极目远眺,长声叹气。艄公说,他祖上是跑船的,咸涩的海风已浸透讨海人的生活,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地都曾留下先辈们的足迹;而今,换了朝代,那片深深的海洋成了久远的记忆,很多讨海人只能像他一样,在江河上当个摆渡的船夫。
艄公口中的“大明王朝”这个词,像一枚倔强的钉子,生生敲入蔡山的心。蔡山莫名地惆怅起来,幽幽地说:“如果不是生活在大明,我们的日子或许好过些。你看,我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今天不得不来投奔凤池的远房亲戚。”
“我也听说今年一些地方庄稼收成不好,官府赋税、徭役却样样少不了,很多村民都跑路了!莫非你是来自那个闹饥荒的思母山?”艄公不愧是摆渡的,消息灵通,嘴也快,一下子猜穿了蔡山的心思。
说话间,船已靠拢码头。小船所泊靠处,是在桅头尾渡头的边角上,因为渡头正中泊着李五的船队。上了岸,蔡山东张西望,被眼前繁华热闹的景象深深吸引:水面上小舢板往来如梭,岸边也泊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人来人往、上上下下忙着装货、卸货;岸上更加热闹,小摊、货仓一排排密密麻麻、挤挤挨挨,更有无数各样打扮的人穿梭其间,讨价还价,嘈杂热闹非凡。
蔡山费劲地挤在人群中,缓慢地蠕动,显得有些兴奋,心想:“我是李五妻子吴氏的远房亲戚,那里总会有活让我干,不致挨饿的。”在一个小摊前,蔡山停下脚步,怯生生地问摊主:“请问五爷的家往哪走?”摊主看了蔡山一眼,露出神秘一笑,指了北边的一片甘蔗林,说:“李五的九落大厝谁不知道?甘蔗林的南边就是了!”
走在凤池的田间小道,空气里飘浮着淡淡的蔗香。蔡山不知不觉间放慢了匆忙的脚步,闭上眼睛,贪婪地呼吸这醉人的香气。他睁开眼,一片翠绿的甘蔗园映入眼帘:山坡上,田地里,九十九溪畔,一丛丛甘蔗如骄傲的士兵,威风凛凛。秋风一刮,甘蔗尾梢随风摆动,发出“哗哗”的声响,似是士兵凯旋的喝彩声。
在甘蔗园的附近,散布着一间又一间圆锥形的“蔗寮”,也就是榨糖作坊。好奇的蔡山钻进“蔗寮”一瞧,一匹黄牛正在拉着石辘,两块圆柱形的石绞随之缓缓转动,旁边一个老师傅则取几根甘蔗放在两块石绞之间,瞬间汁水四溢,糖浆汩汩流出。蔡山伸出手指,戳了一下糖浆,放在嘴边舔了舔,喊道:“甜,真甜!”见有来者,工人急急起身,忙不迭地说:“当然甜啦,周边的六七个‘蔗寮’都是五爷李五的,生产的正是远销京城的‘凤池糖’。请问您是来买‘凤池糖’的吗?”蔡山不紧不慢地答道:“我是五爷二太太的远房亲戚,这次来到凤池是想走亲戚的,请问李五的家在哪?”老师傅走到马路中央,指着不远处一幢幢错落有致的村民小院说:“你一直向前走,然后向右拐,可以看到一座很大很大的房子,门前挂着两串大红灯笼,那就是五爷的九落大厝。”
顺着老师傅指的方向,走在往李五家的路上,感受着迎面拂来的风,蔡山欢快地哼着小曲。“咔嚓、咔嚓——”路过一户人家,房内突然传来一串奇怪的声响,蔡山透过虚掩的门扉,朝里瞅了好一阵,窥探着这个神秘的院子。他瞥见一个中年妇女盘腿而坐,左手捏着棉条,右手握着手摇柄,她轻轻一摇,棉条里徐徐“吐”出一条棉线,又细又直,源源不断地缠绕在一根光滑的黑色转子上。“咦?你这是找谁?”一个过路的行人看到蔡山贴在门边上窥探院子,大惑不解。蔡山这才说明来意。路人听罢哈哈大笑,说:“这户人家在织布,发出‘咔嚓、咔嚓’声响的是布机声,你是外乡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几乎每个妇女都在种棉花、纺纱、织布。难道你没听说过‘凤池换纱笼’的俗语?这话说的是我们这里纺织业兴旺的意思。”“这么说这些纺织品是农户个人的,不是李五的?”经路人一提醒,蔡山似乎明白了什么。“怎么说呢?是李五聘请北方的师傅来家乡教妇女纺纱织布和制作绸缎,教男人弹棉花、染布,现在人们织成的布,小部分留着自己使用,剩余的都卖给李五。”面对蔡山的穷追不舍,热情的路人有问必答。
路人所言非虚,蔡山又路过几户人家,满屋满院响起的都是“咔嚓、咔嚓”的布机声和“嗡嗡”的纺车声。拐进一条悠长的小巷,布机声和纺车声戛然而止,李五的九落大厝如画卷般在蔡山面前铺展开来。
这一年,25岁的蔡山,逃避官府的赋役,从位于晋江县西部的思母山下来到凤池,投奔远房亲戚李五,慈善的李五收留了他,蔡山成了凤池糖厂的一名仓库管理员;这一年,51岁的李五,南糖北棉往返贩卖,富甲闽南,“富得像李五”成为一句流行语;这一年,晋江北岸的凤池一片繁忙景象,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和棉田,到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凤池糖和棉布成为九十九溪畔最时髦的货物。
B
公元1445年,大明正统十年,晋江县六里陂。
一场迟来的冬雨,使凤池小镇笼罩在水雾之中。蔡山草草吃了几口早饭,操起铁镐,顶着逼人的寒气钻进濛濛的雨幕之中。雨中的田间羊肠小道,高高低低,崎岖坎坷,泥泞难行。尽管深一脚浅一脚地迈上小山岗,但是蔡山没有怨言,一门心思以最快的速度赶往六里陂抢修堤坝。
走进六里坡的工地,耳边充斥着吆喝声、呼喊声和哗哗的流水声,蔡山感受到了一股紧张、凝重的气息。铲土的,装筐的,挑担的,每个人只是一个劲地忙碌着,尽管有些手忙脚乱,甚至有些手足无措,但大家还是想尽办法、用尽力气,用最原始的方法加固堤坝。看到这一幕,蔡山满意地点点头,心中突然涌出一股莫名的感动,鼻子有点发酸,暗想:“这些农民兄弟真卖力,五爷让我过来监工,显然是多余的。”
一阵瑟瑟冷风夹着细雨扑面而来,蔡山猝不及防,一个趔趄差点被刮倒。他裹紧了蓑衣,隐没在人流里,挥起手中的铁镐,铆足了劲,刨向梆硬的泥土。尽管经过大雨的冲刷,但表层土之下的泥土却如石头一般坚硬。往往一镐刨下去,蔡山的虎口就震得有些发痛,但梆硬的土层只是裂开一点点土,用力刨几下才能刨出一块块硬邦邦的土块。
“这下雨天,蔡掌柜怎么也来修沟渠?”一个年轻的工人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认出了蔡山的身影,他分明知道蔡山是大富豪李五几个糖厂中的一个掌柜。“闲着也是闲着,就顺便过来了。”蔡山轻描淡写地说。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场面,年轻工人说:“五爷是个大好人,这次出资为百姓修建六里陂,以后晋东平原一带的庄稼再也不怕旱涝。要知道六里陂规模大,是晋江境内一半农田赖以灌溉的水源。五爷可花了不少钱呀!”蔡山点了点头,忽然沉默了下来,像是回忆起一些往事,脸上也露出几分温和之色。他知道脚下这片土地叫六里陂,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坡,也不止六里,而是一条长达40多里的河渠。雨季的时候六里陂堤坝时常崩塌,怒潮排山倒海,狂澜倒灌,晋江县凤池、陈埭、青阳、罗山一带的无数良田沦为沧海,待到潮退水落,留下一片茫茫荒野。慈悲的李五多次接济百姓,疏财修陂。他知道,十年来,自己因为投奔了赏识自己的远房亲戚李五,人生路越走越顺,无论是娶亲生子,还是从仓管到制糖师傅,再到掌柜,他一直很低调地做事,也颇受李五的器重。
公元1446年秋天,蔡山漫步在晋东平原,穿田而过的六里陂传来哗哗的流水声,远远望去,沟渠满了,池塘溢了,水田盈野,稻香鱼跃,蛙鸣一片。一阵风吹来,他闻到田地里飘来一股稻谷熟透的香味,他蹲下身子,拾起一粒稻谷,用牙一嚼,满嘴稻香,露出满脸的笑容,喃喃自语:“六里陂修好了,旱涝保收,农民丰衣足食,晋江‘鱼水之乡’的美称也就名不虚传,五爷一定会开心的!”
C
公元1447年,大明正统十二年,晋江县凤池九落大厝。
“行行好,给我一点吃的东西吧。”清晨,李五的九落大厝大门外排起了长龙,嘈杂的说话声不绝于耳。一群衣着褴褛的饥民,长跪不起,轻叩房门。
“五爷,我们那里灾荒,颗粒无收,请你行行好——”一个饥民用沙哑的声音诉说着自己的痛苦。
“求求你了,我实在太饿了。”饥民的声音此时变得更加凄厉。
大门忽然敞开,走出一位身着棉衣的老者,只听他说道:“每人一袋大米,人人都有份——”这群头发凌乱不堪的饥民这才反应过来,泪流满面地不停给老者磕头:“谢谢五爷的大恩大德!”
这个老者喊来蔡山,让他领着饥民们到粮仓领取大米,一时间,闻讯赶来的灾民达几百人之众。望着老者瘦弱的肩膀及蹒跚远去的背影,蔡山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不由落下泪来。他心想:“五爷老了,今年都62岁了,可他那颗仁爱的心永不老。两年前,五爷捐资修建六里陂;一年前,刚刚在泉州东岳庙捐米一百五十石赈济饥民;上个月,运送大批粮食救济浙江鄞县的饥民;今天,他又开仓布施,救济灾民。”
第一次踏上凤池这片富饶的土地,落魄的蔡山也是一名饥民,所以他特能理解百姓的疾苦。李五也懂这些,比蔡山更透彻。几天前,李五在闲聊中给蔡山算了一笔账:明朝初年,晋江县户数为18079户,人口67407人,每人每年要负担60斤粮食、7.4两白银、200斤食盐。那天,平日里寡言少语、略显木讷的李五打开了话匣子,一口气说了很多,有一句话让蔡山印象很深。他说:“一遇到灾荒,百姓没饭吃,而官府的仓库却积满粮食,宁可腐烂,也不开仓放粮,布施天下。农民缴纳不起官府的赋税、徭役,只好弃家逃亡。但是谁逃走了,村里其他人仍要为他担负赋役,因而逃亡的人越来越多。真命苦的老百姓,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他们活活被饿死?”
送走最后一批灾民,看看时间已经接近中午时分,蔡山顾不上吃午饭就出门收账。途经罗裳山下的画马石,他看到二十八都的里长林良吉与七八个村民正拿着刻刀在画马石旁的一块大石头上刻字。这一幕,让路过此地的蔡山看不下去,心里直嘀咕:“二十八都不是在闹灾荒吗,里长怎么大白天净干些不着边际的事,在这里弄崖刻,记什么功名?”纳闷之余,蔡山走近一看,原来里长和村民们不是记功名,而是在控诉明朝的苛政。但见青灰的石头上,赫然刻着鲜红的血字,让人触目惊心:“盖是都第二图无征秋米五十石,致累里甲贫窜。正统丙寅,予膺里长,值年荒,先贷完纳,俟岁稔资甲助偿,人犹患焉,况取之无制乎……”“哎——”蔡山皱了皱眉,长长叹息了一声。里长林良吉一抬眼,见来人是李五的掌柜蔡山,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自己的遭遇。林良吉拉着蔡山的手,抹着泪说:“是这样子的,我是二十八都的里长,今年是个荒年,交不上税的百姓弃家流亡,我替他们缴纳赋税,等到村里日后偿还,可是官府需索无期,何时才能补上这笔欠账呢?当朝者没良心,不积德,该断子绝孙了……”林良吉的一番话,让蔡山忍不住潸然泪下。蔡山愣在那里,没有吭声,陷入思考,他联想到大清早一批灾民挤在李五家门口和几天前李五说的那一番话,不停地在心里暗骂当朝者:“官府的压迫让百姓无可奈何,这日子要怎么过?”
这一年,人近中年的蔡山,时常与年老的李五到村中古庙上香,他们多次在佛前祈愿:什么时候,晋江大地年年风调雨顺,不再有灾荒,人人都能过上温饱的日子;什么时候,老百姓不再背负沉重的赋役,要知道,他们被这无休无止的徭役拖得耕作不时,农桑废业,穷困潦倒;什么时候,严酷禁海的硝烟可以散去,讨海人家回归海洋,民间航海和自由贸易重新焕发生机,安海码头再现“市井十洲人”的景象……
七、一个私渡客的赴台历险记
A
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晋江县东石石蛇尾码头。
天还没亮,鸡啼几声,一宿没合眼的蔡温友,看了看身边熟睡的三个儿子,又看了看在房间给他整理行囊的爱妻曾氏,不禁悲从中来,别过头,久久不发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