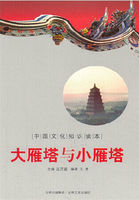才进图书馆门,赫然看见一个东方人。他们同时问对方:“你是中国人吗?”那时,当地华人极少,看见东方面孔很亲切。交谈之下,建平知道他叫邓锦生,66届高中毕业,原是奉贤知青,算是“脚碰脚”,同类人。
“你怎么会到这里念书?”
“叔叔住在附近,要我到这里念书。”
“打算学什么?”
“电脑。”
“电脑是新学科。你怎么想到的?”
“叔叔说的。他还说,现在电脑行业香。它不需要多少中学知识,离开学校久了,书忘了,不要紧。很多原来学中文、英文、营养,甚至政治、音乐的各式各样行业的都改行学电脑,很多都出了头。”
“你叔叔在哪里做事?”
“BBL实验室。”
建平听了,心想,我舅舅和你叔叔同一个工作单位,同一个思路,看来电脑真的不需要多少中学数理化,倒不是书呆子们自己书念得好,以为鸭子企鹅都应读电脑一试。
书念了也就念了,只是很辛苦。大专水平社区大学一般只要念两年,而今已三年半,建平尚差七个学分,利用暑期三个月修课补上,总算也可以毕业了。
建平想,学位快有了,尽管只是大专的,两万美元,合十万,就是一百个千的人民币,也有了,还是见好就收,回上海去吧。原来和珊珊说好的,两年,存够钱就回去,现在已经四年了。总不见得再用四年去读完大学本科,就算我愿意,珊珊也不会愿意啊。女人经不起“等”!
但事情发展比想的还顺利。珊珊来了信,说她来美签证批出来了。
在离开上海前,建平找朋友算过命。那时年轻人很风行这套,好玩,不收钱的。那位朋友说,照面相看,他初到美国会比较辛苦,34岁后,转走眼睛运,学业、婚姻会有很大起色,叫他好好把握!
可不是让“算命先生”说中了!
珊珊的申请被美领馆拒绝过好多次了。一般说,被拒绝过一次,没有新的理由,是不会被批准的。这次,珊珊把他们三年多时间里往返的情书用七根黄丝带结成大大一捆,交进美领馆,说了黄丝带是她未婚夫寄来的,也许因此感动了承办和审批的人。
建平把珊珊从机场接回“家”。那时他已独立另租居处。房东是印尼华人,将一栋三卧室“分层”式的房子,分租给三个学生,建平是其中一个。建平没租单卧独门独户的公寓,无非是为了节省开支。
从第二天开始,建平就驾车陪珊珊游览了纽约一些景点像自由女神像、世贸中心、联合国大厦等,也去看了尼亚瓜拉大瀑布。他在高速公路上,把车开到时速85英里,让她感受飙车的乐趣。秀给她看,车有巡航系统,放开手脚车能自行按设定速度前进。接着又陪她参观了他所念的大学、他打工的饭店,并让她在那里做了两个小时工,当作体验生活。让珊珊看看美国,看看他在美国的生活。
他舅舅请了建平和珊珊在自己家里吃了龙虾大餐,红的龙虾、金黄的玉米,颜色好。用了吃龙虾的工具:钳子和钩子。这一切都很普通,只是表示诚意,想当时大陆出来的人,因为没见过,会喜欢。
珊珊来美的第七天是星期天。周末饭店生意红火,打完工,已很晚了,建平拎了她喜欢的“蜜汁火腿”回家,希望今晚能和珊珊商定一个结婚的日子。但在走到他自己房间门口时,他傻住了。只见房门开着,电灯亮着,里面没有人,但床上、桌子上、椅子上、地上到处都是东西,像被抄了家一样。眼光扫到枕头上有一封信,赶快拿起来读。
“两万美元是过去式。大学本科毕业,有绿卡,是我现在要的。我够狠,够美,有信心能得到。女人总得为自己多打算一点。原谅我不辞而别。不要找我!”
读完信,建平觉得背后好像有人,原来是邻室同学知道事情不太对劲,特地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帮忙的。他轻轻地慢慢地告诉建平,怕刺激他,你女朋友,呃,珊珊下午被一个戴眼镜的男的接走了。
34岁,你走眼睛运!
建平迷失了。好,你狠!来美后,为了你,我在这花花世界,不近女色。现在你找了你的,我为什么不找我的?两个月不到,就和一位在纽约打工做侍应生的同行谈婚论嫁,女方家长请他吃饭。他们住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老楼里。楼梯上有痰痕,进门前就不爽。开始用餐,主人拿出一瓶啤酒,三个人分。建平见杯底那么一点点酒,心想这哪里是喝酒,就是以前在崇明当知青,穷成那样,啤酒也不是这样喝法。
他猛然想到他并不爱她,但图她是美国公民,结婚后,可解决他的绿卡问题。他谴责自己是“不要脸吃软饭的变种”。
认清了自己,他想起邓锦生。66届的邓是国内真正读完高中课程的,早就毕业,转去了四年制新州的M州立大学。向邓借到了他在M大的全部笔记讲义和平时测验或期中期末考试题,并再三落实了在M大,哪些教授给分松,哪些喜欢“当”学生。心想,他妈的,老子大不了再四年,总可弄到M大大学本科文凭。凭文凭找工作,搞绿卡。何必正路不走,走邪路,说不定哪天碰上鬼,永世不得翻身。
珊珊离他去了。多少辛苦挣来为支持和她共同生活的钱,好像也不再有意义了。他不打工了,愿把全部积蓄贴进去,早日拿下M大的大学本科文凭。
“个人奋斗”的意志和决心可激发出无比的能量!和大家一样,他两年就修满全部学分毕业了。在最后一个学期,公司派人来学校招人。他认清自己喜欢和“人”打交道,成绩不是很高,适合做电脑“销售”方面的工作,不适合做技术含金量较高的“开发研究”工作。明确了自己的长处,他成功地把自己推销了出去。一家电脑公司聘用了他,也答应给他办绿卡。
在毕业典礼那天,他舅舅参加了。正式的毕业典礼结束后,学生和他们的情人、家长、亲戚朋友一起散在校园各处拍照,以留下莘莘学子人生道路上这美丽重要的一刻。
其中之一的他,陈建平,36岁,身边没有女人,账户上没有钱,穿着学士袍,带着学士帽,有一丝兴奋,一丝颓伤。舅舅同他说,你现在有大学本科文凭,有身份,有年薪两万的工作,是钻石王老五,去登个征婚广告,恐怕上海美女会像云一般涌来,任你挑啊!
话音才落,珊珊从树后走到建平前面,说:“我应征。这两年我先在车衣厂打工,然后在牙科诊所做帮手,就等你这一天。”“你够狠!”“我心地够……”“美”字还来不及出口,已给建平吻住。
作为长者的舅舅,为这来之不易的一幕,眼泪盈眶,背过身子,走开几步,好让小两口亲热得放肆点。
然而身后的他们松开了。建平两手按着珊珊双肩,眼睛对着她眼睛,问:“你离开那天,把你接走那个戴眼镜的男的是谁?”
珊珊举手伸出食指刮刮他的脸说:“男人都是小气的。那是你舅舅!还不快过去谢谢舅舅。”
建平被刮得不好意思,拖着,最后还是走到舅舅面前说了:“谢谢舅舅。”
“不。该谢珊珊。编剧导演都是她。”
“不。平,要谢,先得谢你自己。从小学程度开始到大学毕业,这六年的书可是——你——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