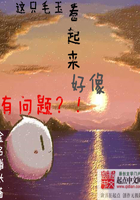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几个重要领域的佛教研究综述
宇恒伟 李利安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佛教研究方面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势头。据我们初步统计,2000—2006年中国内地发表佛教论文近7000篇,台、港、澳、发表论文2360多篇;中国内地召开佛教会议100多次,台湾省召开佛教会议70多次;中国内地和台、港、澳共出版学术著作1400多部,其中学术性较强的专著300多部;大陆地区以佛教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学位论文共140多篇,以佛教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共350多篇,台湾省以佛教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540多篇,以佛教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共50多篇。这么多成果的出现既是佛教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并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国家经济发达、学术不断繁荣的结果。从研究领域来看,藏传佛教研究、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居士佛教研究、民间佛教研究、佛教教育研究、佛教文学研究、佛教艺术研究、佛教与社会关系研究等格外引人注目。以下我们对2000—2006年共7年间中国学术界在这些领域内的研究进行简明的综述,以窥视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佛教研究的基本趋向。因为我们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学术研究成果资料,所以本综述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出现遗漏,特别向被遗漏的重要研究成果的作者以及广大的读者致歉,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和补充,以使我们对新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学术界的基本动向和发展趋势有一个准确的把握。
一、藏传佛教研究
藏传佛教属于北传佛教一系,原来主要流传于藏族和蒙古族地区,近现代以来又相继传入亚洲和欧美洲各地,引起整个世界的关注。汉语学术界特别是中国内地学术界近年来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越来越重视,成果也越来越多。
早在20世纪初,随着弘法活动的开展,藏传佛教逐渐引起世人的研究兴趣。20世纪30年代末,李安宅先生深入甘肃南部藏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写成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是藏传佛教的一部杰作,特别是社会调查方法的应用更有开创意义。20世纪60年代,王森先生的《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2]是20世纪藏传佛教研究的权威著作之一。其他著作如王辅仁的《西藏佛教史略》[3]等在藏传佛教研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总之,20世纪的藏传佛教研究在历史、翻译、教派等几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进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的藏传佛教研究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
1.藏传佛教的历史研究
2000年以前,藏传佛教的历史研究就获得了很大突破,特别是在通史方面,出现了以《西藏佛教史》[4]、《西藏佛教发展史略》[5]、《西藏密教史》[6]等为代表的权威著作。新世纪以来藏传佛教通史研究方面,尕藏才旦的《中国藏传佛教》[7]的第一章,详细论述了藏传佛教的历史进程。在断代史方面,罗桑开珠的《略论新时期的藏传佛教及其特点》[8]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藏传佛教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恢复、发展、繁荣。此外,如尕藏加的《藏传佛教与青藏高原》[9]也对藏传佛教的起源、形成、发展作了系统说明。
2.藏传佛教思想研究
藏传佛教本身是多种思想元素的融合,学术界的藏传佛教思想研究一般是从含义、判教思想、因明学、教派思想的历史与比较等几个方面展开。刘勇的《“藏传佛教”概念分析》[10]提出,从历史、理论、修行、组织、民俗等层面界定藏传佛教,有助于减少学术界许多无谓的争论。朱丽霞的《藏传佛教判教思想之分析比较》[11]对藏传佛教的判教思想归纳为两类:一是“三时判教”激发出来的判教系统,包括宁玛派、觉囊派和格鲁派;二是萨迦派的判教系统。从思想内容到评判标准,萨迦派的判教系统是比较标准的。剧宗林在《藏传佛教因明史略》[12]中,从因明藏传的背景、历史分期、特点三个方面,对藏传因明作了总体论述。因明藏传的历史分为前弘期初传和后弘期再传两部分,再传部分又分四个阶段,即复兴、盛传、研究和发展。藏传佛教因明的特点是崇尚发挥法称之说、创建堆扎式的学习方法、确立应成论式、重新组织因明体系。平措卓玛的《藏传佛教的传承制度》[13]认为,师徒之间的关系是藏传佛教不同派别传承的主要形式。其他文章如圣凯的《藏传佛教的忏悔思想———兼论能海上师的忏悔思想》,较为系统地梳理出藏传佛教的忏悔思想,这具有很好的创新意义。此外,斑斑多杰的《藏传佛教觉囊派的独特教义“他空见”考》[14]认为,“他空见”并不背离印度佛经。在藏传佛教思想方面,学术界的研究更加深入,关注的问题也更宽广,与2000年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3.藏传佛教的传播史和关系史研究
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与其他宗教的交流,同时藏传佛教在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特色。其中,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的比较研究是一个重点。相关文章有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初传时期的再比较》[15]、《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本土化之历史考察》[16]、《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比较论纲———两地佛教形成宗派后的比较》[17]。作者指出,以本土的思想文化为基础是汉藏佛教传播的重要原因和共同之处,汉藏佛教的传播历史体现共同的内在逻辑规律。崔红芬的《藏传佛教各宗派对西夏的影响》[18]指出,藏传佛教的大手印和道果等教法对西夏影响很大。才吾加甫的《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及发展》[19]利用丰富的史料,对藏传佛教在新疆卫拉特蒙古的传播情形进行非常详细的说明。赵沛曦的《论藏传佛教在云南丽江的传播》[20]对藏传佛教在唐代传入丽江进行肯定,并对从唐到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丽江的发展作了论述。此外,藏传佛教在青海、甘肃、四川的传播也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关系仍是藏传佛教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藏传佛教与尼泊尔等佛教的关系是学术界研究的空白。
4.藏传佛教艺术研究
藏传佛教艺术独具特色,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艺术魅力,一直是世人关注的文化现象。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张世文编写的《藏传佛教寺院艺术》[21]介绍了藏传佛教的建筑、藏传佛教的具体表现形式、藏传佛教的器用等,全方位地表现了藏传佛教的寺院艺术。在研究方法上,我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实地考察和对整体风格的探索,注重汉藏文献的应用。如李翎的《藏传佛教阿弥陀像研究》[22]以阿弥陀像为个案,梳理藏传佛教造像样式的历史线索,认为汉传佛教的造像艺术对藏传佛教阿弥陀像产生了主要影响。她的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研究是近年汉语学术界最突出的,特别是关于藏密观音造像的研究,代表性的作品是《藏密观音造像》[23]。们发延的《藏传佛教的唐卡艺术》[24]以藏传佛教独特的唐卡为研究对象,从技术上分析了唐卡制作的七个工序。彭肜的《藏传佛教雕塑艺术及其特征》[25]则集中分析了雕塑艺术的类型和特征,认为藏传佛教雕塑体现了藏族文化独特的审美情趣。谢继胜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现状与未来》[26]对藏传佛教艺术作了归纳和总结,认为我国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刚刚起步。
5.藏传佛教与民俗生活的关系研究
藏传佛教在藏族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成为信众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传佛教与民俗生活的关系研究的重点是藏传佛教对民俗生活的影响。如索南才让的《藏传佛教对藏族民间习惯法的影响》[27]指出,藏族民间的“希董”法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张荣红的《藏传佛教对藏族首饰表现的影响》[28]从首饰的材质、种类、造型、纹饰等方面都显现著藏传佛教的色彩。唐吉思的《藏传佛教因果报应说对蒙古族道德观的影响》[29]认为,藏传佛家伦理思想使他律道德规范转化为自律道德规范,对社会的稳定更具积极意义。
6.藏传佛教与当代社会关系的研究
近代以来,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藏传佛教也在经历不断的变化。如何应对社会变化以及如何调整自身成为新时期藏传佛教的主要任务之一。首先,关于藏传佛教如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周毓华的《试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30]认为,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有历史、政治、理论三方面的基础,党和政府的引导是主要途径,藏传佛教界的努力是内因。其次,关于藏传佛教如何应对世俗化问题,马文慧的《藏传佛教世俗化倾向刍议》[31]指出,藏传佛教的世俗化是佛教适应藏族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然结果,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应对世俗化,同时加强藏传佛教自身的建设。另外,关于藏传佛教与构建和谐社会,主要集中在分析利用藏传佛教的积极因素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方面,如王淑婕的《论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之辨证关系》[32]就主张,利用藏传佛教的文化、道德规范、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
另外,学术界也对藏传佛教的女性问题、佛教伦理、环保等问题进行研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综上所述,2000年以来的藏传佛教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但如何向纵深、细致、现实以及多领域发展将成为未来藏传佛教研究的新问题。
二、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
我国云南上座部佛教属于南传佛教一系,主要流行于云南西南部的临沧、德宏和西双版纳,对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佤族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研究云南上座部佛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的佛教研究;有助于更加合理地处理民族和宗教问题;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其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在汉语学术界的佛教研究中,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相对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研究是比较滞后的。早在1940年,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33]中,以史籍和高僧为重点对滇黔的佛教作过专门的论述,但其中大部分是汉传佛教而不是上座部佛教。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滞后固然与语言、地域有很密切的关系,但与学术界对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的漠视又是不可分割的。2000年以前,汉语圈学术界在云南上座部佛教的历史、僧阶、佛教艺术、佛教典籍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从总体上讲,业已取得的成绩还非常有限,这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上座部佛教研究成为民族问题研究中的局部问题,即学术界往往在对民族问题的研究中涉及少许上座部佛教,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研究的广度都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二是有关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的论文很少,专著更是少之又少;在学科建设、专业人才培养、刊物的发行、研究机构的设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探讨与建设空间。总之,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汉语学术界的云南上座部佛教研究在佛教文献、佛教艺术、上座部佛教的特点等方面继续深入,特别是在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对语言的影响以及上座部佛教的伦理、禅法研究方面,取得比较突出的成果,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上座部佛教教育研究
上座部佛教与藏传佛教在佛教教育方面有自身的特色,并且在各自的发展和对社会的影响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上座部佛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存在密切的关系,因而对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东南亚国家的佛教教育类似,在传统的佛教教育体制中,佛寺不仅被傣族群众当作宗教活动场所,而且还被当作教育机构和学习文化的场所,从而形成了特有的“佛寺教育”。但是,僧侣教育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而境外僧人的教育又明显高于本地,这就造成僧侣教育与世俗佛教教育的脱节。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岩香宰在《从赕佛到现代佛教教育的跨越———对云南西双版纳佛教教育的思考》中提出几点见解:提高宗教管理水平;促进学校教育的健康发展;注重佛教人才的培养。[34]这几点见解都是很有意义的。关于上座部佛教教育研究,在相关书籍和论文中也有涉及,表明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2.上座部佛教传播和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上座部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属于佛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关于上座部佛教何时传入云南的研究中已经涉及这个问题。由于对上座部佛教何时传入云南的时间没有一致的界定,因而关于上座部佛教传播和发展研究的时期和侧重点是不同的。杨学政的《云南宗教史》[35]介绍了明清时期上座部佛教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认为14世纪下半叶润派首先传入云南的西双版纳。稍后,摆奘、朵列、五抵传入德宏、临沧,并逐步得到传播和发展。这是对2000年以前学术界探讨上座部佛教传入成果的简单归纳。姚珏的《云南上座部佛教五十年》[36]则详细描述了新中国成立来的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具有系统、全面、翔实的特点。
3.上座部佛教对语言影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