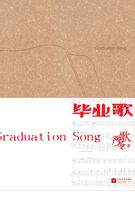但是,他仍然没有丝毫轻松,因为他的亲笔信还在缪斌手里。如果将缪斌逮捕进行审讯,他将这封信在法庭上公布出来,势必全国舆论哗然,同样有损他头上那顶千金难买的桂冠。蒋介石急得一个通宵睡不着觉。宋美龄知道他心中的苦闷之后,开导说:“大令你,可以通过何敬之先生出面,设法把那封信追回来。”
今天早晨六点,何应钦接到蒋介石追回那封信的电话,整整绞了一个小时的脑汁,才给缪斌打电话。现在,阿弥陀佛!终于如愿以偿。
缪斌一路做着美梦回到家里。一进屋,就喜滋滋地对妻子说:“敬之兄的推荐书写得真好!几句话就把我的才能写出来了。在他的笔下,我简直是可以担负国家元首的栋梁之材!”他笑笑,“秀锦!从现在起,你这个‘秀’字加个丝旁。”
“好,好,听你的,加个丝旁。”项秀锦也做着夫荣妻贵的美梦。
她说到这里,门卫报告戴笠和贾金南驱车来了。缪斌和项秀锦赶忙出门迎接。宾主在会客室坐定,缪斌对妻子说:“现在已是下午四点二十分了,你去准备几个好菜,留戴先生和贾先生在寒舍吃晚饭。”
“不用了,我还有许多事等着去办。”戴笠说,“缪夫人请坐,有些事应该让你知道。”
项秀锦以为戴笠也会带来好消息,欣喜地挨着丈夫坐下来。
可是,戴笠却显得难过地说:“我说弼丞兄,你也太不注意政治影响了,不仅府上成天门庭若市,而且你本人也到处探亲访友,引起上海许多人的严重不满,纷纷给蒋委员长写信,提出批评和质问,像弼丞兄这样一个在汪兆铭政权担任过要职的人,为什么受到政府的包庇而不予以逮捕。唉!这使蒋委员长为难极了。”“我曾经提醒过你,要你闭门谢客,少出头露面,可你不听。”项秀锦抱怨说,“现在,唉!”缪斌很懊悔。“我接受雨农兄的批评,从现在起,我闭门谢客,也闭门不出。”他说。“为时已晚啊,弼丞兄!”戴笠说,“你住在家里,那些人还是一双眼睛瞪着你哩!因此你得回避一下。”
“去哪里好?雨农兄!”缪斌心里沉甸甸的。
“对你来个假逮捕,暂时住到福履里路的楚园去。”戴笠说,“等社会舆论平息了你就回来。”
“与那些汉奸关在一起?”缪斌一惊,一副羞以为伍的表情。
“为了减轻委座的政治压力,你就委屈一下吧!”戴笠说,“让你单独住一个房间,可以带厨师去,甚至夫人也可以同去。”
“你就带个厨师去吧!”项秀锦说,“白天我去照顾你,晚上我回来。孩子们在外面谋事和求学,家里实在丢不开。”
“好,我去。”缪斌无可奈何,“请夫人为我准备换洗衣服和烟具,要伙房王师傅与我同去。”
楚园是原上海市警察局长卢英的住宅,因他号楚僧,此宅取名楚园,被没收后成了关押部长级汉奸的地方。汉奸多,房间少,五个人住一间。缪斌去后,就把看守所长的办公室让出来给他住。缪斌一住下来,就到各个房间看望老朋友,每到一个房间就说:“雨农兄要我来这里避避风声,过一向就回去。”大家心中有数,不置可否,一笑置之。
第二天下午五点,一辆囚车开进楚园。接着从囚车上跳下六名武装法警。汉奸们住在楚园半年多了,还是第一次见到囚车和法警,大家纷纷走出门来,提心吊胆地站在一至三楼的走廊上,不知自己是否是第一批提审对象。唯独缪斌没有受到惊动,他由妻子陪同,悠闲自得地横躺在床上抽大烟。
“缪斌!”偏偏一个法警走进他的房间,“别抽了,收拾行李跟我们走!”
“要我跟你们走?这是谁的命令?”缪斌思想上不承认眼前的现实,但潜意识促使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中央的命令。”法警说,“按照政府颁布的提审法,人犯被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不释放,就得解往提审机关。”
“把我当人犯?”缪斌惊骇得乱了方寸,只觉得全身膨胀起来,头皮发麻,两腿发软,尿泡也觉得憋不住了。“若说执行提审法,那么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一住几个月,为什么没解往提审机关?”他惊疑地问。
“那我们不知道。”法警说,“我们是奉命行事。走!上车去苏州高等法院。”
“这就活见鬼了!”缪斌叫喊着。情势急转直下,把他翻落在一个飘绕着无尽烟雾的隘口,进退都十分困难,唯有透过漫漫人生途中的风尘做着茫然的隙望。他对已经吓得面无人色的妻子说:“你马上回去给敬之先生和雨农先生打电话,眼下发生的事,他们知道不知道?都持什么态度?”他对这两个人仍抱有幻想。
江苏省高等法院设在苏州道前街五十六号,这里原是清代的臬台衙门,五开间大门面,一对大石狮雄踞左右,一派庄严气氛。
法院对缪斌的审讯抓得很紧,决定三月十一日下午开庭。消息传出,南京、上海、无锡、苏州一百二十多名新闻记者赶来采访。这天,法院内外戒备森严,门口有武装法警四人守卫,从门口到审判庭的二百米处,站立着十名法警;审判庭门口,又由四名法警守卫着;庭内四角,各站着四名法警。下午两点,庭内的旁听席上就坐满了记者和听众,项秀锦也神色不安地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等待观看使她痛苦而又难堪的一幕。她是昨天下午来苏州的,给看守缪斌的法警送了六两黄金,才将一封信交法警转给丈夫。她在信中告诉丈夫:“我打电话给何敬之先生,他说他对先生的被捕一无所知。戴雨农先生也是这样说的。两位都表示为先生说话。”
下午两点三十分,庭长石美瑜、推事陆家瑞和余樽暨穿着艳蓝色法衣,书记官朱鸣球身着黑色法衣,检察官李曙东身着紫红色法衣,带着一股正气走上审判台就座。
新闻记者和旁听者们注意到了,坐在审判席中间座位上的石美瑜是那样眉开眼笑。他又名可珍,福建闽县人,二十岁毕业于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原来,三天前他刚满三十岁,就由刑事庭推事提升为庭长。年轻得志,心情特别好。
两分钟之后,缪斌由两名武装法警从候审室押上法庭。也许是他从妻子那封信中获得某种安慰,神色显然很镇静。项秀锦从座位上站起来,想与丈夫打个照面,以表示她的存在。但她刚起身,目的尚未达到,她的两个肩膀就被一个法警抓住,被猛地按了下去。
审判厅里出现短暂的沉寂。这种沉寂,对于被审者是一种恐怖的气氛,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没有敲扑捶楚之声的刑罚!
审讯开始,石美瑜按惯例问及缪斌的籍贯、年龄和职业。缪斌说:“江苏无锡人,现年五十岁,一向从事政治工作,自从民国十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始终与党心连心。”
石美瑜起身宣读起诉书。起诉书说:“中日战争爆发后,缪逆斌遽尔变节叛国投敌,与日寇特工古野宏人、吉村虎雄、根本博、山本荣治等相勾结,于民国二十七(一九三八)年建立汉奸组织新民会,任副会长兼中央监察部长,鼓吹中日满合作,反抗中枢,并建立青年训练所,实施奴化教育。民国二十八(一九三九)年六月赴日本,访问敌酋近卫文麿、小矶国昭、阿部信行、米内光政等人,表示亲善;且在东京与汪逆精卫、周逆佛海商讨和平运动。以后附汪逆,先后任立法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民国三十九(一九四○)年策动原江南第四游击队副总指挥李长江投奔汪逆。”石美瑜接着说:“缪逆斌的犯罪行为,已由检察官李曙东氏依照《惩治汉奸条例》第二项第一款‘凡曾任伪政权要职者可作汉奸论处’和第十三款‘通谋敌国,图谋反抗祖国者处死刑’之规定,对缪逆斌提出公诉。法院予以受理。缪逆斌!你有何话可说?”他说罢,威严地坐回原处。
“我要说的话可多呢!”缪斌脑袋晃了晃,“起诉书所说基本上是事实。但并不是叛国投敌,而是以一种特殊手段救国。我出任新民会副会长、立法院副院长、考试院副院长是为从事和平救国作掩护。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这可以从我八年前托朋友于瀚明先生送给何敬之先生的《苏武牧羊图》立轴,以及我亲笔题写在立轴上的一首出诗看出。我的拙诗是:‘只身羁漠北,大节柄匈奴。生死置度外,苦志行若愚。几历酸辛事,渐审道不孤。逾云怀故旧,何日得昭苏?群羊绕我旁,畴分汉与胡。彤云郁未舒,壮士辄长吁。’何先生收到立轴后,写信对我的馈赠表示感谢,对我这首拙诗备加赞赏。前年十二月中旬,我去重庆看望何先生时,他特地把我领进他的书房,指着挂在墙上《苏武牧羊图》对我说:‘弼丞兄的诗写得好,你的苏武精神很值得赞许。’人们常说‘明哲保身’,我是‘明哲保群,’保护同胞不受日寇的欺凌和杀害。”
台下发出一阵嗤鼻的冷笑声。石美瑜拍打着惊堂木说:“缪逆斌应持诚实态度,不许狡辩!”
“我的话并非狡辩。”缪斌说,“是的,我劝说李长江先生投奔南京出任和平军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他指挥的第四游击队原来不足一个军的兵力,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后指挥三个军和一个独立旅。现在,李长江先生这支部队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是我对党国的一大贡献。这难道是我在狡辩!”
台上台下都一怔,仿佛缪斌成了原告,石美瑜成了被告。“缪逆斌说话不能割断历史!”石美瑜又拍打一下惊堂木,“民国三十九(一九四○)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一年,你将一支抗日部队转变为叛国部队,就是犯罪!你仍然是在狡辩。”
台下出现一阵活跃,大家禁不住想鼓掌。
缪斌愣怔片刻,继续说:“起诉书有个很大的疏漏。我在小矶国昭出任日本首相期间,曾受蒋委员长的秘密派遣,多次往返重庆、南京、东京之间,为实现中日和谈停战而奔波。退一万步讲,即便起诉书所陈事实是过错,那么,我功大于过。”
缪斌一语惊四座,台上台下都面面相觑。
“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准缪逆斌在严肃的法庭上胡编捏造。”石美瑜手中的惊木堂拍打得山响,“缪逆斌!你现在必须以忏悔的态度说说你对起诉书的认识。”
“我岂敢在严肃的法庭上胡编捏造!”缪斌不以为然,“蒋委员长秘密派我赴日本议和,有他写给我的亲笔信为证。这封信我于大前天,也就是三月八日上午交给了何敬之先生,建议法庭进行调查。”
台下出现一阵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