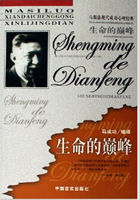“气”和“色”是中国古代哲学独有的概念。“气”,既是指生命体内流转不息的综合性物质,又是指生命的原动力,或称生命力。它无形无质,五色无味,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在体内如血液一样流动不息,气旺者可外现,却能为人所见。而“色”则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它是显现于人体表面的东西,就人体而言,就是肤色。人们日常说某某人面部发黑,有不顺之事,就是指色而言。中国医学都认为,“气”与“色”密不可分,“气”为“色”之根,“色”为“气”之苗,“色”表现着“气”,“气”决定着“色”。“气”又分为两种,一为先天所禀之“气”,一为后天所养之“气”。即孟子所说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概如此,“色”自然也有先天所禀之“色”与后天所养之“色”的区别。古人把“气”和“色”这两个哲学概念拿来判断人的优劣。“气色”既有后天所养者,它们一定是在不断运动变化的,所以又有“行年气色”之说。
扁鹊是战国时代著名的医生,技艺高超,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有一次他路经齐国,蔡桓公知道后,便派人以宾客之礼接待他。
一见到蔡桓公,扁鹊立即对他说:“据我的观察,您已经生病了,不过好在病症只起于皮肉交会之间,若能及早医治,就不会有危险。”
可是蔡桓公笑了笑说:“我没有疾病。”
等扁鹊离开后,他还对左右说:“没想到扁鹊这个名医,竟为了想谋利,而诬指一个健康的人有病。”
过了五天,扁鹊又来请见,向蔡桓公说:“您的疾病已蔓延到了血脉,如不医治,会十分严重。”
但蔡桓公不信,还是回说他没有病。
又过了五天,扁鹊再度向蔡桓公说:“您的病变已经侵入内脏了,若再不医治,恐怕将十分危险。”
这时蔡桓公有点儿不高兴了,认为扁鹊又来危言耸听,于是不理睬他。
再过五天之后,扁鹊前去求见蔡桓公,一见到他,扁鹊一句也不多说,急忙告退。蔡桓公觉得很纳闷,便派人去询问扁鹊退走的原因。
扁鹊说:“病情在皮肉之间时,用推拿就可以治好;
病情在血脉之中时,用针砭就可以治好;若病情进入脏腑之内,用药方慢慢调理,也可以治好。但如今桓侯的病情已深入骨髓里,就是连掌管生命的神,也要束手无策,又何况是我呢?因此索性也不劝他再做医疗了。”
果然五天后,蔡桓公卧病在床,使人赶快去请扁鹊来救治时,扁鹊已经离开了齐国。最后蔡桓公就一病不起,溘然长逝了。
真正有功力的中医,从一个人的气色、眼神等处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身体状况,譬如扁鹊。这里讲的色,非色狼之色,而是一个人的面色;气,非惹祸之气,而是生命力的一种表现和称谓。气是道家修炼的一个术语,气功的气。围棋中也讲“气”,棋子如果无气,意味着死,人如果无气,也就归于黄泉了。
武则天:借佛愚民,制造舆论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又有云:“知人知面不知心。”可见,人心难测。历史上,借他物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事屡见不鲜。武则天借佛愚民一事便是个极好的例子。
武则天弱势斗强势,助力者少;事父又事子,有违人伦;女子当皇帝,更背伦理。每一件事都是对时代和传统的巨大挑战,所以抓住人心,让人跟着走是非常重要的。武则天的方式是:紧要关头一定要鲜明地表示出自己的态度,举事之前先造舆论。
在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中,无忌被剥夺爵位贬到黔州的同时,他的外甥,以勇猛著名能“力搏猛兽、捷及奔马”的凉州刺史赵持满被残酷拷打,死后暴尸街头。这是武氏向异己者提出的警告——不得蠢动!宰相连外甥都保不住,谁还敢不要命和皇后作对。
这是武氏极为拿手的一着,其特点就是利用手中的政治指挥棒来操纵时局。每逢遇到棘手的问题的时候,她就鲜明地表示态度:我喜欢的是什么,讨厌的是什么;你们可走那条道,不可以走这条道;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反对我的,即使是宰相,也抓起来甚至杀掉;拥护我的,地位低的官员,也可以提升为宰相。
由称制的天后转向皇帝,尽管已经水到渠成,但这毕竟违背儒家千古流传的伦理,谁放第一炮,可能就留下千古骂名。群臣处在犹疑中。载初元年九月三日,侍御史傅游艺突然率领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将“唐”的国号改为“周”,赐皇帝姓“武"氏。游艺官居从七品上阶,为何能率领籍在关中的九百余人前来上书?而所言的内容又竟是涉嫌犯十恶罪的“谋反”和“谋大逆”之罪?显然,这是有人授意,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武则天的反应是对此请愿不予允许,但也不予逮捕惩治;不仅如此,她反而超擢傅游艺为正五品上阶的给事中,即一口气让他超升了十阶。
没两天,就有六万人再次请愿建立新朝。为何人数又骤增了?一是傅游艺受到的重赏刺激了人们,另一则是恐怖政策下武氏反对者的下场震慑着人们。这一威一赏如同魔杖一般抓住了人心。
九月九日,六十六岁的神皇实行“革命”,改国号为“周”。
武则天为了争取传位的顺利实现,针锋相对地对官僚展开宣传教育。这就是她为《臣轨》写的序言。《臣轨》是北门学士以皇后的名义写的。在书中,她力图在读者中树立“孝”的观念。她发现了“孝”与“忠”处于不两立的地位。她强调人们尽孝。她钦定的整个《姓氏录》门阀体系就是一个大家族,这个家族的家长就是武则天。她以慈母般的口吻让臣下同功共体。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斗争,武氏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取得胜利。
武则天还大兴神道教化的设施。她兴造天枢、明堂、九鼎、肖神,以及封禅,乃至一再改元,似乎借助这些才能获得信心,强化她的神秘力量。她觉得如此才能够向天下臣民“证圣”,才能够彰显自己是“天册万岁”。她是在自愚,更是在愚民。
李君羡事件反映了武则天要控制世人的头脑。开国功臣李君羡某日当值玄武门,时直太白星屡次在白天出现,太史乃占卜说:“当有女主昌。”民间又谣传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对此很忌讳。后来得知李君羡小名为“五娘”,想起太史和谣传之言,找个借口将他杀了。到了武则天革命称帝,李君羡的家属诣阙诉冤。女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下令恢复李君羡官爵,重新礼葬。她是想让人们相信,她称帝是天意。其实是否真有所谓谣传,还是有人故意加以渲染,是大有疑问的。
新帝国的精神支柱是佛教。道教是李唐王室祖宗之教,可供女皇利用的有限,儒教虽广被利用,但正统儒家反对“牝鸡司晨”,故早年在母亲影响下就笃信佛教的女皇只有向佛教寻求奥援。
她的情夫薛怀义在这方面立有大功。他发现《大云经》里有女主降生成佛之文,就取旧译本加以新的疏解,巧为附会,为武则天篡位制造舆论,证明她的“革命”符合佛教的授记。他们还将武则天说成是弥勒佛转世,套用南北朝以来流行的“皇帝佛”、“皇帝菩萨”的说法,把女皇塑成当今的“皇帝佛”。武则天同意这种说法,并崇佛兴造大像,她的目的是为了佛教的政治意义——为其“革命”和统治提供意识形态的帮助,通过自己的造神愚弄和控制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