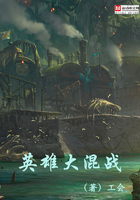荣笑雨
1981年,我参加工作,单位有个同事是残疾人,这让我很担心,担心自己的大意可能会伤害她?担心自己选择与她交往的方式会不会不正确?我到底应该抱着特殊的同情、尊重、爱惜之心还是就把她当做和我一样刻意随便嬉笑怒骂的普通人呢?她希望的方式是什么?我的举止言谈会不会冒犯她的尊严?这种认识观念让我很长时间都无法摆脱忐忑与纠结,半年后才学会与之坦诚相处。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以她为题材的小说。
二十多年后,我读着心钢长篇小说《水滴》的打印稿,这时的心钢已经在残联工作多年,因为平时来往密切,会经常去他工作的残联大楼,跟着也就认识了很多他身边的残疾朋友,《水滴》里的这个那个,很多我都能在现实的人群中找到熟悉的身影,平日里不管在哪相逢,都会有随意的寒暄或者热情的交谈,也就是在这些寒暄中,我才慢慢发觉我可以正常地认识他们的这个世界了。
是的,正常。
我们一开始跟他们接触,无法避免地要有“他们是残疾人,我们要尊重他们同情他们”的先行观念,因为他们是相对脆弱敏感的群体,因而也就更容易受到伤害。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很大程度上就是整个社会群体对残疾阶层的态度,人类社会和动物社会的本质区别我以为更多的不是生存智慧,而是道义,动物的生存法则必须剔除弱小,人类的进步法则必须让弱小受到同等待遇。换句话说,这种道义就是人的智慧。但这种道义这种智慧是指彼此在地平线上“平等相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俯视性的施舍,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卑躬祈求。
一个人缺少什么,就会特别渴望什么。在跟心钢交往中也认识不少残疾人,最先让我震撼的就是盲人对光线的向往,对“看见”的向往,他们完全可能拥有正常人都有的生活、工作、爱情、家庭,而最大的遗憾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爱情,近在咫尺的生活只能让触觉来感知,“看见”成了一种梦想,这种本来是最简单的认知成了不可企及的高天流云,当“简单”都不可企及时,对“简单”的渴望就变成了焦虑,对设计家来说,越是简单的就越是上乘的美妙的,对“梦想”而言,越是简单的就越是难得的。爱情来了,他们拥抱爱情,却不知道爱情的模样,他们有加倍的拥抱、加倍的触摸、加倍的吸吮,加倍的珍惜,加倍的放在心里让她疼起来,心疼得不知自己该怎么办,这显然不是正常人能理解的。所以,当我在一本盲人写的小说里看到这种对爱情的心疼时,也踏实地跟着心疼起来,那是一种认识和理会后带来的心疼。这种认识让我对一个群体有了一种新的认识观,从而又重新认识这个群体。
这个世界是不均衡的,也是不平等不公正的,文明对人、对社会提出平等公正的要求就因为看到了种种不平,把铲除不平作为文明进步的标志。因为在残联工作的缘故,心钢对市政设施中的无障碍建设部分特别敏感,外出看到了就会脱口而出“这里怎么没有无障碍标志?”或“这一点点都做了无障碍的考虑,周到。”他自己并不怎么需要使用这些设施,但他心里装着的不是他自己的方便,甚至也不仅仅是残联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方便,而是整个社会是不是均衡地考虑到了所有群体的利益。他并不主张残疾人时时处处要以残疾人自居,时时处处有怨天尤人的权利,而是主张无论正常人还是残疾人都首先把自己当做一个“常人”,在社会意义上,谁都是也应该是个完整的人,至于伤残,那是个意外,是跟肾结石胆囊炎一样的意外。只有大家都站在同一级人行道上说话,彼此才没有压抑感,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就该站高一级或自甘站低一级,在心理出发点上就不正常。
在心钢小说中描述的残疾人群,虽然行为言谈不可回避地带着残疾阶层的烙印,但心钢从自己的认识论出发,当然地回避了残疾人“身处低层、弱势群体”的天然意识,还有逢涉及残疾人就一定要苦斗成才、一定要奋进不息、一定要贵人相助的公认模式,而是坦然地面对有缺憾的命运和并不光明的种种人生,在他们中也有捣蛋的,也有不上进不争气的,成功者未必会事事俱佳,失落者也可能光华闪烁。
小说的人物设计尽管是群像谱,但一点也不难看出乔花是作者很花心思塑造的形象,这是一个漂亮性感的盲女,一个有情有义有渴望的母性象征,言语不多的外表下藏着对幸福毅然决然的向往,可以受伤,不能受辱,可以身处底层,不可心灵低下,可以不求回报,不可有恩不报,她对曹一木的“以身相报”几乎是挖空了心思,她知道曹一木在清醒时会断然拒绝这种报答,她就制造了一个让曹一木在接受自己按摩后舒服享受的沉睡机会,再把自己“献出来”,在两年前阅读小说的第一稿时,我并不以为这是可以成立的,还跟朋友说起过这段华彩刻意了、牵强了。当今年第二次阅读时,其中的情节铺垫和感情逻辑显然被重新仔细梳理,顺了很多,有了“魅”气,有了可以相融的欲望,很多描写是很能诱惑阅读的,比如,乔花主张不要开灯,因为对她而言,开不开灯世界的颜色都是一样的,这是特殊身份的必然。但对阅读者来说,两个身心亢奋的年轻人处在黑暗的房间里,还能彼此闻到对方具有性别身份的气息,这时对他们之间的发展已经充满假设。而当他们之间的高潮情节居然是以一种让人不可想象的方式(曹一木沉睡中)发生时,几乎不由分说就掉进了这个激烈的陷阱,这个陷阱可以说就是作者最成功的阅读诱惑。
在串故事的人物曹一木背后,一开始就有一个现代生活的影子,他有一位很有话缘的网友“花泪”,这缕信息若隐若现,透露的是现代生活递交过来的公平触须,在谁也没见过谁的世界里,有一种隐约的平等,我们会自然地以为这道触须的后面仅仅是一缕散不开的标志性气息。不料这缕气息最后竟成为一条神秘的线索,一直躲在后面的网友“花泪”以真名“华蕾”现身、以团圆的方式现身、以爱情的方式现身,故事突然从层叠的焦虑变得温暖、欣慰,这时才明白,这条线索才是作者的理想,这个场面才是常态的渴望,两个隔着雾霭的人拨开朦胧,把手握在了一起,这不就是我们都希望的么?人必须从自己潜藏的角落走进可视的舞台,这才是应有的生活。对谁都一样。对平等的渴望首先是能坦然地面对自己,坦然才会带来平等。
心钢也是这样坦然面对自己的。因为出生时器械伤害,他行动说话都不方便,出行时(尤其是下山、下楼时)如有需要,他会大方地说声“扶我一下”,吃饭时会跟身边的人说“帮我夹点那个……”。尽管知情者大都会主动留意这种“搀扶”,但难免会有大意疏忽的时候,但当我们面对心钢的坦然时,我们也坦然起来。这让我觉得生活的正常。
是的,正常。
正常地认识生活是生活的必须,但有时偏偏就做不到,或者你身处谬误中还以为自己正常,这大概是因为一开始的认识观就是错的。在斯宾诺莎的方法论体系里,观念先于方法,观念决定方法,错误的观念带来错误的方法,错误的方法必将错误地认识世界。
很庆幸,我能正常地认识这个世界。正常地认识有乔花、有曹一木、有班固的世界,也像乔花、曹一木、班固那样以“我”才有的独特方式认识世界,像乔花那样,即便是“有没有灯光都一样”的世界,不一样也有温暖和光明吗?
儿时听过一首儿歌,旋律套用的是陕北秧歌,歌里唱着“跛子要跳舞,瞎子要看戏,聋子要听收音机”,虽然有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恭,也披露了一种残疾心理对正常生活的对应渴望。这种渴望也就是对平等世界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