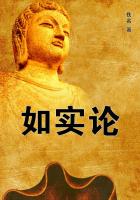一
夜晚,牛腩嚷着要从青河大桥跳下来时,曹一木正与“感时花溅泪”在网上聊天。
曹一木的网名叫“城春草木深”,取自杜甫的《春望》,正好将他姓名暗藏其中。他命里缺木,爷爷给他取名一木,喻意一草一木都是生命,值得珍惜。而“感时花溅泪”是曹一木在网上认识的美眉,其网名也取自《春望》。“感时花溅泪”说她在QQ上见到同以《春望》诗句做网名的“城春草木深”,忽生兴致与好奇,搭讪了一会,感到“城春草木深”幽默诙谐,便把他加为好友。从此,两人一来一去,从陌生到熟悉,每晚都要在网上聊上几句。偶尔谁有事不能上网,都要向对方事先留个言请个假。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两人的称呼也做了简化,他叫她“花泪”,她叫他“草木”,听起来亲切许多。
曹一木所在的城市叫青州,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城,一条细长的青河绕城而过,像一只纤长的玉手抱着个粗大的陶罐漂浮在淡淡的青雾中。山城经济欠发达,市民的生活悠闲散漫。曹一木在残联上班,业余喜欢写点东西,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爱叫他曹作家,也不知是褒是贬。
曹一木的代步车是一辆深蓝色的残疾人电动三轮车。他原先有一辆烧黑色柴油的残疾人机动三轮车,打火时“突突突”地像开手扶拖拉机,熟悉时的人一听到那“突突突”的声音就知道曹一木到了。上个月,曹一木得了5000元稿费,便决定“低碳”一回,把残旧的“黑坦克”换成电动三轮车。那是辆可进出电梯的电动三轮车,小巧轻盈,骑行灵活,带手摇装置,有倒车功能,可助力行驶,免去万一没电的后顾之忧。曹一木爱不释手,给爱车取名为“蓝精灵”。
自从在QQ上认识“花泪”后,曹一木就爱发一些奇谈怪论。“花泪”好脾气,耐心地等待他打出一段长长的文字尽其胡侃。知道他是作家后,她也笑他,你是不是写小说写多了连聊天也当文章来写?不管三七二十一上来就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文字也不嫌累得慌。曹一木嘿嘿地笑着:人家写文章只是“豆腐块”,我可是一写就是“一板豆腐”,好多赚点稿费。“花泪”说:你这是无病呻吟牙痛乱哼哼。曹一木笑曰:是也非也。哥哥我写的不是帖子,而是寂寞。
曹一木在市残联办公室具体负责信访和残疾人专门协会工作。领导说你是残疾人又是残疾人干部,以双重身份接待来上访的残疾人,既合适又有说服力。曹一木想起“以夷制夷”四字,一时无语。青州市郊有座青云寺,传说六祖慧能曾在此闭关顿悟。曹一木每次陪朋友到青云寺游玩,都要在弥勒佛面前站一站。他有点理解佛祖为什么要把这头陀放在寺前笑哈哈地接客,实在是人世间欲望太多痛苦太多穷于应付,读读弥勒佛两边挂的一副对联就能洞观其心境:
日日携空布袋,少米无钱,却剩得大肚宽肠,不知众檀越,信心时用何物供养
年年坐冷山门,接张待李,总见他欢天喜地,试问这头陀,得意处有什么来由
曹一木想,要是我有弥勒佛这样的好心情就阿弥陀佛了。这不,今天上午11点半左右,一个高颧骨黄斑脸的中年女子拖着一条残腿来敲曹一木办公室的门。她像是走了很远的路,满脸尘土,身上发白的工作服被汗水沁透了一大块,沁出点点盐斑。曹一木忙请她坐下,倒了一杯凉白开递上。女子表达有些障碍,絮絮叨叨地说了10分钟,曹一木这才弄明白其来意。
女子叫刘小兰,小时候因小儿麻痹症落下右腿残疾,她在一家棉纺厂下岗后很难再找到工作。刘小兰的老公9年前就没了,留下两个孩子由她独自拉扯大。两个孩子中,老大是男孩,今年高考成绩很好,被北方大学录取;老二是女孩,患有唐氏综合症(又称先天愚性),12岁的孩子只有3岁的智力。昨晚,正为儿子上大学学费发愁的刘小兰,忽然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本地新闻,说有老板愿意捐钱资助贫困大学生上学。她像是在深井里摸索了很久忽然见到一点亮光。电视节目一晃而过,这亮光究竟在哪却不得而知。于是,她今天早早起来四处打听,先是到青州电视台,电视台说资助读书的事应该找团市委,那里有希望工程;团市委说,你是下岗工人,应找工会;工会说,你是女工,应到妇联;妇联说,读书的事,应该找教育局;教育局说,你经济困难可申请低保,找民政局吧;民政局看了眼她瘸着腿说,你是残疾人,快去找残联。刘小兰没到过市残联,打听了很多人,才有一个摩的司机把她送到残联。刘小兰越说越伤心越说越激动,她早上7点多出门,几乎跑遍了大半个城市,这才找到残联。她说跑了这么多单位,只有残联才有人请她坐给她一杯水喝愿意听她说话。
一张笑脸,一声请坐,一杯开水,这本是待人接物起码的礼节。曹一木听着刘小兰的哭诉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他站起来给刘小兰的杯里续了点水,委婉而带些无奈地解释说:刘姐,你如此身体,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真是不容易。可你儿子是健全人,按照政策,残联只对考上大中专院校的残疾学生有一定的资助,但对于残疾人的子女上大学,目前暂没有这方面的资助政策。你还得从别处想想办法。
看着刘小兰期待的目光渐渐暗了下来,曹一木于心不忍,说:这样吧,你的情况我记下来了。我试着帮你多方联系一下,看有没有热心人帮帮你,行吗?刘小兰像在溺水中抓到一根稻草,连连说:曹同志,你是好人一定要帮帮我啊!曹一木感到身上有点沉甸甸的。
眼看已是中午12点半了,曹一木要到饭堂给刘小兰打一盆饭,刘小兰摆手说:不用了,女儿一个人在家,我要回家做午饭了。曹一木送她到楼梯口,她拖着瘸拐的右腿正要沿着步梯俯身而下,曹一木挥手拦住:这里是8楼,坐电梯吧。刘小兰有些不好意思:我是走上来的。我没坐过电梯,心里有点怕。别怕,我送你下去。曹一木等电梯门开后,把她扶进去。不到十秒钟,“嘟”的一声,电梯就到了一楼。刘小兰欣喜地说:真是快啊。看着刘小兰一拐一拐地走出大门,曹一木心里不知是啥滋味。
曹一木在网上告诉“花泪”,刘小兰所找的6个部门分别在城市的东南西北在不同的办公大楼不同的楼层,唯一相同之处都有电梯。从刘小兰不敢坐电梯之举,意味着她一个上午所找的6个部门都是靠扶着残腿一拐一拐地爬上又一拐一拐地爬下。这其中哪怕有个人给她打个电话教她坐一回电梯,她也就少走多少冤枉路少爬多少楼啊!
“花泪”回话道:现在的人都太自我太缺乏换位思考。你是残疾人又在做残疾人工作,自然感同身受。但我想,你天天面对残疾人,泪眼看泪人,岂不是超痛苦?要换了我,我可受不了。
曹一木听了一愕,心里像被触到什么不由得感慨起来:花泪,我当初也受不了这些,心里十分纠结,后来慢慢地习惯了也就想明白了。正因为这特殊的双重身份,我与残疾人情感同构,和他们好沟通些,也能理解健全人的一些“大意与粗心”。其实,自有人类出现,就有残疾人。有的人先天生下来就成了残疾人,有的人则是因为疾病、事故、战争等后天因素成了残疾人。由此,人除了有男人女人穷人富人之分外,还多了一种分类,那就是健全人和残疾人,这本是无可奈何无法选择之事。一个人最为痛苦的,不是当不了官发不了财成不了名,而是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没了或功能丧失了,成了残疾人。正因为如此,健全人天生有一种优越感,在他们眼里,残疾人是“怜悯、痛苦、弱者”的代名词,与生俱来就带着一种原罪,莫名地遭轻视歧视甚至鄙视。殊不知,健全人与残疾人只隔着一张纸,就像天才和疯子只隔着一张纸一样,二者是很容易转变的。残疾,其实是人的另一半世界,有隐性的也有显性的,一些人是生理上的残疾,一些人是精神上的残疾。健全人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归根结底也是对待自己的态度。
草木,你这样说,让我明白了一些。当人类拥有先进的工具和武器能征服一切后,他在地球上就不再有天敌,从此,人类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因而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拼搏排斥厮杀,为名为利劳心劳力,苦得不亦乐乎。很少有人居安思危,思考在名利后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健康人的生命。人一旦失去健康失去了生命,就像电脑突然失去电源,再美丽的图像再复杂的程序霎时间全部化为虚有。
花泪,你说得真好。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能洞若观火,看穿人的表象。他在《道德经》上写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译成大白话就是,缤纷的色彩使人眼睛昏花,变幻的音响使人耳朵发聋,丰腴的美食使人口味败坏,驰骋打猎令人心意狂荡,珍奇财宝令人行为不轨。在我看来,人无论是否残疾,都是活生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珍惜。说到对生命的尊重,我喜欢老子的另外几句话:夫大王亶父,可望能尊生矣。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意思是说,大王亶父可以说是最能看重生命的了。能够珍视生命的人,即使富贵也不会贪恋俸养而伤害身体,即使贫贱同样也不会追逐私利而拘累形躯。
“花泪”:啧啧,真服了你。想不到你掉起书袋来,也一套一套的。
曹一木:马虎马虎,彼此彼此。
二
曹一木原本把金钱看得很淡,但刘小兰的到来忽然让他感到有钱真好,如果自己有大把大把的钱,就可以慷慨地帮助像刘小兰那样贫困的残疾人。有时看着他们带着无奈空洞的眼神到残联求助,他心里特难受。残疾人没有工作找不到钱,就意味着失去自信失去尊严。然而,当天下午,牛腩的出现,又让曹一木的想法有所动摇。
眼前的牛腩像一个酒肉和尚,圆溜溜的光脑袋红彤彤的油面孔满嘴喷着酒气,一件已不见颜色的衬衣上扣不搭下扣地半吊着,露出里面一截白白的肚腩。牛腩整条左腿没了,靠一个倒三角木拐杖撑着。他进门放着椅子不坐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啪”的一声把拐杖重重放倒在地上。但凡使用拐杖的残疾人都是视拐杖为自己的腿,每坐下后会小心地把拐杖放好,唯有他例外。曹一木劝道:这里是办公室,你还是坐椅子吧。说着,弯下腰来扶牛腩。谁知牛腩身子特沉,曹一木腿脚也不便,大半天才把他扶起来坐好,随后又把那可怜的拐杖也扶起。
未等问话,牛腩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成一团的体检表乱舞着说:没法活了,没法活了,还不如一死了之!
半年前,曹一木第一次接待牛腩时他也是如此口吻一上来也是要死要活的。当时,曹一木刚负责这信访工作,听说牛腩嚷着要自杀紧张得不得了,生怕他弄出什么大事来,忙好生劝慰。牛腩一下找到了倾诉对象,拉着曹一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大倒特倒苦水。
牛腩原是一个拉煤的货车司机,老婆超漂亮超温柔(这是牛腩的原话),唯一不足就是结婚多年没有给他生下一儿半女。小两口商量着到福利院抱养了一个模样俊俏的小男孩,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谁知前年冬天,牛腩因酒后驾车酿成重大车祸,不仅把一个路人撞成植物人,自己也失去了一条左腿,最后倾家荡产还不够赔给伤者。从此,牛腩成天借酒消愁,老婆实在受不了,在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带着5岁的儿子偷偷跟一个煤老板跑了,再也不见踪影。
曹一木陪着掉了几滴眼泪,送牛腩出门时还塞给他100元。同事们知道后都笑曹一木心太软,因为牛腩像祥林嫂似的已把这故事讲了N遍,大家都耳熟能详了。为牛腩的事,残联可出了不少力,与民政部门协商为他办了低保,还资助几千元让他摆个摊卖点日杂,谁知那本钱全让他换酒喝了。同事们讲了牛腩的许多笑话数落了他的许多不是,归根结底一句话:烂泥巴糊不上壁。曹一木不以为然,相信牛腩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因为他有初中文化,也不算太残,扶持一下或许可以振作起来,便把他列为市肢残人协会重点帮扶对象。
那天,曹一木约上肢协的几名负责人提着油啊米的登门来看望牛腩。他们七拐八弯地寻到牛腩的家却是铁将军把门。这是一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瓦面平房,透过没有玻璃的木窗,只见里面废品店似的乱成一团,床上被子不叠蚊帐不挂,床下几只鞋子打着乱卦,一根粗长铁线横穿房间,上面挂着几件不知是洗还是没洗的衣服。靠窗的一角,摆了张歪了一条腿的小圆桌,乱堆着三五个没洗的菜盆饭碗爬满了黑苍蝇。更刺眼的是,桌子下面东倒西歪着十几个空酒瓶,一股股异味熏得让人掩鼻。
邻居见几个残疾人来慰问牛腩感到诧异,怪笑着说:今天发饷,牛腩不在家,喂鸡去了。喂鸡?曹一木有些纳闷。那边传来爆笑声:不是喂小鸡,是喂发廊里的“大鸡”。
问了几个人,曹一木这才弄明白,牛腩每月靠200元低保费为生,每当发低保费那天,他都要到发廊里去泡泡。几个肢协负责人一听,抱怨道:残疾人这么多,怎么能选牛腩这样的人来扶持?曹一木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当晚十二点多,曹一木接到牛腩的电话,那边是断点续传的醉话,试图在解释着自己的荒唐,老婆跑了,大半年没碰女人啦,难道天天“打飞机”不成?低保只解决肚子的温饱,可“小弟弟”的温饱谁解决?曹一木听了他的话恨得直咬牙:你失去左腿丢了老婆孩子是你自作自受,没人欠你的。你有手有脚可以去工作自食其力,将来还可以娶老婆,谁像你拿着低保还嫖的?牛腩一再解释:我没嫖,打打波而已。我实在是太无聊太孤独太痛苦了,如果我有一份工作就不会这样了。
曹一木决定不理他。谁知他经常半夜三更喝醉酒后打来电话,曹一木被吵得不得安生,干脆关掉手机。
虽然是恨铁不成钢,但牛腩毕竟是残疾人。曹一木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便张罗着帮牛腩找工作,先是安排他到电子厂组装电器。可是没干半个月,他因跟管理人员打架,被炒了鱿鱼;随即安排他到一家仓库当门卫,半夜三更他喝得烂醉,仓库门大打开,被老板逮了个正着,当即被开了。折腾了四五次,牛腩工作没好好干,坏名声倒出去了,弄得谁也不敢要他。牛腩每次清醒后又是检讨又是忏悔,甚至还抽自己的嘴巴。曹一木百般无奈,还是原谅了他,看能否到外地给他找份工作。
上个月一家深圳的制药厂来青州招残疾人,牛腩去应聘,面试通过了,只差做个体检就能上班。此时,曹一木见牛腩挥着体检表说没法活了,便猜到体检出了问题。
接过牛腩的体检表一看,他的肝功能果然呈阳性。但曹一木还是好言解释:你只是乙肝病毒携带者,并非乙肝。谁知牛腩像抽风似的又哭又闹:没用的,没用的!药厂明说不要我了。我白白花了几十元体验竟是这种结果。我现在不是一无所有了,我有病毒了。曹一木斥责道:你一个大男人哭什么?体检费我帮你出,工作还可以继续找。别动不动说不想活了!说着,掏出80元钱,递给他。牛腩接过钱,一把塞入口袋,抹着眼泪说:曹哥,你是好人,我不烦你了。请看今晚的《民生900》。再见了,永别了。说完,他挣扎着站起来,拄着拐杖准备出门。
《民生900》是青州电视台的民生新闻节目,每晚9点播出。曹一木听出其话里有话,连劝他不要做傻事,再坐一会儿,工作的事好商量。牛腩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头也不回地出了门。
三
听完牛腩的故事,“花泪”紧张起来:草木,牛腩真的会自杀吗?你为什么不拦着?曹一木:牛腩是块牛皮糖,像他这种人绝对不会去自杀的。何况他要走,想拦也拦不住。我对他算是仁至义尽了。“花泪”:现在正好是晚上9点,你快打开电视看看,看会发生什么?曹一木瞟了下电脑上的时钟,果然是9点。他半信半疑打开电视,调到《民生900》频道,一看头条新闻,真给吓了一跳。
电视画面上,四台红色消防车齐集桥下,一架云梯往上延伸,谈判人员站在云梯上与跳桥者对话。多名消防员在桥面上紧张地在铺着海绵气垫,旁边站满了围观的市民和车辆。由于桥太高,看不清跳桥者面孔,只看到小小的人影晃动。电视画外音说,今晚8时,有个不明身份的人爬到青州新修建的青河大桥桥拱最高处,嚷着要跳桥自杀。
曹一木心里“噔”的一声:不会是牛腩吧?
此时,桥上飘落下一张跳桥者扔下的证件,电视给了一个特写镜头,是一张墨绿色的残疾人证。身材小巧的电视台女记者拾起残疾人证细看了一会,介绍说:跳桥者叫牛腩,是个残疾人。据他刚才给谈判人说,老婆弃他而去,工作找不到,家里一贫如洗,最近体检检出身上有病毒,又没钱治,不如一跳了之。现在,桥上风很大,这个叫牛腩的残疾人已在桥拱上面呆了一个多小时,随时有跳下来的可能。
青河大桥是青州标志性大桥,桥面离桥拱顶处有30米高,人要爬到最高点,得沿着桥架上一条小小的铁梯向上攀登。河风猎猎,曹一木真不知道牛腩是怎样靠一条腿爬上去的。他拨牛腩的手机不通,只能干着急。
你快去救人啊。“花泪”闻之急催。曹一木顾不得换衣服,抓起手机就冲出门,心里嘀咕着:牛腩这回你可是玩大了。不过他还是坚信牛腩是怕死之人,绝不会轻意跳下来的。
一路风好大,刮得脸有些痛,曹一木驾着“蓝精灵”救火似的赶到青河大桥。整个现场围得水泄不通,桥两边堵了一长串的大小车辆,一些司机在不耐烦地按着喇叭。曹一木好不容易挤入人群,掏出工作证向现场指挥官说明来意,指挥官打量着这一动就满身是汗的残疾人确实是残联干部后,像见到救星似的,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正准备找残联啊,你认识上面的人,这就更好。你上去劝劝他,或许他会听你的。
曹一木眯着眼往上看,见牛腩骑在桥拱上的一条横梁上,恍惚中似乎整座桥在动。曹一木摆着手说:不行,我怕高,一到上面就头晕,你把高音喇叭给我,我在下面喊吧。指挥官说,没用,下面声音太小,我找两个战士护送你上去。他也不管曹一木是否同意,两个瘦黑的战士上来,一个把一顶白色的消防头盔戴在他头上,另一个携着他就往消防车的平台上送。一个有浓厚湖南腔的战士介绍说,先生别怕,这是我大队新购买的登高平台消防车,云架升直了有32米高,有我俩在后面护着你,你就当看风景好了。这车本是用于高层救火的,想不到先救上人了。先生,你真幸运啊,我们队长都还没坐过,你就坐上了。
说话间,消防车伸出长臂,托着他们徐徐向上伸,开始还平移着向上,后来则呈75度角向上延伸,曹一木只觉得两耳生风,下面的人越来越小,手不禁紧紧抓着栏杆。两个战士一左一右把他夹在中间。漫长的两分钟过去,平台停住了,牛腩那张苍白的脸呈现在眼前,他两只手紧抓在一条竖杆上,两条腿在横梁上紧扣成一个O形。
你们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们看。牛腩见消防车的云梯上又来了人,歇斯底里地喊着。听到牛腩的喊叫声,曹一木心里的惊恐消失了,他清楚自己是来干什么的。牛腩,我是曹一木。牛腩看清果然是曹一木,不自然地笑笑:曹同志,你来干什么?来看你跳桥啊。跳桥有什么好看的?我已一无所有,还不如一死了之。我看你不是想死吧,否则你也不会这么辛苦爬这么高来自杀。你只要在桥面上纵身一跳,也就一了百了啦。曹一木,你是盼我死啊,上这么高来竟说这样的话!我不说这样的话又该说什么话啦?难道我该说求求你别跳了,你有什么条件都可答应你,是吗?这些话,刚才警官都说过了,居委会的同志也答应给你办理低保、安排一间廉租房,还可以推荐你去看地下车库。可这一切你都不答应。非得要我冒险到这么高处来看你表演跳桥秀。曹一木,你以为我不敢跳吗?我跳给你看。牛腩,你别吓我,你看青河水黑沉沉的,跳下去人就像一片破树叶眨眼间没了踪影。你自杀是你自愿的,怨不得人,没人会为你哭。除了明天报纸上发一条新闻,说有个残疾人自杀跳桥身亡,供别人茶余饭后议论几句外,你什么都不是,因为谁也不欠你的。你是残疾人,我也是残疾人,除了残疾人,我们还是人,是人就得活下去,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曹一木,你是作家,我不和你比,你有工作有房子有父母,我什么都没有。死了一了百了。牛腩,我知道你不想死,只是想闹出点动静来。你死了,真的是一了百了吗?我看不是,就像满城的灯火,依然美丽灿烂,依然有新的希望。如果你听我的,就跟我下去,你该有的始终会有的。曹一木对着牛腩嬉笑怒骂了一番,说得唇干口燥,最后看牛腩还是无动于衷,他一咬牙,对身边的战士说:别管他,我们下去吧。
当云梯缓缓启动时,牛腩着急地叫道:等一等。曹一木白了他一眼:怎么啦?咱们明天早上见。牛腩有些嘶哑地喊道:你不是叫我下去吗?我两手两脚都麻了,肚子咕噜着叫了,全身一点力气都没了,叫我怎么下去?你早说不就得了,你等着吧。曹一木给两个战士使了一个眼色。战士马上向下面报告。
云梯缓缓地靠近牛腩。为防止意外,一个战士熟练地用安全绳套住牛腩的腰,然后把他接上平台。牛腩一上平台就瘫在地上,有气没力地说:曹哥,你再不来救我,我手脚就没力抓不稳了,不想跳也会被风刮下来了。曹一木无语,真想上前扇他两巴掌。
生气归生气,牛腩没死,毕竟是值得欣慰的事。等派出所和居委会的人把牛腩接走后,曹一木这才一身轻松地回到家里,在网上向“花泪”报平安。
“花泪”说:我这里收看不到青州的电视,真为你们着急啊。曹一木说:想想我也有点后怕。好在我待牛腩不薄。万一他心存不满,在电视上说是残联不管他死活逼他跳桥的,我就玩完了。那你为什么在上面又劝他往下跳呢?我了解过,上个月牛腩跑到省残联也表演过一次跳楼秀,结果省残联给了他几百元后,他便下来了。因此,他这次跳桥,无非是想吸引警察和媒体记者,制造轰动,达到要钱要物的目的。警察会拘留他吗?应该不会,教育一番做个笔录就会放走的。他这样的人,连警察也怕。我是仗着自己是残疾人,才敢用激将法的。他也是等我来,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两人又聊了一会,都不知再说什么好,便挂了。留下曹一木独自守在电脑前发呆。毕竟刚才跟着牛腩在生死边沿走了一回,想想真是后怕,如果牛腩刚才一不留神,手一松,便真的会自由落体,掉进河里,转眼就成泡沫。生命再卑微,也是一个生命啊。人们通常会为一朵鲜花的凋谢、一个小鸟的死去而伤感而流泪。可是对于一个鲜活的人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人的死去,会产生什么感情呢?或许,我们在电视上看多了太多的灾难性新闻,每天全世界有多少人因天灾因战争因骚乱因车祸因财色因名利因疾病因贫穷而死去,一个个变得麻木不仁了。谁也不会去想,当有一天死亡降临到自己头上,或者自己被全世界所围观所抛弃,又该怎么办?
夜阑人静,曹一木久久难眠,徨然中,敲下一段文字:
生命
生命是在不可选择中诞生的,交织着暴雨与烈日。
尾随一种水声的诱惑,你拾起了夸夫失落的桃杖,好重。是谁在呼唤?这山系撑起的万重云涛,正酝酿着罡风的前奏。旷野的苍茫已失去了记忆,不用回头,该走的是你。躁动的灵肉,饥渴的苦难,旋转的力与美,证明只有你是活的。
虽然你并不高贵,但也不卑贱,原野中你是一尊流动的雕像,你有短劲矫健的线条,挥洒自如地勾画着你火的个性。这是一片升腾的野火,动荡着诗的激情歌的快乐光的旋涡,美丽,热烈,构成某种神秘。拥有生命便拥有一切,你不必再有其他奢求。
是谁在呼唤?千里孤坟边,有一棵青青的橡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