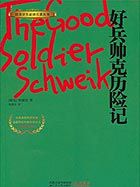然而,我们太年轻了,我们高兴得太早了!古人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在我们喜滋滋拉来货柜准备搬进门面时,索伯玉的姐夫伍添丁和他的亲家伍木川,风风火火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父子俩堵在了商店门口。伍木川对着我们大喊大叫:你们大家都来看啊,这三个有班不上、好吃懒做的狗男女,他们看着我这幢三层楼房,想要侵夺我们的个人私有房产呀!你们大家来为我评评理呀,天底下有这些没有良心的人呀!我就是穷死饿死,也不会把我的门面让给这三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啊!……伍木川连哭带喊,凄凄切切,这就招引许多过往行人和看客,只在几分钟内,门面就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我们三人一时变得非常难堪。一些不明就里的人,看见伍木川哭丧的样子,还表示深深的同情,于是有人谴责,有人声讨,有人起哄,场面一时失控。索伯玉看招架不住,辩解无辞,又是自家的亲家,又怕丢面子让大家看到他的熊样,便趁机偷偷地溜掉了。索伯玉一走,我和洪兰芬这两个“外人”就重现了前几天我们赶那家集体店的情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们俩人自然就没戏了。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只认一个理:产权是人家伍木川的,人家伍木川不同意把门面出租给你,你要强行搬进去,就是不讲道理,就是蛮横,就是霸占,大家众口一词地声讨谴责着我们,换句话说,大家是在主持正义。众人的唾沫能把我们淹死!
在道理一边倒的情况下,我和洪兰芬只好在伍木川父子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闹声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打道回府,把货柜运回,狼狈至极,丢人现眼,丢尽面颜。回来后我们要找索伯玉问清原委,另寻对策。然而一连三天,我们都找不到他。看来此时的索伯玉在受挫面前故意躲着我们。这时的索伯玉已成为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洪兰芬其实比我还要急,生怕他会出事。她到他家探听才知道索伯玉已跑到他们老祖宗的乡下葛岭的索姓亲戚家了。半个月都没再露面。这个时间,我的本家伍木川父子,见我们这边悄无声息,似乎明白经他们这一闹,我们已像霜打的茄子彻底蔫了。父子俩这时堂而皇之搬进门面,堂而皇之开起了青佛城第一家的个体食杂店,门号是“川丁食杂店”,父子各用一个字命名,意为这家商店父子共有。那五个字的书写不太规范,但从那楷书的字体我认出那是出自索伯玉的手笔。这时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我和洪兰芬实实在在当了一回二百五,即拿竹竿敲橄榄给人家拾。而拾者不是别人,正是索伯玉的姐姐一家人。这样的二百五,当得实在冤,实在让人感到倒了八辈霉!而我们所合伙做的那些原来准备大展宏图的货柜,最后只能各分得一个。我后来用它来做书柜,至今还留在那儿纪录着我们昔日曾有过、曾想过成为一代商人的梦想,但每逢我触碰到它们时,就会有一种壮志未酬般钻心的痛,成为一种伤逝和痛楚的纪念。我永远记住这次“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教训,也才第一次认识了索伯玉这个人。索伯玉对我们这次准备合伙经商的失败,他始终不敢面对,不敢正面向我和洪兰芬说清。究竟他有没有从中做了手脚,和他姐姐一家设下了局?看来只有天知道。但索伯玉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过了很长时间才告诉洪兰芬,如果那时我们没有遇到这些龃龉,一直合作,生意做到今天,我们一定都是青佛城第一批腰缠万贯的富翁。
这绝不是塞北雨过后才回南风。有相当的佐证来证明我说的话。索伯玉的姐夫伍添丁自从开始经营这家门面到今天,那门面已翻过几回新,三层的旧楼现已翻建成八层楼房。据说,伍添丁现在的总资产最少也有三千万。而原先的伍添丁是个狗咬都不响的人,现在居然成为青佛城烟酒干鲜店生意最大的老板。从某种意义来讲,是我们成全了他。这其中是我付出了时间,索伯玉付出了失去女友的代价,洪兰芬付出了女人的贞操。因为后来随着门面未能如愿的失败,索伯玉和洪兰芬之间的情爱似乎也不疾而终。洪兰芬是个很有个性和很有思想的女性,她认为索伯玉姐姐一家人窃取了我们所付出的心力和劳力的成果,索伯玉从中有没有和他姐夫一家人做了手脚,她始终表示存疑,因为伍添丁开店门号的毛笔字是索伯玉所书写的。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心里不言而喻。再说,倘若这个问题还不足说明索伯玉做局夺取了门面经营权给他姐夫开店,那么一个男子汉在最关键的时候当逃兵跑到乡下躲起来,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别人来收拾,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品?洪兰芬在合伙经商失败后,看破了索伯玉的手脚,觉得索伯玉这个人不太地道。起码,不是她当初认识的那个可以信任和依靠的索伯玉。洪兰芬开始后悔自己当初看错了人。然而,悔之不及。她已为他付出女人最珍贵的身体代价。当然她始终不知道在和索伯玉那一夜的相思林野合背后,在索伯玉身上发生的那种事。我自始至终没向她吐露过。因为那是索伯玉的个人隐私。虽然我们合作经商不成功,但索伯玉毕竟是我曾经有过密切来往的一个朋友。既然索伯玉敢把个人的隐私告诉我,我就有义务对他的隐私保密。但我能看出来,洪兰芬和索伯玉的一夜情,她只能算作是自己的一时冲动,她对索伯玉的那份热情慢慢减退以致最后疏远。也许他们之间各方面本来悬殊相差就太大,而男女一夜情在那时已算不得什么了。她自己也曾喜欢过索伯玉,就让它像一阵风吹走或一段春水流走吧。
六
常言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遭受这次挫折后,有谁再招呼要和我一起做生意,我都拱手拒绝。这并不是我经不起这种走麦城的失败。我们那次一个人也不够才损失五、六千元。问题是那在众目睽睽丢人现眼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它仿佛一颗毒瘤,长留在我的脑子里,恁你怎么赶都赶不掉。也使自己认识到我不是做生意那块料。那种想发商财的梦不是我这档人做的。我心静如水。又恢复原先的写作生活,我把几篇小说稿整理好寄给了几家文学杂志社,都获得了发表。这时那所氤氲着诡异气氛的索氏祖祠老屋刚好遭遇旧城改造,要拆建新楼盘,在和拆建方办理了拆房和补偿费后,加之生活来源不顺畅,我只得离开了青佛城,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单位那个该死的矿山重新开起我的铲车。不久我在矿区娶妻生子,一边开着铲车,一边偷空写点小说拿去发表挣点稿费贴补家用。日子虽然过得平淡无奇,但也其乐融融。
人啊,该认命时你就得认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一天,洪兰芬刚好有事路过我那里。我到了她下榻的矿山招待所,我作为东道主备了些小酒小菜和她细斟慢酌起来。我们在不经意间谈起了索伯玉。洪兰芬喝了一口干红葡萄酒后,把一口酒喷到窗外气愤地说:索伯玉这个短命的,这个做事有头无尾的家伙,我这辈子生来好像是欠他的。你可能不知道吧,前些时候我差点就被他害死!……
这时,这个已是有一个小孩的中年妇女,带着悲伤和愤怒的口吻,向我讲述了她和索伯玉后来又发生的一段经历。
原来,我们散伙后,她和索伯玉并没因此而散伙,他们毕竟有过那段感情。按照洪兰芬的话说:我们不可能像你那样说散就散。我和他毕竟是从一个工厂离职出来,并且是要出来跑单干的,是一个战壕上没战死的两个重伤员。是的,他们没有理由因一次小失败而分开。他们只有再合作下去。没了门面,生意照样可以做。于是在索伯玉的筹划下,他们又一起干起了那个时代刚开始经商很流行的方式:办皮包公司。他们向工商申办执照,刻了皮包公司的公章,印了许多空白合同,专为商家做中介的皮包生意。具体的操作方法是,将甲方的货物介绍给乙方,再介绍给丙方或丁方。从这种两头空又是两头转中赚取好处费和利润。他们搞了一二年,也真的赚了一些钱。洪兰芬回忆说,我们那时每人手头大约赚有八万元,她原来是准备赚到十万元后就和索伯玉结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