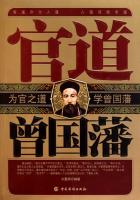从家本位的经济制度过渡到社会本位的经济制度,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制度演进;当然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只有通过这种制度演进,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新性”出现。而说到“演进”二字,可以说冯友兰这一代的学者无不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巨大影响。这里我们仅举一段冯氏说过的话足矣:“在清末,达尔文,赫胥黎的《天演论》,初传到中国来,一般人都以为这是一个‘公例’,所谓‘天演公例’。……所谓‘天演公例’,是就事物之天然状态说者。就人说,所谓文明,本是人对于其所在之天然状态之改变。如果事实上有在天然状态中之人,则此种人是野蛮底。”鲍霁主编:《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页。冯友兰确实觉察到:若从文明自身的演进过程看,天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乃具有一种发展的必然性逻辑在其中;而在此中发掘制度的重要性,本可从世界文明史的实例中拈出。故冯氏特举出英美及西欧产业革命一例,以见出经济制度之先进性与重要性。冯友兰还觉察到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必将要深入到农业文明中:“产业革命,亦称工业革命。有许多人对于所谓工业革命,望文生义,以为此所谓工业是与农业,商业,对立者,工业革命只是在工业方面底革命,对于农业等,并无关系。这是完全错误底。所谓工业革命,不但在工业中,即在农业中亦有之。此所谓革命者,即以一个生产方法,替代另一个生产方法。”鲍霁主编:《冯友兰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91—192页。这里,“替代”一词极为关键;替代须通过制度演进过程来达到,而制度演进及转变的发生总是处于某一过渡时期中的。
冯氏已然注意到“过渡时代”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制度演进关联起来,这一思维取向的表征,实际上是冯氏此论最具魅力处。70多年前,他就一再告知我们中国处于一个过渡时代与转变时代:“中国现在所经之时代,是生产家庭化底文化,转入生产社会化底文化之时代,是一个转变时代,是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在这个时代底人,有特别吃亏的地方。在比较固定底社会中,如果它所行者是那一种文化,则它自有一套制度,在各方面都是一致底。但在一个过渡时代的社会中,在此方面,它已用这一套制度,在另一方面,它还用那一套制度,于是此社会中之人,学会了这一套制度者,在那一套制度里,即到处碰钉子。”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4页。实质上,这说的是过渡时代中多种制度交叉碰撞所带来的困局;然而不能不看到的是,这种多种制度的同时存在,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在这个过渡时代中,我们可亲眼看见许多不同底制度,不同底行为标准,同时存在。……因此,我们的行为,可得到很大底自由。”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5页。当然,趁着这个“方便”的自由,也“有些‘混水摸鱼’、‘趁火打劫’底人,利用这个特别方便之门行事,一时照着这一套社会制度,一时又照着那一套制度。而其所照着者,都是合乎他自己的利益底。……在这个过渡时代,特别有一种做不道德底事的机会,如以上所说者,此则是事实。”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5页。真是一针见血!冯氏所言,直到我们今天仍常所见——过度的利益诉求,何其坚深而不可拔。今日中国,仍未超越于这一过渡时代。冯友兰坚信:“我们是提倡所谓现代代底。但在基本道德这一方面是无所谓现代化底,或不现代化底。有些人常把某种社会制度,与基本道德混为一谈,这是很不对底。某种社会制度是可变底,而基本道德则是不可变底。”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72页。然在笔者看来,过度的利益诉求,反衬出制度建构的重要性;而道德规范的可操作性照样须置入制度构架内,才有更大的合理性。中国传统文化却早已习惯于将道德与法制分成两橛。无论如何,冯友兰也洞见了过渡时期中败德者对不同制度采用为我所用的弊病所在。
冯友兰还进一步深入到制度与文化的关系中,实际上,制度的演进在深层次上也就是文化的演进。冯友兰用了一个“势”字,合乎新势,乃文化发展所需;反之,则成文化发展之阻碍。他说:“某种社会制度,在某种势下,本来是使文化可能所必需底。但于某种势有变时,某种社会制度,不但不是文化可能所必需,而反成了文化进步的阻碍。对于文化的进步说,如某种社会制度,成了阻碍,则对于个人的自由说,某种社会制度,即成了束缚。所谓把人从某种社会制度中解放出来者,即解除此种社会制度的束缚,而去其阻碍也。解除此种社会制度的束缚,并不是不要社会制度,而是要另一种制度。此种新社会制度,因其合乎新势,所以不是一种束缚、一种阻碍,而是文化可能所必需。”冯友兰:《新原人》,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09—110页。实际上,这里深涵着一种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在内。文化的演进方向总是有其价值取向的,当新的社会制度能够对应这一取向,也就是“合乎新势”时,正是这一文化发展取向之所需,也就是制度恰能对应于这一文化的价值内涵。冯友兰此中所谓“势”,恰好表征了时代的价值取向之所在。如其所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即是一时代在精神方面底风尚,人不知不觉地随着它走者。就其不知不觉说,这所谓精神及风尚,即是偶像;领导这些精神底人,即是偶像中底偶像。”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7页。应当说,冯友兰对时代“新势”是敏感的,在他那样的年代,他似乎较早地触碰了理论前沿的“自我”范畴,他向人们传达出这样的信息:“在近代底社会中,人已发现了‘自我’。”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97页。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对这一发现“自我”的文化有一个类型的界定。
冯友兰说:“若从类的观点,以看西洋文化,则我们可知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于此我们所要注意者,并不是一特殊底西洋文化,而是一种文化类型。……若从类的观点,以看中国文化,则我们亦可知我们近百年来所以到处吃亏者,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它是某种文化底。于此我们所要注意者,亦并不是一特殊底中国文化,而是某一种文化类型。”每一文化固然是特殊的,但我们从逻辑上则须从类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特殊事物。基于此,“所以近来近代文化或现代文化一名已渐取西洋文化之名而代之。从前人常说我们要西洋化,现在人常说我们要近代化或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可见,从类型上看,一为近代或现代的,一为中古的,其差别不言而喻。冯友兰称这一见地为很大的觉悟。而其所言“吃亏”的个中原由,亦正在于此。无怪乎冯友兰要强调制度层面的重要性了。
三、“中国近代化所经底步骤”——辛亥革命
我们已然看到冯友兰是如何从注重“新性”原理过渡到具体的制度层面,现在,我们将要看看冯友兰又是如何以特殊的个案来证实上述抽象到具体两个层面的合理性的。可想而知,对冯氏所处时代而言,最贴切而合乎逻辑的例子当然是辛亥革命。
将辛亥革命视为中国现代化的步骤,这当然显示了冯友兰的理论远见。他十分坚定地认为:“建立中华民国底辛亥革命,就一方面说,是中国近代化所经底步骤,就又一方面说,是自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就其是中国近代化所经底步骤说,这个革命是开来。就其是自明末清初以来汉人恢复运动的继续说,这个革命是继往。就这个革命对于以后底影响说,这个革命完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步骤。”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3页。口气的坚定,跃然纸上。同时,冯友兰还认识到辛亥革命之初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发展为后来的三民主义。值得一提的是,冯友兰还十分细致地注意到:“在清末的时候,卢梭的《民约论》一类底书,固然是为一般人所传诵或所暗中传诵,但更引起人的情感底,是明末遗民的著作。在这一类底著作中,有些兼有所谓提倡民权的意思是,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等书。这些书自然更是风行一时,或暗中风行一时。我并不认为,专靠这些书,即能引起清末底革命。不过在这些思想的流行上,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底革命的方向。”因而冯友兰断言:“辛亥革命有长久底、历史底背景。”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3—134页。冯友兰分明看到了黄宗羲提倡的民权在当时有多大的号召力。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谈到辛亥革命时,冯友兰还十分自然地联系到英美的议会政治,并由此而透视了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他如此说道:“普通民主国的议会政治,如英美所行者,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在某一阶段内所能行底一种制度。……一个社会行了这一种经济制度,虽不必行这一种政治制度,但如不行这一种经济制度,必不能行这一种政治制度。在不行这种经济制度底社会里,若有人主张行这种政治制度,其主张即真正是不合国情,其言论是空言无补。”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4—135页。不必多言,这里受到马克思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论的影响是至为明显的。从辛亥革命论中引申出的结论是如此的精彩:
所谓民主政治,即是政治的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化,必在经济社会化底社会中,才能行。冯友兰:《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35页。
可见,经济基础是必要的前提条件;有了经济社会化的因,才会有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的果。究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而从辛亥革命这一中国现代化必经步骤来透视这一原理,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果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