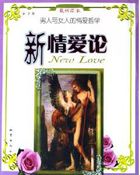然而在逻辑立论上,唐君毅始终是“以人文之概念涵摄宗教,而不赞成以宗教统制人文”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编“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这决定了他必然要将宗教精神及其文化作为人类文化需要之前提,从而在文化上肯定宗教之客观地位,他特别是从中国文化这一座标系来肯定其地位的。因此,“此一肯定,完成了中国文化之发展,显示出人文化成之极致;此与西洋未来文化将以宗教精神之再生,理想主义之发扬,救治人类物化之趋向,两相凑泊。正是人类文化大流,天造地设的自然汇合之方向所趋”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编“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实质上,唐君毅人文宗教观之所以要确立一个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视角,来观照整体的宗教文化及其精神。其中至为深刻的原因在他深以为儒家的生生观念及天人合德的精神,正可整治乃至拯救人类物化之趋向。他自信未来的宗教,必然是一种人文宗教观。
中国文化中天人合德的宗教道德智慧,是唐君毅人文宗教观的一个核心部分。他以儒家的道德形上学而得出:人的存在为一种“道德性与宗教性之存在”,并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中之宗教性成分,是中国伦理道德之内在精神生活上的根据。正是有了这一内在根据,使得“在中国,则宗教本不与政治及伦理道德分离。”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局1989年版,第15页。那么,如何理解他的宗教与伦理道德的不分离呢?在唐君毅看来,首先要注重两者“同来源于一本之文化”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局1989年版,第14页。。正是同一性的本源决定了中国民族之宗教性超越感情,及宗教与伦理道德之合一而不可分。
唐君毅注意到,要深入到更高的层次来把握这一观点,才能更好地解释它的合理性。于是,他以中国思想中最为内核的观念———天人合德,来逻辑地进行解说,如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就强调指出:“至于纯从中国人之人生道德伦理之实践方面说,则此中亦明涵有宗教性之超越感情。在中国人生道德思想中,大家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由古至今中国思想家所重视之天人合德、天人合一、天人不二、天人同体之观念。此中之所谓天之意义,自有各种之不同。在此一意义下,此天即指目所见之物质之天。然而此天之观念,在中国古代思想中,明指有人格之上帝。即在孔孟老庄思想中之天之意义,虽各有不同,然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他们所谓天之观念所指,初为超越现实的个人自我,与现实之人与人关系的。”显然,道德伦理的关系,被唐君毅视为是必然地涵有宗教的超越性意义的。由此,他强调:中国学术文化的实质性问题在,中国古代人对天之宗教信仰,如何贯注于后来思想家关于人的思想中,而成一天人合一之类思想的;从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宗教方面,又如何融和于后来之人生伦理道德方面及中国文化之其他方面。这一思维在他的儒家人文精神的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此儒家之教包涵宗教精神于其内,既承天道以极高明,而归极于立人道,以致广大,道中庸之人文精神所自生。故谓儒家是宗教者固非,而谓儒家反宗教、非宗教,无天无神无帝者尤非。儒家骨髓,实唯是上所谓“融宗教于人文,合天人之道而知其同为仁道,乃以人承天,而使人知人德可同于天德,人性即天命,而皆至善,于人之仁心与善性,见天心神性之所存,人至诚而皆可成圣如神如帝”之人文宗教也。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3页。
这段话中正式将“人文宗教”的范畴提出,这一范畴可看成是唐君毅“融宗教于人文”的哲学思想之结晶;他的整个宗教研究都未脱离“人文”观念。其意义在突出并强化了人的道德主体之地位,而且是在这样一个命题———人既是道德性又是宗教性的存在,得到强化的。对此命题的最终认识是:人能尽心知性而知天,存心养性而事天,故能承天道以极高明,儒家的至诚之道显然是一个必然的中介。
唐君毅认为,正是孔子的道德哲学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原始之宗教既经孔子之融化,乃本人德可齐于天之思想,再与庄子游于天地之思想相与合流;而渐有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之神仙思想。而后之佛学之所以为中国人所喜,亦因佛学始于不信超绝之梵天,而信人人皆可成佛,而如神,如梵天,如上帝。则中国以后道佛之宗教精神,亦孔子天人合德之思想之所开,人诚信天人合德,而人德可齐天,则人之敬圣贤之心,敬亲之心,亦可同于敬天之心。此即后来之宗教精神之所以于天帝崇拜之外,大重对圣贤祖先之崇拜之故。孔子信天敬祖,后人则敬孔子如天,而或忘单纯之天。”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57—58页。这里传达出一条十分重要的学术信息是“中国以后道佛之宗教精神,亦孔子天人合德之思想之所开”;实质上,孔子是自觉地把原始宗教的天道化为“仁”道。孔子教人此仁,是教人效法天之“四时行百物生”之德;天之道为无私,健行不息而有此四时行百物生,故人应当在最大程度上承之以立人道。同时,唐君毅又指出,世界上一些宗教家,皆重祈祷,而低级之祈祷又夹杂私求与私意,将偏私之心,注入于上帝,而使上帝成一偏私之上帝。如其求而不得,则生哀怨之辞,而孔子不重人对于天之祈求,故能“不怨天”。站在唐君毅的“融宗教于人文,合天人之道而知其同为仁道”的立场,显然孔子的人文宗教要深刻得多。所以唐君毅再三强调:孔子之教立,而人皆知修德而人德可同于天德。最终说来:“由孔孟之精神为枢纽,所形成之中国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说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湾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478页。
在天人合德之宗教智慧的思维框架中,唐君毅又试图把通于宗教精神的心性之学,放在一重要层次上,他以为不了解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又是中国思想中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的真正理由所在。他明确指出:“心性之学,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与外及人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通贯社会之伦理礼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见封祖盛编《当代新儒家》,北京,三联书局1989年版,第15页。在他看来,此心性之学的前提乃在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性之善与天命之善通。人能尽性成德,故能赞天地之化育。宋明儒就主张性理即天理,人之本心即天心,人之良知即天地万物之灵明。可见,在终极意义上,宗教精神可通于心性之学。唐君毅的结论是:孔孟思想,进于古代宗教者,不在其不信天,而唯在其知人之仁心仁性,即天心天道之直接显示,由是而重立人道,立人道即所以见天道。
唐君毅早已洞明儒家以道德代宗教的思想特质,一方面,他深信儒家的性善说,但另一方面他也察觉到儒家对人生负面因素未能真切地揭示出来。据此,他的人生论,充分体现出援佛入儒的特征;他肯认佛教视人生为空苦,是发人所未发。他在《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一文中以佛教为例指出:“佛教所最重之观念,实为苦之观念。”“佛教之兴起,其根本动机,明在拔苦,故四谛以苦谛为首。由欲拔苦,乃求苦之因于罪业之集结。而罪业之原始,则不在众生之有原罪,而在众生之依无明无知而起之妄执。故在佛教之精神中,苦之观念为凸出者。佛菩萨之大慈大悲,皆直接由悲悯众生之苦而引起。而苦之因,最后即在无明。故佛教之拔苦之道,重在得智慧,以自罪业解脱。”唐君毅:《宗教信仰与现代中国文化》,见张祥浩编“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49页。这一对佛教的总体认识涵括了佛教的兴起、佛教的核心理念乃至佛教的智慧、因果、解脱等系列观念。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唐氏的人文宗教观,始终是将历史观念与“现代中国文化”甚至“现代人类”联系起来的,读者只须多观其论文题目即可。
据此,唐君毅确信“佛教有一不可代替之价值与地位。”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编“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这种对佛教存在的价值的基本认识,乃基于其无可替代的地位;而这一界定是在其另一论文《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中得出的,可见同样是在现代价值取向下获得的结论。质言之,在唐氏眼中,佛教这一不可替代的地位,不仅被几千年的历史已然证明之,更因其观念的意义,对人类当下的生存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故唐君毅深以为:“佛教虽无神,仍当说为一宗教。人类思想中,重苦难、重智慧、亦重悲愿者,唯佛教能充类至尽。”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编“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3页。这个界定是十分到位的,人类有史以来,在所有宗教与其他思想派系中,只有佛教才最能承当人类的悲愿、苦难及智慧。然而我们要问:为何只有佛教才能对悲愿、苦难及智慧充类至尽呢?对此,唐君毅亦作了学理逻辑的解说,而这一解说的合理性则在宗教与道德的合一上。诚如其在批评西方宗教时所言,西方宗教终归于以道德为手段而成功利主义之说,“此皆不如佛家之由圆满善行而成佛圣,其圣体即无异神体,更利乐有情,穷未来际,加以普度者,其智慧之高,慈悲之深,更为能合宗教境与道德境为一者。”唐君毅:《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见刘梦溪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6页。显然,这种“合宗教境与道德境为一者”的解说,是一种基于学理逻辑的深层解说,是为寻求佛教无可替代之价值地位的逻辑基点。唐先生在其最有学术价值的那部《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中,充量地展显了他的宗教情结,而此情结多基于他对佛教的认识;然而,唐先生是个真正的哲学家,无论对宗教、文化、哲学,他的论述都可见出价值与学理的统一,这是唐先生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最大特点,这一特点导致他对佛教的“超越性”有极其深刻的认识:“然在佛教中,则一方深切认识一切众生之苦痛之可悯,然却又不直接去求一超现实之神,助人拔苦,乃进而超越此求神之心之本身,以透入苦之原——即众生之妄执,以拔苦。而此智慧之透入苦之原,即智慧之穿过苦痛,而超越苦,以求绝苦之原。此智慧能超越苦,而求根绝之原,便使在佛家之思想中,苦与苦之超越与根绝之观念,同时特为凸出。”唐君毅:《宗教精神与现代人类》,见张祥浩编“唐君毅新儒学论著辑要”:《文化意识宇宙的探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50页。必须强调的是,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层面的“超越”,一是超越“神”;二是“超越此求神之心之本身”,达到了超越求神之心的境界,才是佛教智慧的核心价值所在。唐氏这一论述亦可见出其慧根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