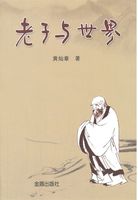问题在我们前面所指出过的钱穆曾将人文演进本身亦视作自然演进,这就需要一个更为根本的逻辑前提的保证,即人类理智与情感等心灵活动之扩大,亦属自然。钱穆已然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何能界定心灵活动的扩大是自然的呢?的确,钱穆曾断言:天地万物与我一体亦因于人的心灵活动之扩大。这不过是钱穆一贯肯认的人类文化与自然的合一之终极理想。然其途径则须以人心去弥纶宇宙,融彻万物。这里的心物问题,最终是人文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钱穆的杰出之处,不仅在总体上指出了人文之进化,未脱离“自然之大化”;还以辩证眼光洞察并以中国文化的特有方式指出了人化自然(“人文化之自然”见于《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社会学》)与自然人化(“自然之人文化”见于《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社会学》,“自然又须在人文中发展而完成”见于《双溪独语》)的逻辑关系。如《双溪独语·篇二十二》即指出:“今日凡与人类切身相关之自然界,多已经人类心灵创造,而成为人文化的自然,也可谓乃是符合于人类理想之自然。……原始自然,并不曾限制人类心灵之自有其理想,而使自然日益接近于人文化。”这段极为重要的论述中已经出现了“人文化的自然”与“自然近于人文化”的命题,可见钱穆是立于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倡言其人文自然互涵说的。如其所说:“由自然人生演进到社会人生,而在社会人生内依然涵有自然人生。……精神人生……涵蕴有物质人生。”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3页。正是这种互涵说,合理地解决了何以在有了人类社会历史以来,人们所面对的自然也就涵有人文因素了;而人文领域虽不断演进,也仍有自然基因之作用。所以人类心灵活动之扩大,既是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自然展演结果,也是天地万物与我同为一体(人化自然)的终极原因。易传“人文化成”的基本精神,仍在这里发挥了极大作用。“人文化的自然”作为钱穆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还见于他的一篇重要论文《文化三阶层》中:“几十万年代的人类精神之不断贯注,不断经营,不断改造,不断要求,而始形成此刻之所谓自然。这早已是人文化的自然,而非未经人文洗练以前之真自然。一切物世界里面,早有人类心世界之融入。”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7页。这里另须提及的是,钱穆正是在“人文化的自然”命题基础上作出其文化三层次之划分的,它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被大陆有眼光的学者所借鉴,这无庸赘述。此处我们仍要强调的是,文化历史之演进,一方面本有自然之基因;另方面,也有脱离自然(规律)轨道之可能。钱穆极为担忧那种人文社会历史愈发展,距离自然愈远的状况。他深心告诫说:“文化远离了自然,则此文化必渐趋枯萎。”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5页。因而,现代人必须懂得人类“从自然中产出文化来……然而文化终必亲依自然。”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7页。钱穆还相当敏锐地觉察到,自然可以不要文化,但文化却万万不能不要自然。这就是社会文化历史的规律所在。在人文演进的社会历史发展中,人们必须保持一种健康心态:“只有上述的一个心态,那是人文和自然之交点。人类开始从这点上游离自然而走上文化的路。我们要文化常健旺,少病痛,要使个人人生常感到自在舒适,少受捆缚,只有时时回复到这一心态上再来吸取外面大自然的精英。”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2页。这种别有意味的“交点心态”说,无非是要让人们更为深刻地理解并丝毫不能懈怠地提醒自己:人类社会历史进步的源头究竟何在。
钱穆用诸多的范畴来阐述社会历史文化的演进,如“历史演进”、“传统之演进”、“人文社会演进”、“儒学演进”、“人生演进”、“文化演进”等等,显然,这些都是“人文演进”基础上演变并以人文演进这一主线贯穿的。“演进”一词,深涵着“生命”之活力。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钱穆的显著特征在于他对历史所富有的“生命感”,所以他的文献中常常出现“历史生命”、“文化生命”之类的概念。对于历史,他甚至强调到这种地步:“历史乃是一种生命之学。”钱穆:《史学导言》,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39页。这与前面所述的人文本位观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因为钱穆更看重的是历史演进过程中的生命,只有活生生的人才是维持历史动态演进的根本保证,历史事件是其次的,背后支撑起所有事件的是生命;而且生命的积累与延续使历史社会文化得到延展。所以历史时间概念与科学时间概念有所不同,因为历史时间是整体生命的时间。钱穆的这一理解也是独特的:“人文科学里的时间,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过去穿过现在而迳向将来,它是一以贯之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力量,就叫做人生。这样的人生才成了历史。历史是一种把握我们生命的学问,是认识我们生命的学问。”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6页。这里所传达出的“人生”概念,是钱穆着力于“群体”生命而得出的有深度意义的概念,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生学与人生观,而且他的人生概念还密切关联着社会历史文化。
当然,以钱穆那种充满智慧的历史哲学之整体眼光,不仅要透视到生命、人生等与社会历史相关的范畴,还必然要透入“民族”文化历史演进中变化与持续的辩证关系及其价值范畴,因其毕竟是从整体人文演进的视角来看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由此他认为:“没有民族,就不可能有文化,不可能有历史。同时,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也不可能有民族。个人的自然生命,有它自然的限度,然而民族文化历史的生命,则可以无限持久。凡属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必然有它两种特征:一是变化,一是持续。……我们的文化生命,则在持续中有变化,在变化中有持续,与自然现象绝不同。讲历史,便要在持续中了解其变化,在变化中把握其持续。所以讲历史应该注重此两点:一在求其变,一在求其久。我们一定要同时把握这两个精神,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精神。所以说‘鉴古知今’,‘究往穷来’,这才是史学的精神。史学是一种生命之学,研究文化生命,历史生命,该注意其长时间持续中之不断的变化,与不断的翻新。要在永恒中有日新万变,又要在日新万变中认识其永恒持续的精神,这即是人生文化最高意义和最高价值之所在。”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7—8页。只有以一种真正的“人文演进”观来观照社会历史与文化,才能得出这种极其深刻而联贯的既讲求“变化”,又讲求“持续”的“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之结论。这里我们有必要提醒的是,钱穆仅在这短短的一段话中,就已多次运用历史生命与文化生命这类的范畴了。这种颇具特色的人文史学观,足以证明钱穆已达到了一种高度的历史意识与人文意识的统一,其连接点无疑是人文演进这一核心理念。
这里,我们还须强调的是,钱穆正是以“人文化成”的视角与中国文化的特有方式,洞察到“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的规律,他的辩证眼光已暗合于西方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这一学说,以钱穆的独特表征:“即人文之自然化,自然之人文化。”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4年版,第208页。相对于现今的人文世界,这两个命题是极为贴切的。钱穆以《中庸》的“明”“诚”关系作一解说:“于自然中化育出人文,中庸谓之‘自诚明’。人类有此智慧,乃能自主自立,自动自发,人文日进,然终不能违反自然,而仍必以回归自然为其极则,中庸谓之‘自明诚’。”钱穆:《晚学盲言》(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这段极为重要的传统式论述已经包含了与前类同的“人文化的自然”与“自然近于人文化”的深意,可见钱穆是立于一个坚实的思想基础上倡言“人化自然”与“自然人化”理念的,当然,钱穆的洞见同时是中国文化重视道德人心之深厚底蕴所化育出的一种眼光,故其每每着力倡导:“人心境界愈高,人心能力愈大。”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305页。看来,钱穆自称“我是一个文化乐观论者”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226页。是有理由的,它不仅基于对中国文化的自信之上,显然还立于他所建树的“人文演进”观对自然——人文及社会历史的逻辑贯通之上。
由人文演进理念所达致的最终境界——天人合一观
钱穆天人合一观的基本特色是建基于人文演进的自然人文同体观,落实于人生真理与宇宙真理的合一。由于其涉及面之广与理解力之深,更由于他阐说的独特性与创发性,我所不得不从更宽阔的视角来切入。
钱穆最具独创的地方就体现在他对原初浑沌的天人合一与人文演进中逐步深化而达到的天人合一,以中国思想中的“唯道论”所作的解说。照他的看法,“中国思想不妨称为唯道论”,“道既是自然的,常然的。同时也是当然的,必然的”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5页。在原始意义上,道就是自然之道;而所谓当然、必然,则只要是人文演进中合于此自然、常然的道,那就无疑会成为当然、必然之道了。但原初意义上“那些道,各照各道,互不相碍……如大马路上车水马龙,各走各路,所以说,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鸢飞鱼跃,是形容那活泼泼的大自然之全部的自由”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页。所谓“大自然之全部的自由”,当然是原初自然之道意义所显现的自由。然而只有明人文意义上的自然乃至必然之道,才能有“无入而不自得”的自由与合理性。如钱穆《双溪独语》中对“儒家制礼,斟情酌理,合乎自然”之合理性,就体现出相当深刻的理解。他以为全部人文演进之目标就在“人文大道与自然大道之合一”钱穆:《晚学盲言》(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61页。的天人合一境界上。而且,晚年的他还在《双溪独语》和《晚学盲言》中述说过这样一种理念:人文最高演进,即是自然之最高可能,此曰天人合一。
人文演进何以能导致最高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境界,这是钱穆要回答的关键问题。这里,我们又须暂回到与生俱来出于自然的“人心”上,因为钱穆曾以其完美的圆圈图象与理论阐发的结合,表征了“人心是人文与自然的接榫处”。他还在《民族与文化》一书中指出:“人心与生俱来,其大原出自天,故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则达于天人合一。”所谓大原出自天,当然是出自自然,然而与生俱来的而又出自自然的“人心”,并不妨碍其通过人文修养之终极造诣而与天合一。这是儒家最高明的地方。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儒家传统,在长达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将天人合一作为其终极理想,这是有着极其深厚的农业文明之思想基础的。钱穆对此多有论述,此不赘言。这里仍须强调的是钱穆之所以要视“文化史是一部人心演进史,”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305页。正因为人心在自然到人文之演进过程中,本身正是“人文与自然的接榫处”(接榫一说见于《中国文化丛谈》与《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略论中国心理学》),而事实上没有这一接榫处,也就谈不上“人文演进”了。这是钱穆人文思想中极为精微的地方,不可轻易漏过。因为钱穆以为,归根到底,由生命界演化出心灵界,惟演变到人心才最灵,才到达顶点。当然这不是说万物无灵,惟人有灵,而是说万物各有灵,人则为万物中之最灵。最为重要的是:“天人合一,即合在此灵之上。”至此,我们当知钱穆在根本上是要以天人的“一”,由人心之灵来“合”成,这显然和原初浑沌的合一有完全不同的境界,原因当然是有了“人文演进”的进化过程。天人物我内外的融和合一,枢纽竟在一心之灵!钱穆描画的圆圈图像,其最后最内一圈之圆心,即为最成熟而最富代表性的人心。因而它是可弥纶宇宙、融沏万物并且能以最精微的方式上通最广大的最先、最外一圈(天)。“上通”才能合一,然而“通”则有赖人之修养:“人人皆可为圣人,即是人人皆可凭其道德修养而上达于天人合一之境界。”[7][P134]这也就是钱穆反复论述的成就理想人格,才可上达天德。可见在人文演进过程中,真正的天人合一境界还要靠人格来成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