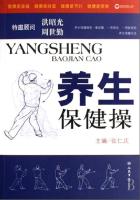博览会之后,收到了很多媒体的邀请,大多是做一些专访,以冯以文弟子的名义。
我挑了一些知名度比较高的,准备上电视台或者接受记者的采访。
采访的内容无非是一些很笼统的问题,比如说你是如何战胜无法被人赏识的痛苦,如何坚持下来最终获得胜利。
虽然不是我想去的,但却是万万不能不去的。
冯以文说:“这只是起点,让众人知晓你,接触你的起点,日后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即便再不愿意,只有接受,对你的帮助会很大。”
对于他的建议,我一向尊重,10多个媒体尽可能地都去。
一段时间内,电视里荧幕上,冯以文弟子的新闻铺天盖地地下来,微博的V号几天内连续涨了几十万的粉丝,涨幅很是客观。
经常有人评论我,赞美我,当然也有不少吐槽我,辱骂我。
一切都宠辱不惊地接受,相比于无人知晓,我宁愿被人骂,但是生活如鱼得水。毕竟这世上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你。
即便他们不认识你,甚至没有跟你说过话,都难免平白地遭受些白眼。
之后,我安心地呆在顾宁弦公寓里画画,什么事都不去管不去听。
某一天,许久没有联系过的方瑶打电话过来,接通后,我听见她大惊小怪的声音:“言言啊,几天不见,你都成冯以文的弟子了?快说,难道被潜了?”
“我是那么没节操的人吗”我头上一排黑线,“得到冯以文的赏识,是因为我有这个才华。”
方瑶小声说:“真不是被潜了?”
“……”我无力地重复,“不是。”
“哦,那就好。”她说,“打电话过来是想告诉你,明天我要来北京一趟,准备迎接我吧。”
“你来北京?”我换了一边拿手机,“什么时候?”
方瑶不满地抱怨,“明天12点到。本来不想来的,我们那个主管假惺惺地说什么给我一个接触世界的机会,我呸,接触个毛线世界,有种让我出国啊。”
我笑着露牙齿:“后天我要出国。”
方瑶嚎叫:“神马?我要来见你了,结果你要出国了!”她怨念颇深,开始哼唧:“我就知道,顾言言你变了,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了。”
因为她明天要过来,我后天要出国的事实,导致她在电话里碎碎念了一个小时,不准我挂电话,也不准我不说话。
直到聊着聊着,我晕乎乎睡了。
第二天醒来,手机里短信被方瑶满满的愤怒表情给霸屏了。我无奈地想,方瑶还真是一点都没有变化。
出门前,顾宁弦刚好从外面走进来,拎了一些吃的。
“去哪里?快吃午饭了。”居家好男人顾宁弦摇了摇袋子里的烤鸭。
我咽了咽口水,强忍住移开目光:“去接方瑶,她要来北京出差。”
“嗯。”顾宁弦走过来,亲了一口,才放我走。
机场很是喧哗,形形色色的人来来往往。
我站在接机口好半天,瞧见方瑶穿着一身耀眼的红衣,蹬着高跟鞋,一摇一摆地走过来。朝她摆了摆手。
方瑶扔下行李,把我抱了个满怀,又蹭了蹭:“哎呀,人家想死你了。”
“少恶心我了。”我推开她,“你要是想我,怎么都不给我打电话,以前都让我给你打电话。”
“哎呀,我一不小心就把你给忘了。”方瑶毫不留情地说,把一部分行李塞进我的怀里。
我边走边说:“亏得我们多年的交情,分开了几公里就忘光光了。”
“为了补偿我们之间的友谊,你请客吧。”她说。
我理所当然地点头,然后说:“等下,谁请客?”
“你。”
我:“方瑶!!”
北京烤鸭某店。
方瑶擦了擦油腻腻的手指,打了个舒爽的饱嗝。
“真舒服,好天气,好心情。”
“谁昨天朝我抱怨来着。”我毫不犹豫地戳穿。
“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政治老师不是说过吗,物质是在不断地运动的。”方瑶摸了摸肚皮,“对了,你和顾宁弦怎么样了?”
我止不住地笑,含蓄地说:“还可以。”
“瞧你那副春心荡漾的表情,我就知道你俩肯定好。”她吃了一口鸭肉,回味无穷,“几垒了?”
方瑶的豪言壮语已经使我锻炼出一身的铜墙铁壁,淡然说:“全垒。”
“噗。”方瑶喷出被咬烂的鸭肉,被呛到了,止不住地咳,她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无所谓地说出来,被刺激到了。
我递给她餐巾纸,她擦了擦嘴角,咬牙切齿地说:“在单身狗面前秀恩爱,你们不怕我咬死你。”
我笑:“谁让你问我的。”
所以,这就叫做——自作自受。
方瑶吃完,打算去酒店住,我说:“不如去我们的公寓吧。”
“得了吧,我可不想当点灯泡,更不想晚上出来上厕所的时候,听见奇怪的声音。”方瑶眨眨眼,阴险地笑。
我轻咳了一声,帮她把行李运回了酒店。
方瑶来北京,我却不能陪她,确实是个遗憾,这天我陪她在酒店玩得很晚才回去,顾宁弦正坐在沙发上看书,看到我回来后,轻轻地说了句:“回来了。”
我“嗯”了一声,抱住他:“明天就要走了,一个月不能见你了。”
没有你做的可口饭菜,早上醒来看不见你安静的睡颜。
顾宁弦反抱回来,耳边气息热热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把握住剩下的时光。”
话中包含的意味,我听得明明白白,红着脸任他动作,或将我上上下下地抛,或面对面坐在椅子上动,从客厅,厨房到卫生间,从卫生间,卧室到客房,甚至是阳台,一晚上换了无数个地方,皮肤贴着皮肤,下身连着下身。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地板上,身下是昨晚穿的衣服,旁边躺着顾宁弦,他早就醒了,环着我的脖子,却没有将我叫醒。
脸上的皮肤细致得几乎看不见毛孔,我手指在他脸上跳舞,笑出了声,他亲了一口,蹭着我的鼻子,声音低哑:“几点了。”
热烈的阳光透过窗帘,落下一地阴影,我伸出手在附近摸了摸,摸到他的手机,迷蒙着眼睛看了一下:“哦,11点了。”
等下,11点了。
我发了三秒钟的呆,忙起来,边穿衣服边说:“快迟到了!!12点的飞机!”
穿完了衣服和裤子后,我起身,往厕所冲进去,很快又冲了回来,沙发边,顾宁弦已经穿好了衣服,我仔细一看,看到他手中拿的东西,脸整个从下至上红透。
12点的飞机,大概11点45到候机室。
冯以文身边的助理本来满脸焦急,看到我出现在门口,才松出一口气。
“顾小姐,你可吓死我了,还以为你忘记要去法国了,打手机也打不通。”助理在冯以文身边拍了拍胸口,“这次是和法国伊利丹画廊合作,可不能迟到。”
我抱歉地看着他们:“不好意思,昨晚没睡好。”
“没事。”冯以文微笑说,“赶上就好。”
飞机12点准时出发,载着我去了那个浪漫的国度,同时,离顾宁弦也越来越远。无缘由地,我突然感到一阵不安。
“顾小姐,你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助理关心地看着我说,“要不要吃点药。”
我按了按额角,强撑说:“没事,大概是没休息好的原因。”
虽然我说无所谓,但冯以文还是吩咐助理把药拿出来,给我服下。
我坐在最里头,手里捧着玻璃杯,怔怔地望着外面。
也许真的是我多虑了,东想西想,坐立不安,好像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对于这样莫名其妙的预感,我哑然失笑,甩了甩头,晃去那一分奇怪的感觉。
法国,是我人生的新的旅程,我将会踏上从此与其他人不同的路,应该高兴才是。
下飞机后,我呼出一口气,望了望异国的天空,和金发碧眼的白种人,勾起嘴角跟在冯以文的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