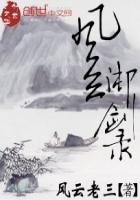这正是钱德利家族的情况,母亲的娘家。伊莎贝尔和艾瑞斯并不姓钱德利,但她们的母亲是姓钱德利的;母亲过去也姓钱德利,虽然她现在姓弗莱明;弗洛拉和维尼弗莱德依然姓着钱德利。她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祖父。祖父年轻的时候为了某个原因离开了英格兰,至今她们都无法就这个原因达成一致。母亲相信祖父是个牛津的学生,花光了家里给的钱没脸回去了。他是赌光的。不是这样。伊莎贝尔说,那不过是编出来的话,真实的情况是他把一个女仆的肚子弄大了,不得已娶了她,然后带她到了加拿大。家族在英格兰的领地就在坎特伯里附近。(天路历程,坎特伯里大钟。)其他人对此并不信服。弗洛拉说他们原本住在英格兰西部,钱德利这个姓和车蒙德里这个姓是有联系的;那里有车蒙德里贵族,钱德利很可能就是那个家族的旁支。不过也有可能,她说,钱德利是个法国姓,原本拼写应该是Champdelaiche,意思是拥有薹草的领地。如此一来,这个家族很可能是随着征服者威廉大帝来的英格兰。
伊莎贝尔说自己文化不高,她知道的英国历史只有苏格兰的玛丽皇后一人。她问谁能告诉她,征服者威廉究竟是在苏格兰的玛丽皇后之前,还是之后,到达的英格兰?
“薹草地,”我的父亲点头称是,“难怪他们在那里发不了财。”
“好吧,我可分不清薹草和燕麦,”艾瑞斯说。“不过他们在英格兰足够富了,据祖父说,他们在那里是乡绅。”
“是在玛丽皇后之前,”弗洛拉说。“苏格兰的玛丽皇后也不是英国人。”
“听名字就知道了,”伊莎贝尔说,“所以哈——哈。”
她们每一个人都相信,不管细节如何,曾经一定有过大衰败,大灾难,而如今她们遥不可及,留在身后,留在英格兰的,是土地、宅院,还有安逸和荣誉。不然还能怎么想,就看看她们的祖父吧。
她们的祖父是个邮局职员,在福克磨坊。他的妻子,不管她究竟是不是个被诱拐的女仆,给他生了八个孩子后就死了。一旦大孩子们可以到外头干活给家里赚钱了——想读书简直是胡扯——做父亲的就把工作给辞了。直接原因是和邮局局长闹翻了,不过实际上他也不想干了;他打定主意就待在家里,由儿女们养着。他有着一副绅士派头,阅读很广,说话咬文嚼字,自尊心强。他的儿女们毫无怨言地供养他。他们安于平凡,却鼓励自己的孩子们——他们都不敢生太多,只要了一两个,大部分是女孩——外出求学,读商校、师范学校,或者是护士培训班。母亲和她的表姐妹就是这些孩子。她们常常谈论起她们自私的异想天开的祖父,却很少提她们体面的、努力工作的父母。祖父可真是个老势利鬼,她们说,但他多帅啊,即便年纪大了,还是一副好风骨。他的嘲讽一触即发、一针见血,他说的话能有多伤人啊。有一次,在遥远的多伦多,事实上就在伊顿百货的大厅里,福克磨坊马具匠的老婆上前和他搭话,一个无害亦无脑的婆子。她喊道:“哎呀,离家这么远居然还能碰到朋友,真好啊!”
“女士,”钱德利祖父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他可当真一点儿都不敷衍,她们说。女士,你不是我的朋友!这个老势利鬼。他目空一切地昂首阔步像是只冠军鹅。另一次,一个阶层较低的女士——对他而言阶层较低——很好心地给他带了点汤,那时候他正感冒了。他坐在女儿的厨房里,头顶上甚至都不是自家的屋檐,泡着脚,完全是一个患病的,实际上也是濒死的老人。他却依然有胆子背过身去,留着她女儿去说客套话。他看不起那女人,因为她的语法很糟糕,而且还没有牙齿。
“但他自己也没有啊!他那个年纪不管怎样也没有牙齿了!”
“装腔作势的老呆瓜。”
“吸儿子的血。”
“就是傲慢、自负。他整个儿就那样。”
不过说起这些故事的时候,她们自己高声笑着,浑身洋溢着骄傲,夸夸其口。她们很骄傲能有这么一位祖父。她们相信拒绝和比自己阶层低的人说话是无礼刻薄的,相信强抓着荣誉感是不可理喻的,尤其是当你的牙齿全掉了的时候,但奇怪的是,她们依然敬佩他。她们真的敬佩。她们敬佩他的谩骂,那谩骂的对象可是他的老板,勤勉的邮局局长。她们也敬佩他的傲慢举止,那傲慢的对象是他的邻居们,加拿大的民主公民。(哦,太遗憾了,那个没有牙的邻居说,可怜的老朋友,他都认不出我了。)甚至,她们或许还敬佩他能决意让别人去工作去养他。一个绅士,她们这么称呼他。她们的语气很嘲讽,但是能拥有这么一位祖父一直很让她们高兴。
我不能明白这一点,当时也好,以后也好。我身上有太多苏格兰的血液,太多父亲的血液。我的父亲永远都不会认为这世上是有人生而低贱,或生而高贵的。他是彻彻底底的平等论者,决计不会对任何人,如他自己说的,“哭诉”,也不会磕头,也不会向任何人脱帽屈膝,他待人接物就好像彼此没任何差别。我也是这样的人。后来,有些时候,我会想,这种姿态是否也是出于一种让人僵化的审慎呢,正如任何高尚的道德一样。有些时候,我会想,难道在父亲和我心中,真的不存在一种优越感吗?那种优越感更为完整和坚固,若拿母亲和她的表姐妹们那种孩子气的势利相比较,后者简直望尘莫及。
多年以后,长大了的小镇女孩已嫁为人妻成为人母,生活在大城市的高级社区衣食无忧。一天,她突然接到了艾瑞斯姨妈的电话,但她却开始对艾瑞斯姨妈的拜访忧心忡忡,说不清道不明地感到不安。
我渴望姨妈的这次拜访能顺顺利利的。我是为了自己这样想。我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动机,我只希望艾瑞斯姨妈能够作为一位不让人丢脸的亲戚闪亮登场,另一方面我也希望理查德和他的钱和我们的房子能够让我在艾瑞斯姨妈心目中的地位大大提升,我不再是什么穷亲戚了。我希望所有这些都能实现,体面地,貌似不经心却有礼有节,最终使我自身的价值在两方面都能得到愉快的承认。
我曾经想过,如果我能弄出个有钱的举止优雅的重要人物来做亲戚,理查德对我的态度或许就会改变。一个法官、一个外科医生,大概就能做得圆满了。我不太确定艾瑞斯姨妈,作为一个替代,能做到几分。我对理查德提到“达格莱墟”的态度有点担心,也担心姨妈说话露出的渥太华山谷口音——理查德对农村口音很不宽容,对我的就诸多不满——艾瑞斯姨妈的声音里还有些东西让我忧心忡忡,但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她是不是表现得太急迫了?她是不是在炫耀某种她认为理所应当的家族权利,而如今的我却不再认同了。
原来“我”的丈夫出身于金融世家,虽然爱“我”,却一直对“我”的出身有诸多不满。而如今,艾瑞斯姨妈的出现,让“我”情不自禁地以丈夫的目光审视自身。
但当然这些对我来说都无关紧要吧?所有关于甜点叉的废话?认为拥有了这些东西就拥有了文明的生活态度,我以前是那种人吗?现在是吗?不,我绝对不是。不过这么说其实也不全对,应该说我也是也不是。也是也不是。“背景”是理查德用的词。你的背景。他的声音是降调的,有一丝警告。或者那只是我自己听起来如此,而不是他的真实意思?当他提到达格莱墟,甚至一个字都没有地递给我家信,我都感觉羞愧难当,就好像有什么在我身体里生长。是霉菌,肮脏的,扫兴的,无处可逃的。贫穷,对于理查德的家庭,就像是口臭或是脓疮,一种让患者也跟着感到羞耻的疾病。不过表现出来是不礼貌的。如果我在他们面前提一句我的童年或我的家庭,他们都会往后缩一缩,仿佛我说了下流的脏话。不过大概是因为我有点尖锐也太敏感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芙笔下的那些教养不够的人物,只为着进不了马戏团就大吵大闹一番。或许他们正是为此感到尴尬。他们跟我相处很注意技巧。理查德可没那么有策略,不然怎么会娶我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他觉得我的过去是个寒酸的包袱,希望我能和过去一刀两断。他时刻留意着我和过去藕断丝连的蛛丝马迹;确实就是藕断丝连。
不出所料,这次的拜访成为了一次灾难。艾瑞斯姨妈表现得非常夸张与不自然,而丈夫则毫不掩饰自己的鄙视之情。“我”夹在中间,无所归依。
艾瑞斯姨妈比过去更加壮了,扑着粉的脸红彤彤的。她因为一路上坡累得气喘吁吁。我不愿意求理查德去酒店接她。我不愿意承认我是有点怕求他;我只是不想让事情一开始就上错了轨道,比如逼理查德去做他不愿意的事情。我安慰自己说她可以叫个出租车。然而她却坐了公共汽车。
“理查德太忙了,”我对她撒谎,“都怪我。我不会开车。”
“没关系的,”艾瑞斯姨妈很坚决地说,“我就现在气接不上,不过一会儿就好了。都是这一身肥肉。我是活该。”
她一开始说“气接不上”,还有“一身肥肉”,我就知道理查德会怎么想了。其实早在艾瑞斯姨妈说那些话之前,我第一眼看到她出现在家门口,就马上预感会发生什么。她的头发,记忆里原来是灰棕色的,现在染成了金色,吹成了一个泡泡堆;招摇的孔雀蓝裙子,金色的装饰穗带从一侧的肩膀处喷涌而下。现在我回想,她看起来简直光彩照人。我很希望我不是在家里遇见她。我希望我能给予她应得的欣赏。我希望一切能重新来过。
“好吧,说起来,”她欢快地说,“你现在生活得很不错嘛!”她看着我,还有假山花园,还有绿化灌木以及大面积的玻璃窗。我们的房子坐落于顾罗思山一侧的卡皮拉诺高地。“我说,这儿可真是个漂亮的地方,亲爱的。”
我带她进屋把她介绍给理查德。她说,“哦——,那么你就是丈夫了。好吧,我可不会问你生意如何因为我能看出很不错。”
理查德是一个律师。他家族的人不是律师就是股票经纪人。他们从来不把他们做的事叫生意。他们根本就不说自己做的事。谈论所做的事情被认为是粗俗的,谈论做得如何就更加不可饶恕了。如果当时我能对理查德强硬一点,我就会幸灾乐祸地看他措手不及地遭遇到这一问候了。
我立刻建议喝茶,也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隔离带。我拿出了瓶雪利酒,想着老年女人通常都会要这个,她们应该都不常喝酒。但是艾瑞斯笑了,说:“你怎么忘了,我喜欢杜松子酒混着汽水喝,就和你家人一样。”
“还记得那次我们全到达格莱墟看你们吗?”她说,“根本不准喝酒!你妈妈还是一个乡下姑娘呢,家里都不许放酒。尽管我一直以为你父亲是会喝一点的,如果你把他带出去的话。弗洛拉也是滴酒不沾的。不过你知道维尼弗莱德可是个酒鬼吗?她衣箱里还藏了一瓶。我们会偷偷溜进卧室呷上一口,然后用古龙水漱口。维尼弗莱德说你家是撒哈拉沙漠。瞧我们正穿越撒哈拉。不过我们喝的柠檬水和冰茶可够浮起一艘战舰的了。得起航四艘战舰呢,对不?”
也许在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她也注意到了什么——我的惊讶,没有及时热情地欢迎。也许她也有点感觉受挫,尽管同时也为着这房子和家具欢欣鼓舞,屋子里一切都很高雅、老派,也不全是理查德挑选的。不知什么原因,她谈起达格莱墟和我的父母时口气有一点高人一等。我不觉得她是有意要提醒我的出身,要置我于尴尬;我想她只是希望能让自己有一席之地,让我知道她也属于这里,而不是那里。
最后,艾瑞斯姨妈终于离开,这次拜访结束了。但是家中的战争还在继续。那种情感的裂缝,无可弥补。
终于,艾瑞斯恢复过来了,问我最后的公共汽车是几点钟。理查德再次消失。不过我说我可以叫个出租车送她回酒店。她说不用。她喜欢坐公共汽车。她没说假话,她总是可以和什么人搭上话。我放弃了自己的计划陪她走到公共汽车站。她说希望她没把理查德和我的耳朵吵翻,还问理查德是不是挺害羞的。她说我有一个很可爱的房子,一个很可爱的家,能看到我把自己的人生经营得这么好让她感觉很骄傲。当她和我拥抱说再见的时候,眼泪浸满了她的双眼。
“真是个可怜的老妖怪。”理查德说。他走进客厅的时候我正收拾咖啡杯。他跟着我去了厨房,数落起她说的那些事,那些虚头八脑的事,那些自吹自擂。他还指出她的语法错误,列举怎样用其他正确文雅的表达来替换这些错误。他装得想不通。也许他真的想不通。也许他觉得在我谴责他没有陪客人待在屋里,谴责他表现粗鲁,谴责他没有主动提出送客人回酒店之前,最好先下手为强开始他那一方的攻击。
他正说着呢,我把派热克斯牌玻璃盘往他头上扔了过去。盘子里还有一片柠檬蛋白酥皮饼。盘子没有击中目标,但砸到了冰箱,饼飞了出来,打在了他一边的脸上,就好像是老式电影或者《我喜欢露西》的肥皂剧里演的一样。对他而言,那诧异就和银幕上的一模一样,他突然呈现出一副完全无辜的模样;他的话停住了,嘴却大张着。就我而言,我则诧异地发现,那一幕尽管旁观的人们总觉得滑稽可笑,然而在真实生活中,竟会成为如此可怕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