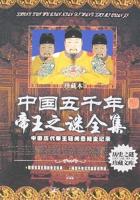自此之后,每次我寻找欢乐,都追忆这天夜里的情景。苏斯那次艳遇之后,我再次可耻地堕落了。快乐,我偶尔顺便得手一次,那都是偷偷地进行的。然而一天晚上(那是在抵达拉布雷维纳之前不久),在船上与科姆湖一个年轻船员,却是妙不可言:湖面奇幻的轻雾和岸边潮润的芳香融于月光里,我在月光笼罩下,心醉神迷。过后呢,什么也没留下,只是一片可怕的荒漠,充斥着没有应和的呼唤,没有目标的冲动,不安,争斗,令人疲乏不堪的梦,想象的激奋,恼人的颓丧。离开拉洛克前两年的夏天,我觉得自己变疯了,在那里度过的所有时间,都是关在房间里。本来只有工作能把我留在房间里,可是强迫自己工作也白搭(我正在写作《乌有国游记》),我像着了魔,像魔鬼附身,大概希望从毫无节制之中寻求排遣,从另一面登上蓝天,让纠缠我的魔鬼精疲力竭(我承认正是我的魔鬼给我出的主意),结果被搞得精疲力竭的是我自己,我狂躁地消耗着自己,直到彻底衰竭,直到自己面前只剩下痴愚和疯狂。
啊!我脱离的是多么可怕的地狱!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诉说,没有任何人出出主意;我相信一切调和都是不可能,起初死活都不肯退一步,所以只有沉沦……可是,有什么必要重提那些凄惨的日子?难道对它们的回忆能够解释我这天夜里的疯狂?在梅莉姆身边的尝试、“正常化”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行不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正常状态。这里不再有任何压抑、匆忙、暧昧,我所保留的回忆中没有丝毫灰色。我的快乐是巨大的,假如掺和了爱情,我都无法想象它会有多圆满。怎么会有爱情问题呢?我怎么会让爱情支配我的心呢?我的快乐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不会产生任何后悔。可是,把那个美好、野性、热烈、淫荡、神秘的小小肉体搂在自己赤裸的怀里时,那种冲动叫做什么?
穆罕默德离开我之后,我久久地沉迷在激动不已的狂喜状态。在他身边我已经五次达到高潮,但还是一次又一次设法重现那种销魂的快感。回到宾馆的房间,直到清晨,意犹未尽。
我知道,这里叙述的某些细节会引人发笑,其实我很容易略而不提,或者以情理上逼真为准加以修饰。但是,我追求的不是逼真,而是真实;真实,难道不是恰恰在它最不逼真的时候,最值得讲出来吗?你想吧我除了实话实说还能做什么?
由于我在这里仅仅是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此外我刚刚读完薄伽丘薄伽丘(Boccace,1313—1375),意大利作家,出生于巴黎,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先驱。代表作《十日谈》。的《夜莺》,所以我想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大惊小怪,倒是穆罕默德的惊讶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什么地方超过了这种限度?那是在随后发生的事情之中;正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中,开始了对我来讲不可理喻的情形:尽管我已经那样心醉神迷,那样精疲力竭,但我还是不知道停止和休息,而是把自己搞得更加精疲力竭。随后我常常感觉到,试图节制也做不到,尽管理智告诉我要节制,要谨慎。每次我试图这样,随后就不得不孤独地把自己搞得彻底精疲力竭;不彻底精疲力竭,我就得不到任何休息,而休息,想少付出代价是得不到的。总之,我根本不负责解释,我知道我一定会什么也没明白,或者对人体的机能知之甚少,就抛弃生命。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穿着便鞋,远远地跑到——是的,的确是跑到穆斯塔法城外。对刚过去的一夜丝毫不感到疲倦,相反感到非常快活,灵魂和肉体都感到轻松,而且整个一天都是这样。
两年后我重新见到穆罕默德。他的面部没有多大变化,只稍稍显得不那么年轻了,身材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但目光中再也没有那种忧郁的神色,我从中觉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冷漠、不安和下流。
“你不再抽大麻了?”我明知故问。
“不抽啦,”他答道,“现在我喝苦艾酒。”
他仍然富有吸引力——我说什么?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吸引力,但看上去厚颜无耻多于淫荡好色。
达尼埃尔和我在一起。穆罕默德把我们领到一家不三不四的旅馆的五层;底层有一家酒吧,一些海员在喝酒。老板问我们姓名,我在簿子上登记了恺撒·布洛克。达尼埃尔要了啤酒和汽水,“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他说。我们进入的房间只靠刚才上楼时所拿的那枝蜡烛照亮。一个侍者送来啤酒、汽水和玻璃杯,放在蜡烛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只有两张椅子,达尼埃尔和我坐下,穆罕默德则坐在我俩之间的桌子上。他现在穿了件白罩袍,代替了过去那套突尼斯服装,向我们伸出两条裸腿。
“每个人一条。”他笑着对我们说。
我坐在饮了一半的玻璃杯旁边没动,达尼埃尔抓住穆罕默德,搂在怀里,抱到房间里端的床上,让他仰着横卧在床边上。不一会儿,我只看见垂在大动的达尼埃尔身体两边的两条细腿了。达尼埃尔甚至没有脱大衣。他个子很高,靠床站着,只模糊地看见背部,脸被黝黑的长鬈发遮住。达尼埃尔穿着那件长及脚跟的大衣,显得非常魁梧,俯在那个小小的身体之上,盖住了它,像一个高大的鬼在吸一具尸体的血。我差点恐怖地叫喊起来……人们总是很难理解别人的爱情和别人做爱的方式。甚至包括动物的做爱方式(我似乎应该把这个“甚至”留给人类)。人们可能羡慕鸟的歌唱和飞翔,写道:
啊!你知道鱼在海底是什么样吗?
它们那么舒适!
甚至啃着骨头的狗,也从我身上看到某种与禽兽相通的东西。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每种动物获得快感的姿势,尽管不同种类之间千差万别。关于这一点,古尔蒙先生竭力看到人与各种动物之间存在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认为这种相似之处只存在欲望领域,而在古尔蒙先生所称的“爱情物理学”方面,也许正好相反,不仅在人与动物之间,而且往往在人与人之间,不同最为明显,以至于如果允许我们进行观察,我们身旁人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像两栖类和昆虫以及狗和猫的交配一样,往往显得稀奇古怪、荒唐可笑,干脆说吧:显得极为可怕。可是为什么扯得这样远?
大概也因为这样,在这一点上,不理解非常深,不妥协非常剧烈。
我呢,只理解面对面的、相互的、不带强暴的快乐,像惠特曼惠特曼(Whitman,1819—1892),美国诗人,《草叶集》作者,早期作品宣扬肉体和性爱的美妙。一样,在偷偷的接触满足之后,常常感到恐惧,因为一方面看到达尼埃尔那种搞法,另一方面看到穆罕默德那样心甘情愿地顺从。
这个难忘的晚上之后不久,王尔德和我就离开了阿尔及尔。他赶回英国,需要去了结博西的父亲肯斯贝利侯爵对他的指控。我呢,则希望赶在博西前头到达比斯克拉。博西已决定把他爱上的布里达赫阿拉伯青年阿里带到比斯克拉。他的一封信通知我他即将返回,希望我同意等他,以便与他、与他们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长途旅行,因为他与阿里单独去,可能会有性命危险。他披露,阿里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英语,而博西自己不会讲阿拉伯语。我天生性格不好,这封信反而促使我赶快离开。或许因为我不乐意促成这次冒险,帮助一个认为一切都该着他的人,或许因为沉睡在我心灵里的道学家认为拔掉玫瑰的刺不合适,或者更简单,是因为我阴郁的心情占了上风,抑或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离开了。但在我停留过夜的塞蒂夫,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我手里。
我以反常的热情,欢迎行将摧毁我的道路的一切东西;我不力求解释,这正是我天性的一个特点,因为我无法理解……总之,我立刻中止旅行,开始在塞蒂夫等待道格拉斯,像先天逃避时一样心甘情愿。尽管这样,从阿尔及尔到塞蒂夫的旅程我觉得非常漫长,可是很快我就觉得这种等待更加漫长。真是没完没了的一天!“明天那一天又会怎么样呢?中间隔着一个比斯克拉呢。”我想道,在这座丑陋的军事和殖民山城一条条规则而枯燥乏味的街道上大步走着。在这里碰到的几个阿拉伯人看上去都是流亡者,可怜兮兮,我无法想象人们会到这里来做生意或奉命住在这里。
我迫不及待地想认识阿里,估计他是一个很朴素的卡瓦其人,穿着大概与穆罕默德差不多。但是我看见从火车上下来的是一个年轻贵族,穿着非常讲究,系一条丝质腰带,缠着缀满金饰的头巾。他还不到16岁,但举手投足显得多么高贵!目光眼神显得多么高傲!对旅馆里向他鞠躬的侍应生,他带着多么不可一世的笑容扫视他们!他很快就明白,尽管昨天他还是那样卑贱,现在该他头一个进来,头一个坐下……道格拉斯找到了自己的主人,他本人也算穿得考究,但看上去像一个听从阔绰的仆人吩咐的随从。任何阿拉伯人,不管他多穷,都心怀一个即将诞生的阿拉丁阿拉丁(Aladin),《一千零一夜》中《神灯》的小主人公。,只要经命运点化,他就会成为国王。
阿里无疑很帅,肤色白皙,前额清纯,下巴匀称,小嘴可人,面颊丰满,眼若仙子,但他的美貌对我丝毫没产生支配的效果。他的鼻翼显示出某种凶悍,太过匀称的眉毛弧线显示出某种冷漠,嘴唇轻蔑地撅起时则流露出残忍,这使我一切欲望全部消失。他整个人最令我产生排斥感的,是他那女性的外表,而恰恰这一点也许会使其他人神魂颠倒。我说这些话无非是想让读者明白,我在他身边生活了相当长时间而方寸未乱。甚至像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道格拉斯那副如痴似醉的样子,反而促使我情绪更加恬淡,他走后我在比斯克拉逗留期间,一直保持着这种情绪。
绿洲宾馆,头年我们在这里租住过主教套房,已经拥有这类房间。但刚刚开张的皇家宾馆,所拥有的设备,从情趣和方便上讲,仅略逊于绿洲宾馆。一层三个房间,其中有两间紧挨着,位于一条走廊尽头,那里有一道门通到外边。走廊那道门只供我们出入,我们有钥匙,这样到自己房间就不必穿过宾馆。不过,我通常是从窗户进出房间。我的房间与道格拉斯和阿里的房间隔着走廊,我吩咐搬来一架钢琴放在里面。他们那两个房间朝向新开的娱乐场,中间隔了一块相当宽阔的空地,上面有一些停课的孩子在嬉戏;就是头年到我们的阳台上来玩的那些孩子。
我说过阿里不懂法语,我推荐阿特曼给他们两个当翻译,因为阿特曼听说我要来,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希望到我身边来帮忙,我正不知道如何用他。但随后我就责备自己,竟然想到给他安排这样一个位置。除了道格拉斯和阿里的关系对一个阿拉伯人来讲,没有任何稀奇之处,我当时对阿特曼也没有那么深厚的友谊,后来要那样为他操心——不过不久他就值得我操心了。起初我一提出那个建议他就连忙接受了,我很快明白,他是为了有更多时间呆在我身边。可怜的小伙子看到我决心不陪道格拉斯外出溜达,总之明白他很少有机会见到我,感到十分难为情。道格拉斯每天带他和阿里乘马车去附近某个绿洲,如舍特马、德洛赫、西迪·奥克巴等,在宾馆的阳台上,可以望见这些深绿或翠绿的绿洲,镶嵌在沙漠赤黄色的外衣上。道格拉斯硬想拉我去也不成。他与那两个年轻随从在一起肯定会感到无聊,因为在我看来,那两个人像是快乐的赎金,但我对他没有丝毫同情感。“这是你心甘情愿的!”我想道。对于按天性自己多半会倾向于接受的事,我摆出铁面无情的架势稳住自己。关于赎金的想法也是这样,我更加埋头工作,自鸣得意地觉得正在赎回某种东西。如今岁月使我变得更加循规蹈矩了,一种旧的伦理竟有如此多迟疑和残余,真是令我吃惊。这种旧伦理我根本不再赞同,但人们仍然依据它作出道德上的反应。我试图弄清楚,是什么动力使我的机体情不自禁地如此反抗。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我弄明白了主要是反感和没有诚意。不过博西也很不令我喜欢,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令我感兴趣远远甚于令我喜欢。尽管他殷勤、体贴,甚或也许正因为这些,我总是严阵以待。与他交谈我很快就会厌倦。我宁愿相信,与一个英国人,或者仅仅与一个比当时的我稍许更精通英国情况的人交谈,这种交谈也会更丰富多彩。可是道格拉斯呢,一般的话题谈完了,就总是以一种令人讨厌的固执,一次又一次谈那些我一谈就感到非常尴尬的话题,他一点也不尴尬就使我愈加尴尬。只要在那没休没止的客饭席上再见到他,就够我受的了。他会多么可爱、风趣、优雅地突然嚷道:“我绝对要喝香槟!”我为什么一定要不快地拒绝他递来的那杯香槟呢?有时,在与阿特曼和阿里一块饮茶时,我听见他上十次重复——他得意的不是这句话本身,而是他这样重复:“阿特曼,告诉阿里,他有一双羚羊一样的眼睛法语里羚羊一样的眼睛,意即温柔的大眼睛。。”他每天都使无聊的极限后退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