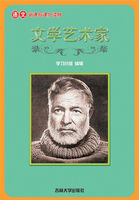跟里尔发生对骂之前的几个月,我见了一位著名的神经外科医生,名叫米尔顿·海费茨。海费茨掌握了一些极先进的技术,专治脑动脉瘤和其他一些以前无法处理的病症。我前去见他,是因为我的止痛药的药效越来越不行了。他告诉我说他是个“大脑人,”而不是“腰背人”。“不过,”他告诉我说,“您应该去看杜克大学医疗中心的布莱恩·纳肖尔德,他最近开发出了一种治疗神经痛的技术。”我立即给杜克大学打电话,并预约了门诊。纳肖尔德告诉我说,他和这所大学的其他一组医生正在使用一种新的技术,是用激光精确烧灼各个神经纤维。他们正在进行实验,用一种方法把神经丛上的单根纤维挑出来,然后用激光使其烧断。这种技术给了我一种希望,即它可以消除疼痛,但不又致损坏邻近的神经,这会使我保持对膀胱和大肠功能的控制。
咨询过后,我与纳肖尔德医生约定了第一次外科手术的日期,并在几个星期后进行了手术,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医生们在激光的使用中相当保守,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引起疼痛的那些神经并没有完全烧断,可我的感觉的确好多了。我可以说,这次手术使我的疼痛减轻了一半。我腿上的感觉从觉得像泡在沸水里一样,到感觉像泡在极烫的水里面一样——应该说好些了,但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把这个好转抵销掉的是,我的药效越来越低,持续稳定地下降。可是,我把这次手术部分的成功看作一种好的迹象,因为未来可能会更好些。这是自枪击以来我看到的第一线希望。有一阵子,它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在杜克进行过手术不久,与里尔法官对骂之前,我自己也开始了一些手术——我想把《风尘女郎》的销售提高一个档次。我决定竞选美国总统,这是个恶作剧的把戏,可并不是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我已经开办了一家新闻杂志——这是我短暂信教之后早就计划好了的——可当时我仍然处于新生体验的影响下,这本杂志完全不是我首先预想到的那种主流杂志。《叛逆》像它的名字一样,是全国最具叛逆性的一本新闻杂志,完全成了我恐吓别人的工具,我利用它宣布了我准备竞选总统的消息。1983年12月31日的编者按页上是我穿着一件T恤衫的照片,T恤衫上写着:“拉里·弗林特竞选美国总统”。照片下面是一个问题:“谁将是我们的下一届总统?”编者按的第一句话就确定了语气:
现在,全世界都已经明白,热衷于核武器的美国牛仔罗纳德·里根及他的全体内阁都必须不体面地下台。里根团伙,我就是这么称呼的。是一个丑闻,在全人类的历史上都不曾出现过这样的丑闻,因为这个星球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一种痴痴呆呆的法西斯顽固王八蛋充任世界领袖的时候。
这些话是我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费尔德市的联邦监狱医疗中心写的,当时我处在孤独的囚禁中,这还得感谢里尔法官。我还在编者按中说,也许里根及其内阁应该跟我一起到斯普林费尔德进行完整的精神状况评估,“也许,监狱的这个杂种,洛根医生,会给美国人民一些答案……”我还加上:“上帝知道,我们很需要这些答案。”
除了为《风尘女郎》争取一些知名度以外,我那闹哄哄的总统竞选活动还真的制造了真正的热点,我极想找出这个国家在猥亵法上面的一些漏洞。我知道,联邦通讯法中有一个等时规定,候选人的声音或者图片出现在广告中时,禁止对该广告进行查禁活动,而美国刑法却又禁止猥亵材料的传播。我制作了一个X级的电视宣传片,里面包括了我的照片和我的声音。我把它送到好几家电视台,坚持要他们播放。电视台的经理们想到播放我的广告可能会出现的情景,他们几乎晕了过去,因此拒绝播放。我敦促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发表一个意见,他们否决了我的广告,但只是当我已经在政府的各个部门引起了惊慌之后才决定的——而且是在花费了许多时间以后才决定的。FCC显然是把我的总统竞选当真了,更为可笑的是,许多公民也这么想。我获得了许多捐款——这是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尺度,表明了普通人对里根政府的不满。
除了我在监禁期间为《叛逆》写的一些社论以外,我还设法参加了许多提高知名度的活动。我在联邦监狱的经验当然是像地狱一样的,可它也不是毫无收获的。我先后被送往两处不同的地点:一是密苏里的斯普林费尔德,一是北卡罗莱纳的巴特纳。在两个地方,我都想尽办法让囚禁我的人难受,同时也让我的知名度不断上升。大多数进入联邦政府监狱系统的人都与世隔绝,软弱无力,我却有一群律师监视着对我的处理,还有无数的记者和新闻工作者吵吵闹闹着索要有关我的现状的新闻。我在监狱里定期发放有关总统竞选、德罗林案件及其他我可以利用的活题的宣言。我发现整个情形很容易对付,并以想得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利用我的监禁。比如,我会给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把我接到亚特兰大的CNN台接受采访。这真使权贵们吓得要死,但他们又不能阻止我。
联邦监狱简直拿我这块硬骨头没办法。典狱长好几次对我弟弟吉米说,他们希望把我弄走。“他在毁灭我们的生活。”他们常说。我对他们头脑简单的控制办法一点耐心也没有了。我在巴特纳的时候,他们在我身上进行一种新的行为修正技术。这是一种对孩子或者白痴而不是成人适用的奖惩办法。当我拒绝服从,或者参加某种“不适宜的行为”时,他们会拿走我的收音机或者其他基本的用品,以示对我的惩罚。很自然,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合作,而且很快发现自己什么便利和特权都没有了。某个家长型的家伙会来到我的牢室里,像责备小孩子一样责备我,然后拿出奖励的希望。他们以为他们可以像训练黑猩猩一样训练我,这种疗法只唤起了我最为低贱的本能。有一天,当这个家伙又跑进来的时候,我把自己拉的粪便一把仍在他身上,打了个正着。我对他吼道:“狗娘养的,你把我的东西都拿跑了,可你拿不走我的心!”面对着他们行为修正法的失败,他们很高兴把我弄走了。
斯普林费尔德也急于早早把我弄走。我已经对这种制度付出了太大的注意力,知名度却又是这个系统不太喜欢的东西。巴特纳本来不太情愿收留我这个爱闹事的家伙的,巴特纳的典狱长非常清楚我为什么从斯普林费尔德转到这里来的。联邦监狱系统是管理者和典狱长们的小小兄弟会。我留下了一个极长的尾巴,从斯普林费尔德到加利福尼亚的特明诺岛。我在斯普林费尔德的出现差点让典狱长帕塔斯基丢了饭碗。阿尔西娅定期来看我,有一次,她遇到了典狱长的女儿莉莎。阿尔西娅和莉莎慢慢相熟了,过一阵子后,她们开始聚会了。她们吸一些烟,还用鼻子吸可卡因。消息传开了,说是阿尔西娅和典狱长的女儿在一起吸毒。莉莎·帕塔斯基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就在吸毒,可她以前一直隐瞒着没让人看出来。可是,这个习惯被人发觉后——尤其有谣言说是阿尔西娅让她抽的——联邦人员决定,如果帕塔斯基不能控制他女儿的毒瘾,他就无法控制一座大监狱。我送到巴特纳以后,帕塔斯基也调到了一个小地方。五个半月以后,我放了出来。第九巡回法庭驳回了里尔的判决,并取消了蔑视罪名。
我的总统竞选没折腾多长时间,从巴特纳放回的几个星期以后,我暂时放下了这项活动。我竞选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为《风尘女郎》换来了很高的知名度,也把注意力导向了我很关心的好几个问题。鉴于现在我的注意力转向了民权活动,我决定继续定期对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些议员进行启蒙教育,还是用以前的一些手法。我不再发表演说了,因此这种启蒙活动合乎逻辑的媒体就是《风尘女郎》了,我向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个议员和最高法院全部9名法官免费寄送这本杂志。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我说,这免费的杂志会帮助他们“及时掌握所有的社会议题和潮流。”我还觉得,这些杂志也可能会使这些老王八们得到几年以来的第一次勃起。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保守份子们大发雷庭,命令邮政总局禁止向他们发送《风尘女郎》。我提起了诉讼,并在联邦法庭上阻止他们发布这种禁令。这事最后定下来了,因为一位法官认为,发布这样一个禁令将有违宪法。这个案子处于搁置阶段时——其间,《风尘女郎》照寄不误——我决定跟参议院最顽固的一个家伙杰斯·赫尔姆斯玩一把。在《风尘女郎》的封底,所有的性用品广告都集中在这里,我让艺术设计部门为杰斯设计了一个电话性服务广告。广告顶端写着:“杰斯·赫尔姆斯——电话性服务——最好是黑人。”我们把他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他在参议院的电话号码包括在里面了。然后,在底下,我们还加了一句:“如果没有人接,请拨……”这里还加上了他家的电话号码,这是我们从一位记者那里搞来的。赫尔姆斯接到无以数计的电话,他只得把家里的电话掐断了。真是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