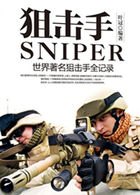在最高法院击败基顿上诉案之前的好几个月,约翰·德罗林及其同名汽车公司正在制造全国新闻,我缩在自己的卧室里一直在追踪德罗林案件。多少年以来,我收到不少照片和影带,都是一些富人、著名人士、名声不好的人的现场证据。有些人认为我是专治伪善的警察,因此,当他们找到或者想办法拿到具有敲诈作用的材料时,都直接寄到我这里来。我从不敲诈别人,可是,对一些骗子我可决不留情。我在《风尘女郎》上发表了好多给这些人造成危害的照片,还摧毁了更多的人。我从不试图有意伤害无辜的人。我收到过令人尴尬的、性暴露的图片,有帕特·布恩的,有台德·特纳和简·方达的,有帕米拉·李·安德逊的,还有好几个右派政客的。可是,直到约翰·德罗林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机会给联邦政府来个措手不及。
德罗林因为持有大量可卡因而被联邦调查局逮捕——据说他准备销售这些药品,以期挽救他奄奄一息的汽车公司。德罗林的赛车装有不锈钢包层,但销售出现了大麻烦,因而他的汽车公司到了倒闭的边缘。德罗林想尽办法还债,其间还遭到过逮捕。有一天,新闻广播讲过他的故事之后,我接到一个包裹,是德罗林辩护律师办公室里的一位未署名办事员寄来的。包裹里面有一盘录相带,里面记录着逮捕的情况及逮捕以前不久发生的一些事件。这是件惊人的事件,里面显示出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如何设下陷阱,让这位绝望的企业家钻了进去。看完带子之后,我决定,这盘带子应该让全国观众看一看。政府设陷阱坑害别人——引诱他们犯罪然后逮捕他们——这个想法真使我气愤。如果没有联邦调查局的参与,可能就没有犯罪,其特工人员提供了可卡因,还提醒德罗林说,把这些可卡因卖出去就有可能解决他的问题。
曾获艾美奖的导演东·休伊特是“60分”节目的制作人,我多年以前见过他。他接到消息,说我这里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带子。有一天早晨,他从纽约打来电话,问他是否可以立即见我。“来吧。”我说。几小时后,他到了,阿尔西娅带他进来,并引到了我的房间里。带子已经装在录像机里面了,我就坐在电视机前,摸着遥控器。“我们看看吧。”休伊特说,省掉了一大堆废话。我按下按钮,黑白带就开始放起来。放完之后,休伊特大叫起来:“我的天!你怎么搞到这带子的?”“我从来不说出自己的来源。”我说,一边咧嘴笑了起来。
话传出去了,说“60分”节目组拿到了带子,几天之内,联邦公诉人、德罗林的律师和CBS公司的律师就到了法庭。联邦来人提出强制令,要求禁止新闻网络公布这盘带子。结果强制令没有发出来,带子在接下来的星期天播放出来,并引起了全国轰动。新闻报纸纷纷在头条位置刊出以下醒目的标题:“德罗林审判无限期推迟”、“德罗林的律师要求撤销所有罪名”、“弗林特的录像带搅毁刑事案”。我认为这盘带子是对联邦政府的起诉。而不是对德罗林的起诉,因此很高兴看到整个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可是,这事没能持续多久。联邦政府稍后才处理这件案子,希望这场风波过去以后再行审理。也许,这场风波的确过去了,可同时我还在不断寻找来源,又搞到另一盘带子,这次是一盘录音带。我在住处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将其内容透露了出来。
吱吱嘎嘎的声音刚刚能够听得清楚,但很难听懂,因此我还准备了一份录音文字打印稿分发出去。我先用麦克风播放磁带,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记者们可以听到好像是德罗林的声音,他用悲伤的声音对另一个男人说话,应该是一位联邦调查特工。打印稿把中间的空白填上了。在磁带上,德罗林请求退出这场可卡因生意,可是这名特工却威胁着要伤害他的女儿。这是一份很惹人上火的材料,我又不能鉴定这份材料的真伪,可我有很多理由相信这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么联邦局的案子就搞不下去了。
记者像炸了锅一样,他们都气疯了。他们围着我,而我的保镖却在尽力维持秩序。“再放一遍!”好几个人在叫喊。“行。”我说。第二次放也不太清楚,可这次我的身边围着记者,有些人在提问题,有些在开玩笑。其中一个说:“弗林特先生,我们看看房子怎么样?”我说:“没问题,为什么不呢?”我一下子分了心,让保镖推我进到房子里,一大群记者跟在我身后。我把带子和录音机都留在外面了,我让人出去拿进来,可再也找不到了。到今天为止,人们还在对这盘带子的突然失踪感到怀疑。我不知道应该对他们说什么,它真的丢了。很明显有人拿走了,可在当时它好像就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罗伯特·塔卡苏基是指定审理德罗林一案的法官,他认为我的目的在于扰乱该案的审判,因此向我发出传票,命令我带着录音带出庭。我情绪很糟,因此决定不予合作。塔卡苏基批准了针对我的逮捕令,1983年11月1日——我41岁生日——这天,由15名联邦人员组成的执法队在我家逮捕了我,并将我带到严厉的罗伯特·塔卡苏基面前。他要我交出带子,我告诉他说,带子丢了。他勉强同意了我的说法。他接着问:“你的录音带是从哪里搞来的?”我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对我的无礼,没有谁有权力让一位出版人或者记者提供他获取情报的秘密渠道。我开始闲扯起来,谈到我手上掌握的其他一些带子,但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这跟德罗林那盘带子有何关系?”塔卡苏基低沉地问道,他的耐心都快用完了。又说了几句话以后,塔卡苏基宣布,他将每天罚款1万美元,直到我说出来源为止。第二天他将我放了回去,拍了惊堂木。
“我操这个法庭”T恤衫表达了我的挑战姿态,第二天到法庭面见这位塔卡苏基法官大人的时候,我决定再来点更厉害的。我很愤怒,疼得厉害,吃了很多止痛剂,是一种很强烈的合剂。安妮·列包维茨在我家里,准备为《名利场》杂志拍摄一些我的照片。她让我小心地摆好姿势——全裸着躺在沙发上,身上还盖着美国国旗——这时,阿兰·伊萨克曼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我得在一个小时内到达塔克苏基的法庭上。我对自己说:“我现在像个坏小子一样三天两头被唤出庭了,还不如干脆就当个坏小子。”我把安妮带来的旗子拿过来,请我的护士把它别在我身上,就像餐巾一样。我就这样别着国旗到了法庭。塔卡苏基问了我几个问题,命令我不准出州境,还必须随时到庭。塔卡苏基对我的旗子一言未发,可这个阴险的联邦诉棍命令法警在法庭外将我逮捕了,罪名是玷污美国国旗。
两个星期后,我在一位联邦法官面前接受国旗玷污案的审理。这天,我的疼痛已难以忍受,得来上一剂才行,但在结束审理以前是不行了。当麦克马洪法官最终审理我的案子时,我的愤怒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我们激烈地争辩起来,麦克马洪命令我接受精神病检查。可他并没有给我定蔑视法庭罪。不幸的是,一位高级法官听到了争吵的声音,命令我接受另一次审讯,并在那里辩明为什么我不能被定蔑视法庭罪。一个月以后,在指定的那一天,我到庭听讼了一一可是,我当时的情绪可不是能够被哪个法官吓住的。
我坐在轮椅里被推进了法庭,面对一个阴沉的联邦法官曼纽尔·里尔。里尔的名声如同他的脾气一样糟糕,我们两个都是爆炸性的混合物,里尔以严厉的用词谴责我对国旗的行为,一场辱骂性的对话开始了。我没有说什么有意义的话,全都是在泄愤,而且是怒气冲天,我有很多气愤的理由,我的生活一团糟,我的用词也反应了我的感情,里尔警告我注意自己的语言。说到某个地方,我气愤到了极点,竟对他啐了一口。他气极败坏,尖叫着对法警说:“让这家伙闭嘴!”法警找了一根胶带,封住了我的嘴。里尔继续向我发问,可我现在只能点头摇头表示是不是了。在肯定我一定会文明说话后,他命令法警扯掉胶布。我一点也不文明,骂了很多脏话,里尔肺都气炸了。“弗林特先生!”他大喊,“我判你在联邦精神病监狱蹲6个月!现在,从我的法庭滚出去!”我对他大骂起来:“狗娘养的——你就这点本事?”他也回敬了我一句:“不!我要判你蹲12个月!”我又骂回去:“狗日的听着,只会这儿招?”他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跨过一排座椅回到他的小屋子里了,他一边走一边说:“15个月!”法警推着我的轮椅走了。一个小时内,我就到了特明诺岛的联邦监狱。
1983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许多方面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