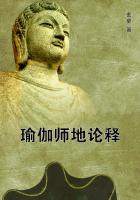阿尔西娅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我的信教是令人怀疑的人。那些觉得我并没有发疯的人认为我是不诚实的。大多数人认为我是个穷奢极欲的家伙,只喜欢金钱、肉欲,贪图安逸,只顾自己。我的信教对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个骗人的把戏,只不过是另一个增大知名度和利润的办法。我是个喜欢走极端的人,喜欢自行其是。我猜,我可以公正地说,我的再生经验带有我余下的一生的特征。我不仅渴望上帝,我是扑向上帝的,我开始了一系列新的活动。我的思想四分五裂,可是我谈到了一些计划,准备把《风尘女郎》变成一种“教会刊物”。我购买了好几种主流杂志,包括《洛杉矶新闻自由》和乔治亚州普莱因斯市的一份周报。我还宣布准备开办一份新闻杂志,取名叫《叛逆》。
同时,当我阅读《圣经》并开始结交一些新朋友时,阿尔西娅发现她得与我一边谈杂志拷贝的最后期限,一边得讨论经文。她总算想法对付过来了。后来她常说:“我从来都没有真正想过要当基督徒,主要是因为我对你无法做那样的事。”在我致力于更高的人生追求时,是她在管理着《风尘女郎》的一些俗务。当我思忖着如何为上帝工作时,她在想办法保障我们仍然留在这门生意里。《风尘女郎》通常是提前3个月出稿的,因此不可能出现紧急的变化。可是,我们如何把宗教溶入一本皮肉杂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因此,一边是我在阅读预言,一边是阿尔西娅在掌管利润,这使得关系非常紧张。
我转教也引起《风尘女郎》一一片混乱。我认为,我对妇女新的责任应该包括给每个人一份好的薪水。在一次员工会议上,我宣布:“没有谁能靠一年7000美元过好生活,因此从年初开始,每个人——员工、编辑助手、秘书——每年至少都将拿到1.5万美元。我将把可以腾出的地方都腾出来,用作日间关照中心,妇女们可以带孩子来工作,并在喝咖啡的时间内看孩子。”我的管理人认为我发疯了。在另一个会议上我宣布,公司新的政策为,不准吸烟。在《风尘女郎》工作的一些人都惊呆了,完全搞糊涂了。有些员工——多半是些工资得不到提升的人——认为我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我的转教甚至还改变了我的饮食。露丝带我入了教,可别的人,也就是我的新教友迪克·格利高里,却鼓励我成了素食者。格利高里是位说笑话的人,后来转变成了社会活动者,他让我明白了素食的好处,是由有机胡萝卜汁、矿泉水和高效维他命组成的一个食谱。我早年靠碗豆和大腊肠为生,有了钱以后吃得好一些了,可仍然是以高热量食物为主的。信教以后,几周内我减了25磅。当时我不知道,可素食很快就救了我一命。
在1978年早期,我的辛辛纳提一案的上诉仍然处于搁置期,针对《风尘女郎》的另一个猥亵案又在乔治亚的劳伦斯维尔提起公诉。尽管我已经信了教,可我对第一修正案的立场却没有改变,我决定有力地反击这次新诉案。我对露丝讲了搁置起来的那个猥亵案,她提出陪伴我,并提供感情支持。我拒绝让她跟我一起去并解释说,如果她去,那会损害她兄弟重新当选的机会,更糟的是还有可能会影响她的宗教服务活动。可我还是感激她的心意,她慢慢成了我最好的朋友。这次审判原定是在3月的第二个星期开始,因此我决定飞到巴哈马的彼德岛,和迪克·格利高里呆一段时间,以让自己准备好诉讼。我决定戒食、祈祷、研读《圣经》,试图放松自己。露丝认为这个想法不错,不过阿尔西娅却有矛盾的感情,因此决定不跟我一起去。审判开始前的一个星期我回来了,身心状况大不一样,并准备好面对乔治亚的法律诉讼。
劳伦斯维尔是典型的南方城镇,市法院稍稍有些破旧,可仍然有一种威严的气氛,它座落在市镇广场阳光斑驳的一侧。3月6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来到法院。我身后跟着一群律师,包括保尔·堪比里亚,他个子很小,是法林格忠诚的助手,还有当地的一位律师吉因·里弗斯。早晨的程序稀松平常,法官在中午11点退庭午餐。我与律师们到当地一家餐馆,即V&J饭馆,我要了两杯葡萄汁,还有一些水。中午时分,我们开始回法院,一边走一边闲谈着。这是个安静、平和,像春天一样的日子。
我们走上法院的人行道,准备上石级的时候,事情发生了,我听到了开枪的声音。“出什么事了?”我在想。我转身朝吉因·里弗斯看去,正好看见一颗子弹撕开了他的胳膊。他被打中了!当他倒地时,我还在朝枪响的方向转身。我立即听到了第二声枪响,这次可打中了我。就好像一根发烫的棍子捅进了我的腹部,我疼得直喘气,这时又被另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低头看去,发现我的小肠都翻了出来。第一枪打中的角度真是蹊跷,差点把我的肚子前面打飞。我不知道第二枪打中哪里了。当我双膝弯曲倒地并慢慢失去知觉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见鬼!我今天的官司算是打不完了!”我完全不信我有可能会死。接着,我面朝下倒在吉因旁边的地上,并失去了知觉。
救护车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在去医院的路上,我不知怎么就醒了过来,尽管仍然是迷迷糊糊的。救护人员在对我说话,他们说:“挺住,我们几分钟就到医院了。”我们到达格温莱特县医院的时候,人们在来回奔跑,大声喊叫着,我被抬出了救护车。我通过门廊时,一位医生见到我了,我双眼迷茫地看着他,说:“给我一点止痛药就行了,我没事的。”我也不知道我被伤成什么样了。我的一根腹动脉被一颗点四四的开花弹头撕开了,全身大部分的血都流出来了。我能够活下来真是一件奇事。这位医生没搭理我,而只是对着我身旁一群护士和救护人员在大声发号施令。我被直接推进了手术室。
这间小医院的乡村医生干了件了不起的工作。他用了好几个小时,尽力把我修补起来,不管有没有可能救活,决不放弃。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进行了好些几乎无望的外科手术,企图阻止我的小肠出血,并修复一些关键器官。我的小肠有6英尺多被切掉了。我空空的大肠暂时止住了感染继续扩大。如果吃得很饱,情况可能会糟得多。这位医生并没有指望我会有很大的机会活下来,事实上,他已经对保尔·堪比里亚说过,说我不一定挺得过来。保尔对他说:“他的妻子随时可能到达,就几分钟,对她千万不要这样说!”我被打中几分钟后,保尔就给阿尔西娅打了电话,她已经坐上了能找到的第一班飞机。3个小时后,她来到我的身边。
进行过好多手术后,阿尔西娅不知什么时候进来了。我因为疼痛和药物已经糊里糊涂。我们只是简单地说了几句话。我说:“他们差点干掉了我。”接着,医生要她离开,告诉她说我的脾脏裂开了,还有内出血,可找不到在哪个地方。她流着泪出去了。又过了不久,这位医生在一行人的簇拥下又进来了,说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并提议说,我最好用医用直升机转院到亚特兰大的艾莫里大学医院。阿尔西娅同意了,不到半个小时,我就飞到了艾莫里。
在艾莫里的头几天完全是一片模糊。一组医生在我七零八落的内脏里进行了11次外科手术,以阻止内脏出血,可是我还在流血不止。输了很多血,以便补偿大量失血,尽管做了很多手术,可没有人能够找到出血点。他们不能无限制地给我输血,医生叫来阿尔西娅和我的家人。“他可能挺不过来了,”医生对他们说,“只是个时间问题。”医生们保证最后再试一把,阿尔西娅哭得像个鬼。当时,我已经受了感染,浑身疼得不行,医生们认为这种感染是可以加以控制的,不过如果仍然流血不止,那并没有多大用处。管床医生召集其他医生会诊,一位年轻的放射科医生有两下子,他出了个主意:“用CAT扫描,说不准可以找出问题。”CAT在当时还是个很新的仪器。“试试吧。”大家都同意。这位医生为我订购了好多份血浆,希望进行扫描时会增大出血,因而就可以增大查出出血点的机会。
他们把我推进放射室,抬上那台巨型机器的时候,我已经失去了知觉,可扫描中途我不知怎么又醒了过来。醒来时我感到一阵恶心,可当我听到那些医生笑嘻嘻的声音时,又感到振奋起来。“找到了!”这位年轻医生很激动地说。“是一根动脉在不停地渗血,约在离心脏半英寸的地方,这里面有一块弹片,可能是弹片的某个地方把它割开的。”我在里面欢呼起来,吐得屋里的医生人人身上都是血。医生拿起注满某种止漏剂的针筒,摸索着找到了漏洞,堵住了。我的预后暂时从“病危”转变成“不好”了。
事后证明,医生对控制感染的看法过于乐观。止住流血后,腹部感染开始了。他们用好多种抗生素进行静脉注射,可某种顽固不化的细菌已经在我的内脏里生根开花——医院药库里所有的药物都奈何它不得。我持续高烧,腹部肿了起来,膨胀如鼓,看上去就好像有了身孕。医生又一次召集我的家人,对他们说,我还剩下24到48个小时。这阴惨惨的判决立成新闻消息。可在亚特兰大,一位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医生听到了这个消息。他给艾莫里打电话,对他们说:“我们这里有一种药,他可能会对它产生反应。还没有投放市场——还在试验中——可我们会想办法让你们拿到这种药。”我的管床医生告诉了阿尔西娅,她立即同意了,并签署了免除责任书。他们把我用冰裹起来,以免持续高烧导致大脑受损,同时用一根IV导管往我身上注射这种实验性的抗生素。几个小时以后,感染开始消退了。又做了一次手术使腹部感染完全清除,我的危险也解除了。我可以活下来了——好坏以后再说。
当时,我还一点都不知道,这还只是恶运开始的兆头。我的腿不能动了,尽管脊椎一点事都没有。一颗子弹穿过了脊椎底部叫做cauda equina(拉丁语:马尾)处的神经丛。这颗子弹并没有打中脊椎,否则我可能会因此而瘫痪但不会痛疼,撕开了单个的神经纤维,使我的腿不能动弹,但又保持着感知能力。我很快得知,这是叫做“周边神经损伤”的生理损伤,它会引起最剧烈的疼痛。可笑的是,当我的健康得到改善,意识完全清楚以后,这种疼痛却以指数级升了上来。流血止住了,感染消除了,而疼痛却残留下来,这疼痛完全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