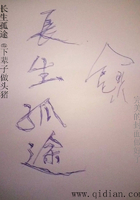我中途去洗手间。
有人在后面连声叫我:“木小姐,木小姐。”
我回过头,只见一个服务生在冲我笑:“是木小姐吧,2号包厢有客人找你。”
“客人?”
“请随我来。”
他为我带路。走到一个包厢前,他敲门:“先生,你好。”
“请进。”
我开门进去,暗暗倒吸一口凉气。
里面是林兆。
我说:“你好。”
如生意场上见大客户,发觉是多年前有老恩怨的旧故,千言万语剩下“你好”二字,已经在盘算退路。
灯光昏暗,空调送出徐徐冷风,我觉得浑身毛孔骤然收紧。
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向身边一侧伸手,“坐吧。”
“牧牧和我妈都在外面。”我说,“是服务生叫我过来。”
“我刚好看见你了。”他拿起菜单,“吃点什么?”
我拢着裙子坐下,“谢谢,我刚刚吃过。”
“喝茶?”
“吃得太饱,没有心情。”
我犹豫片刻,忍不住说,“林先生,上次的事情,我……”
“还是龙井?”
“不,不用了。”
“就明前龙井吧。”
我提高音调:“林先生。”
他终于放下菜单,抬眼看我。
这目光使我心虚,仿佛欠了他巨债,现在却要寻借口不还。
我说:“你还没有吃饭?”
“哦,我已经吃过了。”
“那就不用破费了。”我看着他,“我没有想到你在这里。牧牧和我妈都在外面等我,我只说几句话就走。”
他沉默。
“我很感谢你,这段时间你帮了我很多……我一直以为我们有默契,比如……不谈结婚的默契。”
“你的求婚来得太突然,我当时没有一点心理准备。”
“……很抱歉。”
我快快说完,准备起身。
“木晓。”
他还有话要说。
我心里警报大作,一个字不想听。
我大力开门逃出包厢,向着母亲与牧牧的方向跑去。
“……阿晓,怎么这么慢?”母亲远远向我招手,“连牧牧都快吃完了。”
我的那份饭还剩一半,已经凉透。
“太可怕了,厕所里正在排长队。”
她皱眉,“高级餐厅也要排队?”
“谁让女客这么多。”我从自己座位上拿起手袋,“我去结账。”
总台小姐仰着脸,笑得春光灿烂:“是17号桌的木小姐?”
“你们怎么知道我姓木?”
“刚才有位林先生已经给你们付了账单。”
“人呢?”
“才走的。”
旁边的服务小姐都看着我笑。她们大约以为这是情侣们玩的高级戏码,拿言情当生活看。
我二话不说追出门外,隔着玻璃远远看见楼下有一辆轿车开走。
是林兆的车。
虽然一顿饭不值几个钱,可是我不想欠他半分。
我拿出手机拨他号码:“林先生。”
“是我。”
“谢谢你主动替我们付了账单。”
“不客气。”
“不是客气不客气的问题……”我顿一顿,“我会找时间把钱还给你。”
在挂断电话的最后一瞬间,我听见他的声音:“木晓。”
我重新把手机放到耳边。
“你还爱着周宴。”
“林……”
“是不是?”
话到嘴边,我一个字也说不出。
“等你考虑清楚,给我电话。”
他先挂断。
我失神许久,才听见母亲叫我:“……阿晓,你付钱没有?”
我半夜里披衣去父亲卧室。
书桌上留着他的照片,前面有一瓶酒。
我点上烟:“爸爸,我想和你说两句话。”
他在照片里看我。
父亲生前一直不习惯拍照片。每次出去游玩,被摄影师强拉到镜头前面,他只会垂着两手,眯起眼睛,勉强向两边扯起嘴角,露出一个略带羞涩的笑容。
他用这笑容拍了一生中几乎所有的照片。
“你女儿这辈子就因为信了一个男人的求婚,走错许多路……”我说,“现在又有一个男人向我求婚,我该怎么做?”
我坐在房间地上。地板冰凉。
挂钟里秒针嗒嗒地走。
等一支烟抽完,我摁熄烟头,又拿一支放到嘴边。
突然察觉手机震动,我从口袋里拿出来看:“我是林徐,明天能不能见一面?”
我重重靠上床沿。
我才三十岁。心已经这么累。
蓦地想起林兆在电话里说:“你还爱着周宴。”
他不是说:“你是不是还爱着周宴?”也不是说:“难道你还爱着周宴?”
他是斩钉截铁:“你还爱着周宴。”
这地球上我最不想再扯上关系的就是周宴。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的女儿姓周,我要管周家老爷子叫爸爸,就连证明我们已经不再有关系的离婚证也只是拿来证明我们曾经有关系的物件。
这世上谁最爱你?反正不是向你求婚的那个人。
我霍地站起来:“爸爸,我明白了。”
正要回去自己房间,打开门,母亲就站在外面。
我不自觉后退一步:“……妈。”
她看着我,一字一字说得很慢:“你刚才说,林兆向你求婚了?”